【唐文明】阳教、阴教与文教——康有为孔教思想的提出
 |
唐文明作者简介:唐文明,男,西元一九七〇年生,山西人,北京大学哲学博士。现任职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著有《与命与仁:原始儒家伦理精神与现代性问题》《近忧:文化政治与中国的未来》《隐秘的颠覆:牟宗三、康德与原始儒家》《敷教在宽:康有为孔教思想申论》《彝伦攸斁——中西古今张力中的儒家思想》《极高明与道中庸:补正沃格林对中国文明的秩序哲学分析》《隐逸之间:陶渊明精神世界中的自然、历史与社会》等,主编《公共儒学》。 |
阳教、阴教与文教——康有为孔教思想的提出
作者:唐文明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表
选自作者所著《敷教在宽:康有为孔教思想申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闰六月初四日甲寅
耶稣2017年7月26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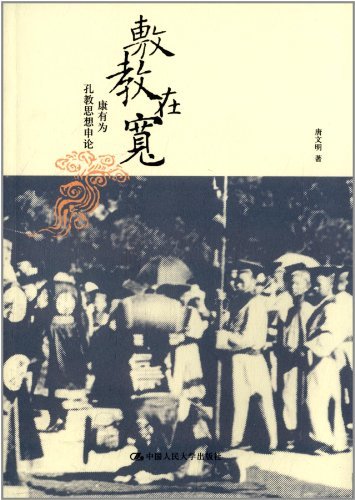
学界一般将康有为的孔教思想紧密关联于他的今文经学观点,仿佛在康有为那里,以《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为中心的今文经学观点与其孔教思想具有一种必然的关联,讲孔教就必然讲孔子为素王、为大地教主等等。
实际上这是一个错误。
“孔教”二字在康有为著作中首次出现,是在写作于1886年的《康子内外篇》,而康有为孔教思想的提出,在文献上则最早可见于比《康子内外篇》略早的《教学通义》。[1]
从其思想内容看,我们可以将康有为的孔教思想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890年会晤廖平之前,其时他还没有彻底确立他后来的今文经学立场;
第二个阶段是从他确立自己的今文经学立场一直到戊戌变法;
第三个阶段是从他戊戌流亡后到辛亥革命前;
第四个阶段则是在辛亥革命后。
其中后三个阶段都是在他确立自己的今文经学立场以后,因而之间的差异主要不在孔教的理念上,而在与政教关系有关的制度安排上。前一个阶段则基本上为学界所忽视,即使有论者论及,也往往是一笔带过而已。
本篇集中从第一个阶段考察康有为孔教思想的提出,主要是有以下两点考虑。
首先,康有为在第一个阶段提出的孔教思想与后三个阶段的孔教思想在很多方面有直接的关联,因此,从对第一个阶段的考察中我们可以更明确地看出康有为提出孔教思想的一些缘由和动机。
其次,也是最值得注意的,前一个阶段与后三个阶段涉及康有为对经学的不同理解和对孔子的不同评价,这意味着前一个阶段的孔教思想与后三个阶段的孔教思想就其经学方面的思想基础而言是很不一样的。
要言之,前一个阶段所提出的孔教理念并不是建立在后来的今文经学的思想基础之上,而这个孔教理念或许能够为未来的儒教重建提供一些更为有益的参考。
贯穿《教学通义》的一个核心思想是在治理的层面上理解教化的意义、考虑教化的落实,所谓“善言教者,必通于治”。[2]这个思想可以说是康有为孔教思想的一个基本进路,虽然他的孔教思想在后来发生了很多变化,但通于治理而言教化的思路基本上没有改变。甚至可以说,《教学通义》所针对的就是那种离治言教的思路。
在前言中,康有为概括了该书的主要内容和写作主旨:“上推唐、虞,中述周、孔,下称朱子,明教学之分,别师儒、官学之条,举六艺之意,统而贯之,条而理之,反古复始,创法立制。”[3]以下略加阐述。
康有为认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与“君子所以异于小人者”皆在于智,进而以智论圣:“智人之生,性尤善辨,心尤善思,惟其圣也。”[4]他指出,教学的内容关乎“人道之所由立”,主要包括礼教伦理和事物制作。
礼教伦理的确立和事物制作的完备皆需要极高之智,所以教学之始源只能归诸具有极高之智的上古圣人,他将之断自黄帝:“礼教伦理必在事物制作之后,虽或造于庖牺,必至黄帝而后成也。礼教伦理立,事物制作备,二者人道所由立也。礼教伦理,德行也;事物制作,道艺也。后圣所谓教,教此也;所谓学,学此也。”[5]
自黄帝至尧舜,逐渐确立了制作极美的德行道艺之教:“传及尧、舜,道绪皇皇,上下百年,万制昌洋,盖教学之至盛也。”[6]在此他引《尚书》、《孟子》中舜“命契为司徒”、“命夔典乐”等记载,指出“立教设学,自此始也”。[7]此所谓“上推唐、虞”。
康有为阐述立教设学自尧、舜始的观点时最核心的一点是他明确区分了教、学、官,并试图联系历史和现实刻画这种区分的重要意义:
“今推虞制,别而分之,有教、有学、有官。教,言德行遍天下之民者也;学,兼道艺登于士者也;官,以任职专于吏者也。下于民者浅,上于士者深;散于民者公,专于吏者私。先王施之有次第,用之有精粗,而皆以为治,则四代同之。微而分之,曰教、学;总而名之,曰教。后世不知其分擘之精,于是合教于学,教士而不及民,合官学于士学,教士而不及吏,于是三者合而为一。而所谓教士者,又以章句、词章当之,于是一者亦亡,而古者教学之法扫地尽矣。二千年来无人别而白之,治之不兴在此。今据虞制别教、学,釽擘条理,推求变坏,知所鉴观,以反其本,则教、学有兴。”[8]
康有为对教、学、官的区分意味着他从一开始就区分了三种不同的教:庶民之教、士夫之教和官吏之教,亦可从学的角度分别称之为庶民之学、士夫之学和官吏之学。《教学通义》的核心内容,就是刻画这三种教或三种学在历史上的流衍,其核心观点正如上引文所提示的,认为三者合而为一其实意味着庶民之教和官吏之教皆亡,只剩下士夫之教,而士夫之教又亡于章句、词章之学。
康有为聚焦于从周公到孔子的变化,来说明庶民之教和官吏之教皆亡而只剩下士夫之教的过程。此所谓“中述周、孔”。他首先阐发章学诚的看法,以周公为制度、典章之集大成者:
“盖黄帝相传之制,至周公而极其美备,制度、典章集大成而范天下,人士循之,道法俱举。盖经纬天人,绝无遗憾,而无事于师儒学校之矜矜言道也。”[9]
然后分别以公学、私学为目,详说周公制作之美备,进而论及周衰时的失官、亡学,以至于孔子的“不得位而但行教事”。公学、私学之分亦追根于虞制:
“盖司徒教民,故以兴行为先;典乐教胄,又以德艺为重。然礼掌于伯夷,又无射、御、书、数,则教胄实在崇德也。当时稷教稼穑,夷典三礼,垂作工,益作虞。夫曰教稼典礼,必有教学,推之工、虞,当亦复然,则非徒司徒、典乐之教可知也。但司徒、典乐之教为公教,凡民与国子皆尽学之;稼、礼、工、虞为私学,或世其业,或学其官,而后传之也。”[10]
质言之,公学乃成人之通学,私学乃守官之专学:
“公学者,天下凡人所共学者也;私学者,官司一人一家所传守者也。公学者,幼壮之学;私学者,长老之学。公学者,身心之虚学;私学者,世事之实学。公与私必相兼,私与私不相通。”[11]
康有为此处以身心之虚学与世事之实学区分公学与私学容易引起误解,仿佛公学所指只是后世所谓德行之学,其实不然:
“公学凡四:一曰幼学,《尔雅》以释训诂,《少仪》以习礼节也;二曰德行学,六德则智、仁、圣、义、中、和,六行则孝、友、睦、婣、任、恤也;三曰艺学,礼、乐、射、御、书、数也;四曰国法,本朝之政令、教治、戒禁也。四者天下之公学,自庶民至于世子莫不学之。庶民则不徒为士,凡农、工、商、贾必尽学之,所谓公学也。”[12]
其论私学,则曰:
“既各有专官,各有专学,则各致其精,各不相知,如耳、目、鼻、口各不相通,而皆有专长。其他不能,不以为愧,不知,不以为耻。材智并骛,皆足以致君国之用。”[13]
值得注意的是,康有为论公学与私学皆涉及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之学。一方面,他将六艺之学归于公学,认为“六艺为古凡民之通学,非待为士而后能。”[14]另一方面,因为六艺皆涉官守,皆有专精,所以六艺之学亦列于私学。我们知道,康有为对公学与私学的这些论说是以《周礼》的记载为依据的。
在论及周代学制即国学、大学时,康有为同样依据《周礼》,但提出一个理学意味颇重的观点,即认为执掌大学的大司乐“专以乐教国子”,其目的在于养德,从而与师、保、司徒、司谏、司救及其他百职之官在分工上呈现出不同:
“原先王之教学,所以舍弃六行、六艺、百职与一切名物、度数、方技,而专崇乐者,所以养德也。德成为上,行成次之,名物、度数为下。变化气质,涵养性情,德也。夫自司徒、谏、救董教于乡遂,师氏、保氏总学于王宫,自王公卿士之子及俊秀之士,既无不笃伦饰行,身通六艺矣。若百职之学,各有专官,咸世其业,书存于府,吏为其师,国子即百司之官吏也,既各守父师之业,自能讲求,而后入于大学,则大学无事重教之也。且大学之乐师于百官之业不能相通,百司之书不能遍习,亦无以教之也。譬稷子之习于农,伯夷子之习于礼,益子之习于虞,垂子之习于工,皆公卿之子充补胄子者。若以其专家世守,岂夔所能教哉?此司乐之所以舍六艺、百职而惟乐是教也。”[15]
在以《周礼》为依据阐述了周代教学之盛况后,康有为博引诸经文献,叙说周衰时的失官、亡学,即我们常说的礼坏乐崩,进而申明孔子定六经、立儒教:“孔子不幸生失官之后,搜拾文、武、周公之道,以六者传其徒,其徒尊之,因奉为六经。习其学、守其道者,命为儒。”[16]
康有为的“中述周、孔”就其基本意图而言与章学诚一样,都是为了强调周公之制的重要性。对周公之制的强调当然不意味着对孔子的贬低,而是有鉴于后世对孔子的尊崇偏于义理德行方面而忽略了孔子之所愿乃在于恢复周公之制。
因此,我们看到,康有为最终回到 “周、孔之道”的传统说法以衡定周公与孔子,并在联系现实时试图以庄子所谓的“内圣外王”为理想提出一个更为整全的治教复兴方案:
“经虽出于孔子,而其典章皆周公经纶之迹,后世以为学,岂不美哉!虽然,以之教学则可,然亡官守之学则不可。……今复周公教学之旧,则官守毕举。庄子所谓百官以此相齿,以事为常,以衣食为主,蕃息畜藏,老幼孤寡为意,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外王之治也;诵《诗》、《书》,行《礼》、《乐》,法《论语》,一道德,以孔子之义学为主,内圣之教也。二者兼收并举,庶几周孔之道复明于天下。”[17]
前已述及,就对周公与孔子的理解而言,康有为在《教学通义》中与章学诚最大的不同,在于他提出了《春秋》为孔子改制之作的观点。对于孔子作《春秋》、改制度在历史上所发挥的功效,康有为则以君臣名分为要领、以“讥世卿”为主旨,刻画了从汉到清的变化:
“《春秋》之学,专以道名分,辨上下,以定民志,其大义也。自汉之后,《春秋》日明,君日尊,臣日卑。依变言之,凡有三世:自晋至六朝为一世,其大臣专权,世臣在位,犹有晋六卿、鲁三家之遗风,其甚者则为田常、赵无恤、魏罃矣;自唐至宋为一世,尽行《春秋》讥世卿之学,朝寡世臣,阴阳分,嫡庶辨,君臣定,篡弑寡,然大臣犹有专权者;自明至本朝,天子当阳,绝出于上,百官靖共听命于下,普天率土,一命之微,一钱之小,皆决于天子。自人士束发入学,至位公卿,未尝有几微暗于之念动于中,故五百年中,无人臣叛逆之事。”[18]
对于秦汉以来的这段历史,康有为紧扣教学的主题,以立学为主线,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他首先对汉代的立学作了评价,其中有肯定,但更主要的还是批评,甚至认为后世的问题还是出在汉代:
“余读汉史《儒林传》及《艺文志》,未有不色然而喜也。喜经学之兴,喜先王大道之有籍以传,喜孔子之学尊而大盛。及见明帝临雍亲讲,圜桥观听之士亿万人,东京风俗以原,气节以昌,未尝不叹田蚡、孙弘立学之功,美武帝之崇儒,德汉儒之能抱遗经也。及考求学术之变,后世民治之坏,则不得不深罪汉之君臣,每读《儒林传》而湫然矣。”[19]
具体来看,康有为对汉代立学的批评主要是说,本来是源自先王的内容丰富、极其美备的教学体系,在汉代则变为五经之学,进而变为章句之学,由此造就的只是“无家国之任,惟高陈大道”的儒者。换言之,虽然汉代立五经博士是教学制度重建的一个重要事件,但仅止于立五经博士却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意味着“六艺不定成书,百官亦无专业,小民不能下逮”,且“轻当王之典为已甚”。康有为还以假设的口吻说:“若采搜古经雅记,定六艺之公学,制百职之官书,斟酌先王,施于当世,然后立学而教之,使后世有所籍,以增长润色,不必复国公之道,何尝不美备也?”[20]
概言之,康有为认为,汉代虽然立学有功,但“立学又不备”,这是导致后世制度驰废坏绝、教学不兴的历史根源。
在谈及宋代的立学问题时,康有为有一处提到了朱子。他首先肯定朱子《学校贡举私议》“请罢解额舍,选待补、混补、季书、月考之目”的意义,指出其目的在于“以塞怀利干进之心,选道德之士及诸生之贤者,而命以官,讲明道艺以教训其学者”,然后笔锋一转,对朱子提出批评,理由是朱子没有依据三代学校之教对于教学内容提出改革意见,仍袭旧时章句之学:“而所谓教之之法,亦仍汉、唐章句史学之旧,而非能复三代学校之教也。……朱晦庵庶几于道德之师而不足言。”[21]
于是问题就产生了:既然康有为在对秦汉以后立学之历史的刻画中对朱子有明确的、实质性的批评,又如何理解他在前言中所说的“下称朱子”?要明确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从《教学通义》一书的结构说起。
前已提及,有学者认为《教学通义》一书可以第十一章“春秋”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部分。这种看法实际上是在康有为的今文经学究竟是否抄袭了廖平、《教学通义》是否在康有为见廖平之后做了关键性的修改等陈旧争论的左右下产生的。很容易注意到,《教学通义》中直接看起来与康有为后来的今文经学立场比较接近的一些观点,主要出现在第十一章“春秋”和第十八章“六艺上”中。
因此,如果以康有为抄袭了廖平且在见廖平之后关键性地修改了《教学通义》立论的话,那么,很自然地就会以第十一章“春秋”为界将《教学通义》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并提出康有为见廖平之后主要修改了后半部分的结论。这个看法的问题首先在于其忽略了在第九章“六经”中康有为对《春秋》的看法已经和章学诚不大相同,其次,也是更重要的,这个看法未能从《教学通义》的整体写作构想来看待其结构和各章之间的关联。
我们知道,康有为写作《教学通义》,本亦有上书之意,所以其意图在于缵三代教学之绪而又立足现实,提出一整套他认为堪称完备的教学复兴方案。以此来看《教学通义》一书的整体结构,我们可以将之分为前后两个部分:
从第一章“原教”到第十二章“立学”是前半部分,主要是依据经、史方面的有关记载,阐述尧舜以来一直到清代教学问题的沿革和演变,第十三章“从今”则是一个转折点,从这一章一直到最后第三十一章“谏救”是后半部分,主要是以前半部分的论述为基础,立足现实,提出一整套他认为堪称完备的教学复兴方案。
就是说,如果将《教学通义》分为前后两个部分的话,那么,应当以第十三章“从今”为界,而非以第十一章“春秋”为界,这是符合《教学通义》一书的整体写作构想的。
于是,接下来的问题就在于,既然在第十二章“立学”中已经对朱子提出了“庶几为道德之师而不足言”的批评,为何在第十三章“从今”之后的第十四章又提出了“尊朱”?这个问题更直白的表达是,如何理解第十四章“尊朱”在《教学通义》整本书中的位置和意义?如果仅仅是想在对宋代之立学提出严格批评的基调上对朱子作出有限的肯定,那么,第一,不需要以“尊朱”这样高调的说法命题,第二,肯定朱子的这一章不应当放在作为前后转折的“从今”这一章之后,而是应当放在之前。
但事实是,康有为是在第十三章“从今”之后谈论“尊朱”的。这其实表明,康有为对朱子的尊崇,与他推述尧、舜、周、孔而阐发出来的教学思想有密切关系,也与他试图立足现实提出一整套教学复兴方案的想法有密切关系。康有为对朱子的尊崇,首先当然不能被理解为仅仅是对作为理学家的朱子的尊崇。这一点从上引第十二章“立学”中他对朱子的批评就可以看出。
而在写作时间相近的《民功篇》中,康有为明确对朱、陆的理学进路提出了批评:
“近世学术,大端有朱、陆之二派,一在格物理,一在致良知。二者皆托于《大学》,而自以为先圣之学。传其绪者,相攻若寇敌。余以为皆非也。”[22]再者,康有为对朱子的尊崇,也不能被理解为仅仅是对作为历史上的一个经学家的朱子的尊崇,尽管他对朱子的经学成就作出了不低的评价。[23]
理由很明显,正如前面已经论及的,如果这样的话,“尊朱”这一章的内容就应该放在“从今”这一章之前。由此不难想到,康有为推述尧、舜、周、孔而阐发出来的教学思想,正是他尊崇朱子的思想基础——当然也是他批评朱子的思想基础。
康有为对朱子的尊崇,还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意味,就是说他是以继承朱子的事业为一生之志向的,正如上引《谒白鹿洞紫阳书院》第二首诗中所表达的那样:“煌煌遗规在,吾道有蕲向”。
说得更明确一点,康有为的核心想法是,以尧、舜、周、孔以来的教学统绪为依据,以朱子的遗规为指南,立足现实,提出一整套完备的教学复兴方案来。此即前言中所谓的“下称朱子”。其中“立足现实”这一点,也就是康有为着重表达的“从今”之义。“从今”这一章在《教学通义》中的重要性也值得充分重视。康有为刻画教学之历史而提出的一个重要看法是,因应时代的变化而进行改制是三代教学统绪中的应有之义,如周公、孔子,皆是改制之圣人。圣贤从今之旨还表现在对国法、掌故的重视上,这是他在讨论公学时已经谈到的。
质言之,整个《教学通义》的核心思想,其实就是从今改制。于是我们看到,康有为以如下话语结束“从今”这一章:“故从今之学不可不讲也。今言教学,皆不泥乎古,以可行于今者为用。六艺官守,咸斯旨也。朱子曰:‘古礼必不可行于今,如有大本领人出,必扫除更新之。’至哉是言也。”[24]
于是我们还看到,“尊朱”这一章之后,康有为按照前面对于三代教学体系中不同部类的划分,多处引用朱子,尽可能参考朱子的相关做法和想法,依次提出他的一整套教学复兴主张,计有幼学、德行、读法、六艺、敷教、言语、师保、谏救等内容。[25]
第十五章论幼学,康有为依据《礼记·内则》等经典,指出幼学“其事至切实,一则为学世事之基,使长不失职,一则为人义之始,使长可为人,乃人道之必然,理势之至顺者也。”[26]
接着,康有为指出秦、汉以后“幼学无善书颁行天下”,其中特别评论了朱子晚年所编《小学》:“朱子晚年编《小学》,分立教、明伦、修身三例,引古嘉言善事明之,所以养德性、立人伦,于先王立教之道,诚为近矣。但其所编,规模未善,不失于深,则失于杂,于先王蒙养之义,幼子切近之学,考以古《少仪》、《弟子职》之意,未为当也。……朱子思虑精密,而忘为幼学计,亦其疏也。若朱子于幼学留意,为编一书,五百年人才必不止是也。”[27]
之后在此基础之上,康有为以“拟分三十类”提出“今修幼仪”的具体方案,其要点即在“以通今为义”。
第十六章论德行,康有为仍以朱子的《小学》为主要讨论对象。他认为朱子的《小学》其实不是幼学之书,而是德行之书,于是他在德行一章提出的方案是,以朱子的《小学》为主,再加调整、增附,与国法一起颁于民间,讲于学堂:“朱子《小学》一书,虽名《小学》,而中引古今嘉言善行,实言德行之书也。若汰其高深,别其体例,叙六德为统宗,以诸法拊之,分六行为门目,缀嘉言善行于其下,以经为经,以儒先之言行为传,兼明祸福之报,以耸天下之民,颁之于乡学,令民皆讽诵,州里僻壤广设学堂,朔望与圣谕、国律同讲,民无有不听。不听者以为无教,人共摈之。”[28]
第十八章论六艺之礼,关乎康有为从今改制思想的核心内容。康有为同样以称引朱子的方式来表达从今改制、修定礼乐的重要性和正当性:
“朱子曰:‘礼,时为大。使圣贤有作,必不从古之礼。只是以古礼灭杀,从今世俗之礼,令稍有防范,节文不至太简而已。’又曰:‘夏、商、周之礼不同,百世以下有圣人作,必不踏旧本子,必须斩新别做。’又曰:‘礼坏乐崩二千余年,若以大数观之,后来必有大人出来尽数拆洗一番。’夫新王改制,修订礼乐,本是常事,而二千年中,不因创业之未暇,则泥儒生之陋识。有王者作,扫除而更张之,亦何足异乎?朱子谓:‘不知迟速在何时?’此晦盲否塞至于今日,此其时也。”[29]
康有为就复兴礼乐的问题所提出的方案是:
“今宜将国朝《会典》、《通礼》广加增备,及公私仪式定为一书,颁发郡县,立于学官,自穷乡远方社学义学咸令诵读。岁时饮酒,乡老学师率其子弟会而习礼,择其精熟,上名于教官,而后许入学试吏。其有公私仪式不从官书者,以违制论。有司时时举罚之,则国礼之行遍于遐壤,风一道同,庶几复周时六礼防民之义也。”[30]
至于如何对本朝的《会典》、《通礼》广加增备,康有为亦本之从《周礼》中提炼出来的六艺兼及公学、私学的思想,提出由士人之通博者修定《礼案》的建议:
“王者既制《会》、《礼》,颁之于天下,则上自朝廷,下及州县之史,乡党之师,必有专习礼科者。若六朝贺循、熊安生、皇侃、崔灵恩之属,专门礼学,以备仪礼采问之选。而士人之通博者,亦欲考知古今,得以推礼制损益之故,则当采集经传,分四代之古礼,别周、孔之异制,下及汉、唐二千年来礼制之因革沿革,定为一书,谓之《礼案》。俾学者有所考求,而不致庞杂于耳目,烦劳其心思,白首而不能言,穷老而无所用。今刑律有《刑案汇览》,以参定疑狱,岂可无《礼案汇览》乎?”[31]
在此他又一次谈到朱子,评价了朱子的《仪礼经传通解》:“朱子《经传通解》,从事晚暮,不及成书而卒,大体虽举,未免疏略。”[32]实际上仍是以朱子的遗规为指南。
在具体论述如何修《礼案》时,康有为提到经学中的今古文之别的问题:
“今修《礼案》,欲决诸经之讼,平先儒之争,先在辨今古之学。今古之学,许叔重《五经异义》、何休《公羊解诂》辨之,近儒陈左海、陈卓人详发之。古学者,周公之制;今学者,孔子改制之作也。辨今古礼,先当别其书。古学者,周公之制,以《周礼》为宗,而《左》、《国》守之。孔子改制之作,《春秋》、《王制》为宗,而《公》、《谷》守之。”[33]
此处以礼制之异辨今古文经学之别的看法,也被有些学者作为康有为抄袭廖平的一个主要证据。[34]虽然我们不能完全排除康有为会晤廖平后对《教学通义》有所修改,但摆脱那些无谓的争论,我们首先应当意识到,《教学通义》一书的核心思想是从今改制,而康有为在此辨今古文经学之别是服从于该书整体的论说脉络的。
具体而言,康有为在此处主张辨今古文经学之别,目的是为了修一部《礼案汇览》,是为了总结历史,衡定周、孔,这和他确立今文经学立场之后辨今古文经学之别的情况很不一样。后来辨今古文经学之别是要否定古文经学,因而必须对古文经学的“非正当来源”作出一个明确的解释,此即《新学伪经考》以“刘歆伪造古文”立说的意图所在。
在《教学通义》中,康有为辨今古文经学之别的思想并不是为了否定古文经学,而是为了澄清周公之制与孔子之制的区别,以彰明“新王制作,修定礼乐,本是常事”的从今改制思想。前后立场最大的差异自然还是体现在对孔子的评价上。
具体而言,在《教学通义》中,康有为的实际看法是,孔子的改制也是随时损益,并不具有为万世立法的意义,对后世只具有参考价值;而在《孔子改制考》中,康有为的立场和汉代公羊学家是基本一致的:孔子的改制不仅是为汉代立法,也是为万世立法。
这样的话,是不是说《教学通义》中的康有为由于过分尊崇周公而对孔子的评价太低,且在看待经典的立场上具有一种历史主义的嫌疑,以至于将孔子从圣人降低为一个相对一般的历史人物?[35]
诚然,以孔子为素王、为大地教主的看法是对孔子的极高评价,但或许一个更为理性的尊圣态度并不意味着将作为圣人的孔子拉低为仅仅作为一个历史人物的孔子,而且更有可能获得历史文献的充分支持。
在历史的孔子和圣人孔子之间自然存在着诠释的张力,不过,承认孔子是一个历史人物并不一定会消解孔子的圣性;而肯定孔子的圣性,也不必拒斥孔子作为历史人物的一面。
其实,孔子的圣性恰恰、也只能展现在他自己实际生活的时代和处境中,且礼以时为大、当随时损益也正是经义中所有,就是说,有可能的是,礼之随时损益不惟不是对经义的放弃,恰恰是以经义为准绳而又立足现实的改制之作。
实际上,如果忽略在具体理解上的一些差异,主要从如何衡定周、孔的角度看,康有为在《教学通义》中对孔子的看法,与朱子的看法也是相当接近的。朱子强调礼当随时损益,并不影响他亦以孔子为立教之圣,所谓“继往圣,开来学,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虽然在此我们首先还是应当提到章学诚对康有为的影响。
第十九章论六艺之射御,康有为再一次通过具体的问题充分表达了他的从今改制思想。他建议将古代的射礼改为烧抢礼,理由是:
“推古人之义,不在器而在义也。射之义在武备,今之武备在枪炮,则今之射即烧抢也。则烧抢为凡今男子所宜有事也。古者有乡射礼、大射礼,则今宜立乡烧抢礼、大烧抢礼。燕饮有射,选士有射,则今燕饮以烧抢,选士亦以烧抢也。射有正、有耦、有鹄、有乏、有获、有鼓,烧抢亦立正、立耦、立鹄、立乏、立获、立鼓,皆以寓武事于承平,寓将卒于士夫也。为射之器者,有弓人、矢人,讲求于精,则枪厂制造亦宜精也。射为六艺之一,天下男子所共学,今亦以枪为六艺之一,天下共学之可也。师古人之意,不师其器也。”[36]
从今改制的思想,也充分体现在论读法、论言语、论师保等具体各章中,此处不再详述。[37]
就我们讨论的主题而言,最值得注意的是第二十八章论敷教。敷教的问题,在前面论幼学、论德行、论读法等章已有所涉及,而康有为专门列一章论敷教,可见他对这个问题的重视。如果说在康有为的教学复兴方案中,庶民之教、士夫之教和官吏之教皆在考虑之中的话,那么,论敷教这一章专门针对的是庶民之教的问题。
康有为首先重述了《教学通义》一开始就阐发过的主题,即敷教之制来自虞舜之命契为司徒,而至春秋、战国时已沦亡,其标志即是教与学的混淆,或者说“误以教属于学校”:
“自黄帝制舟车,制文字,即有以教民,旁行四海,民服其教。帝舜命契曰:‘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盖忧天下民之不教,故命司徒总领敷教之事。既曰‘敬敷’,则必有章程行其敷教之法,必有官属宣其敷教之言,必有堂室以为敷教之地,然后能遍于天下之民。若学校,则有典乐之夔,绝不相混也。《周官》尚有岁月读法,谏救劝德犹是敷教之余法,不与学校相杂。孟子言:‘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义。’则专申教,而误以学校系之,皆未知教学之流别也。自尔之后,误以教属于学校,读法、谏救之典皆亡,小民于是无由被王者之泽。”[38]
误以教属于学校,导致以学为教。而以学为教,其实意味着教的沦亡,因为学主要面向士大夫,而教则主要面向庶民,二者有很大的不同:
“夫学患不深详,教患不明浅;学患选之不精,教患推之不广,义皆相反。以学为教,安能行哉?”[39]
教的沦亡首先意味着敷教制度的沦亡,具体来说就是教章(敷教之章程)、教官(敷教之官属)、教堂(敷教之堂室)的沦亡。后世以六经设官立学,于士夫之教勉强可行,于庶民之教则有所不逮,此所谓“以专经为学,学虽失其实而犹存其意,教则殆尽亡之。”[40]
教的沦亡的后果是“民无由被王者之泽”,在此康有为特别提到了因“民无教化”而使基督教等异教及巫术在民间广为流行的状况:“滇、粤之间,百里无一蒙馆,以巫为祭酒,为其能识字也。故耶稣教得惑之。今遍滇、黔、粤之间皆异教,以民无教化故也。豫、陕、燕、齐之民亦少识字者,皆无教故也。”[41]
康有为还反驳了那种认为庶民之教并不重要的观点。
他首先提到,虽然官方敷教之制已沦亡,但民间犹有善堂之设,实切于古敷教之义,只是其内容多流于驳杂而不要于正:
“官不敷教则民自设之。今民间善堂多为宣讲善书之举,此古敷教之义。其耸动民心,而劝之迁善悔恶不少。惜宣讲之书既杂以释道,大率袁了凡之学,不要于正,又无官劝之。”[42]
之后他指出,因此而对庶民之教心存轻视者其实是“本末舛决,目不见丘山”,并将这个问题提到国家治乱的高度上来看待:
“士人高者讲研经史掌故,下者为词章科举,非斥其不典,则鄙其俚俗,笑而置之。不知人心风俗之所寄,国家治乱之所关,视学校选举之政,未巨有宏于兹者也。选举止及于士,敷教下逮于民。士之与民,其多寡可不待计也。而士大夫多轻视之,此所谓本末舛决,目不见丘山者也。乱国之政不务本,亡国之政不务实,其以此夫。”[43]
在说明了敷教之重要性之后,康有为就敷教问题提出了具体的方案:
“今为敷教之书,上采虞氏之五伦,下采成周之六德、六行,纯取经文切于民质日用,兼取鬼神祸福之根,分门别目,合为一经,详加注释,务取显明,别取儒先史传之嘉言懿行为之传以辅之。以诸生改隶书院,以教官专领敷教事,学政领之,统于礼部。每州县教官分领讲生,隶之义学,以敷教讲经为事,以《大清通礼》、《律例》、《圣谕》之切于民者,以幼稚书数之通于世事者辅之。常教则为童蒙。朔望五日敷宣,则男女老孺咸集。朔望大会益盛,其仪其义简而勿繁,浅而勿深,务使愚稚咸能通晓,推行日广,远方山谷,务使遍及,苗黎深阻,一体推行,愚氓朴诚,耸劝为易,性善之良,人所同具,兴善远罪,共兴于行。下美风俗,上培国命,为政孰大于是!讲生开一善堂,于德行、道艺宜许之以彰瘅之事,以劝风化。其大者上之教官转达学政,有所奖罚,兴行自易,此谏救让罚之义也。”[44]
这个敷教方案至少有以下几点值得留意。
首先,鉴于敷教之事主要针对庶民,士大夫所习之传统经典又太繁难,康有为建议以传统经典为依据,另编敷教之书,其内容主要侧重人伦日用,亦包括鬼神祸福之说。
其次,康有为建议设立敷教之官,即隶属礼部的学政、教官、讲生等,给予敷教以制度上的保障。
第三,康有为在此明确提出了定期讲经的建议,而教官、讲生所讲者还包括国法、幼学等方面的内容。
第四,康有为还建议敷教之官属应有奖罚之权责,如《周礼》中之司谏、司救有让罚之义一样。[45]
最后,康有为高度肯定了恢复敷教之制之于为政的重要意义,所谓“下美风俗,上培国命,为政孰大于是”。
从以上对《教学通义》一书主要内容的简要梳理可以看到,虽然康有为在《教学通义》中没有明确使用“孔教”一词,但孔教的主张在《教学通义》中已经昭然若揭了。而他的孔教主张,一言以蔽之,就是师法上古、三代而恢复敷教之制。
或许有人会认为既然“孔教”一词与“儒家”或“儒教”等传统的说法不同,而康有为在《教学通义》中也没有使用“孔教”一词,那么,康有为的孔教理念就与他后来立足今文经学立场而以孔子为素王、为大地教主的看法具有必然联系。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看法。
前面已经提及,康有为首次使用“孔教”一词,是在写作于1886年的《康子内外篇》中。《康子内外篇》的写作时间稍后于《教学通义》,离康有为会晤廖平差不多还有四年,其时康有为当然尚未确立其今文经学立场。就是说,康有为在确立今文经学立场三、四年前,就已经使用“孔教”一词了。
实际上,康有为在《康子内外篇》中对孔教的理解与他在《教学通义》中所表达的教学思想没有太大的区别。一个明显的证据是,如果说康有为在确立了今文经学立场之后的“孔教”概念是相对于早期的“周孔之教”而言的,那么,在《康子内外篇》中,康有为恰恰是以“孔教”来指涉“中国五帝、三王之教”或“二帝、三皇所传之教”,就是说,恰恰是以“孔教”作为“周孔之教”的简称。
与此相关的是,在《教学通义》中康有为虽然有尊崇周公的一面,但他同样尊崇孔子。康有为对孔子的尊崇在很大程度上也体现在他对朱子的尊崇上,而朱子对孔子的尊崇实过于对周公的尊崇。
从以上梳理也可以看到,康有为提出孔教主张的思想基础来自《尚书》、《周礼》,其中的要点是对教、学、官的区分,即对庶民之教、士夫之教、官吏之教的区分。正是以这一区分为依据,康有为论及后世庶民之教的沦亡,而他的孔教主张正是基于庶民之教沦亡的看法而提出的。
其中立教章、设教官、建教堂等制度性设置,则是基于司徒敷教“必有章程行其敷教之法,必有官属宣其敷教之言,必有堂室以为敷教之地”的看法而提出的。
学界流传甚广的一个说法是认为康有为提出制度化的孔教是在模仿基督教,这一说法至少就康有为早期的孔教建制主张而言是很不妥当的。从《教学通义》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康有为就复兴孔教而提出的制度方面的主张,和基督教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联系。他始终站在国家治理的高度上看待恢复敷教之制的重要性,而立教章、设教官、建教堂等制度性建言也都是对朝廷的进言。
另外也可以想见,其时他对基督教并没有多深的了解。[46]不过,基督教在民间的发展的确是他提出孔教主张的一个现实触动。这一点意味着,康有为是在强烈的现实关怀下以《尚书》、《周礼》等经典的思想为依据提出了他的孔教主张。与此相关的一点是,师法上古、三代而恢复敷教之制的孔教主张,从属于《教学通义》一书的核心思想,即从今改制的思想,或者说是从今改制思想的一个具体内容和重要组成部分。
那么,师法上古、三代而恢复敷教之制的孔教主张,与康有为的理学背景有何关联呢?这是本篇从一开始就试图讨论的一个问题。
实际上,从前面的梳理中我们可以看出,康有为提出恢复敷教之制的孔教主张,与他的理学根底和为学进路有很大关系。
首先,康有为对周孔之道的认识是以他自己的灵修工夫为基础的,而他的灵修工夫恰来自他的理学根底。具体来说,康有为以周、孔之道为一个教化,这个看法最重要的一点,系之于他的灵修工夫。我们可以在很多层面上理解一个教化的存在,但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教化对人心的安顿作用,即教化能够为人提供具有终极意义的安身立命之所。
其次,康有为对朱子学的服膺和理解使他更重视教化落实的制度问题,更重视通于治理而言教化的思想,从而也使他在重建敷教制度的考虑上采取了明显的政教一体的进路:“故人民之先,未有不君、师合一,以行其政教,如中国者也。事势既极,而后师以异义称而释然也,离于帝王之以为教焉。后起者如耶稣之于欧洲亦是也。昔疑耶稣何能于罗马立教,观于佛氏之立而释然也。中国陆、王之学,离政教而言心,亦是也。”[47]
第三,正是因为他的理学根底,才使他的经学研究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敢于且能够拒斥乾嘉学派猎琐文单义、无关乎人心风俗的为学进路。本性理之学通之经、史之学的为学进路,对于理解清代以来的儒学变化相当重要,这一点似乎还没有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48]而与经学相对应的正是教化的概念。就是说,本性理之学通之经、史之学的为学进路也提示我们应当充分重视康有为提出孔教思想背后的经学基础。这一点除了从《教学通义》对《周礼》、《春秋》以及《尚书》等经典的讨论中清晰可见之外,也特别表现在康有为对朱子的评价上,即他不是仅仅在一个集大成的理学家的意义上肯定朱子,而是在儒教教化史的宏大视野中就朱子所做的全盘性的教化改革而充分肯定朱子。
行文至此,或许有人会问,在写作《教学通义》和《康子内外篇》的时期,康有为是否认为孔教是一种宗教?在《康子内外篇》的“性学篇”中——如前所述,这也是康有为最早使用“孔教”一词的篇章——我们可以找到一个较明确的答案。
在其中,康有为以阴阳之义论列诸教:
“天地之理,惟有阴阳之义无不尽也。治教亦然。今天下之教多矣:于中国有孔教,二帝、三皇所传之教也;于印度有佛教,自创之教也;于欧洲有耶稣;于回部有马哈麻,自余旁通异教,不可悉数。然余谓教有二而已。其立国家、治人民,皆有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之伦,士、农、工、商之业,鬼、神、巫、祝之俗,诗、书、礼、乐之教,蔬、果、鱼、肉之食,皆孔氏之教也,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所传也。凡地球内之国,靡能外之。其戒肉不食,戒妻不娶,朝夕膜拜其教祖,绝四民之业,拒四术之学,去鬼神之治,出乎人情者,皆佛氏之教也。耶稣、马哈麻、一切杂教皆从此出也。圣人之教,顺人之情,阳教也;佛氏之教,逆人之情,阴教也。故曰:理惟有阴阳而已。”[49]
从中可以看出,如果我们对“宗教”一词采取狭义的理解,那么,与“宗教”相当的或许是康有为所谓的“阴教”。就此而言,孔教不是宗教,因为孔教是顺乎人之性情而设立的阳教。不过也不要忽略,阳教与阴教都是教。
因此,如果我们把“教”或“教化”作为一个种概念来概括诸教,那么,可以把孔教或儒教称为文教而区别于狭义的宗教。
注释
[1] 其实关于这一点,梁启超早就明确指出过,只是学术界未曾注意罢了。在写作于1901年的《南海先生传》之“第六章:宗教家之康南海”中,梁启超说:“先生所著书,关于孔教者,尚有《教学通义》一书,为少年之作,今已弃去。”这是明确将《教学通义》作为论孔教之书。见《饮冰室合集》第一册,《饮冰室文集》之六,第69页。
[2] 见《康有为全集》第一集,第19页。
[3] 见《康有为全集》第一集,第19页。
[4] 见《康有为全集》第一集,第20页。
[5] 见《康有为全集》第一集,第20页。
[6] 见《康有为全集》第一集,第20页。康有为另有《民功篇》详述自庖牺至尧、舜、禹诸圣制作之功。
[7] 见《康有为全集》第一集,第20页。
[8] 见《康有为全集》第一集,第21页。
[9] 见《康有为全集》第一集,第21页。
[10] 见《康有为全集》第一集,第20页。
[11] 见《康有为全集》第一集,第21页。
[12] 见《康有为全集》第一集,第21页。
[13] 见《康有为全集》第一集,第26页。
[14] 见《康有为全集》第一集,第23页。
[15] 见《康有为全集》第一集,第29页。正是因为持有这个观点,他反对程、朱以先王之学制论《礼记》中之《大学》的看法:“《大学》一篇,殆后儒论学之精言,而非先王学规之明制,微妙精深,尤非十五岁之童子所能肄业也。”见《康有为全集》第一集,第31页。
[16] 见《康有为全集》第一集,第35页。
[17] 见《康有为全集》第一集,第38页。我们知道,在确立自己的今文经学立场之后的康有为也常常引用庄子的这段话,而描述的对象则全部落在了孔子身上。就是说,后来的康有为以孔子为内圣外王的典范,而早期的康有为则将周公与孔子合在一起作为内圣外王的典范。
[18] 见《康有为全集》第一集,第40页。他又提到《春秋》之功,亦施于日本。
[19] 见《康有为全集》第一集,第40页。
[20] 见《康有为全集》第一集,第40页。
[21] 见《康有为全集》第一集,第43页。这一批评也是康有为对胡瑗的批评。
[22] 见《康有为全集》第一集,第82页。
[23] 康有为尊崇朱子当然有朱次琦的深刻影响在里面,而朱次琦对朱子的评价恰恰摆脱了汉、宋之争的门户心态,是以朱子为郑玄以后折衷汉、宋的百世之师:“孔子殁而微言绝,七十子终而大义乖。岂不然哉!天下学术之变久矣。今日之变,则变之变者也。秦人灭学,幸犹未坠。汉之学,郑康成集之。宋之学,朱子集之。朱子又即汉学而稽之者也。会同六经,权衡四书,使孔子之道大著于天下。宋末以来,杀身成仁之士,远轶前古,皆朱子力也。朱子,百世之师也。”见简朝亮编:《九江年谱》,转引自钱穆:《朱九江学述》,见《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卷八,第314页。
[24] 见《康有为全集》第一集,第45页。与他后来的托古改制的思想相比,托古在这里还没有出现,而是依古,不过,忽略其中一些具体的差异,可以说,无论是托古还是依古,其实都是从今的表现。
[25] 中间有七章文目俱阙。
[26] 此处所引来自题为《论幼学》的一篇单行文章,见《康有为全集》第一集,第59页。编者在这篇单行文章下加按语曰:“今存《教学通义》缺‘幼学’一篇,或即本文。”
[27] 见《康有为全集》第一集,第59、60页。
[28] 见《康有为全集》第一集,第47页。
[29] 见《康有为全集》第一集,第48-49页。第49页对朱子的称引还有:“朱子曰:‘孔子欲从先进。礼之所以亡,正以其太繁,周文已甚。’”“朱子曰:‘古礼必不可行于今。’”“朱子谓:‘《仪礼》非一时所能作,逐渐添得精密,然后圣人写出本子,皆以称情立文也。’”
[30] 见《康有为全集》第一集,第48页。
[31] 见《康有为全集》第一集,第50页。
[32] 见《康有为全集》第一集,第50页。
[33] 见《康有为全集》第一集,第50页。
[34] 黄开国、唐赤蓉:《<教学通义>中所杂糅的康有为后来的经学思想》,载《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1期。
[35] 这正是康有为在确立今文经学立场之后的观点:“以孔子修述六经,仅博雅高行,如后世郑君、朱子之流,安得为大圣哉?章学诚直以集大成为周公,非孔子。唐贞观时,以周公为先圣,而黜孔子为先师。……神明圣王,改制教主,既降为一抱残守阙之经师,宜异教敢入而相争也。今发明儒为孔子教号,以著孔子为万世教主。”语出《孔子改制考》,见《康有为全集》第三集,第85页。
[36] 见《康有为全集》第一集,第52页。
[37] 第二十章题为“六艺下”,当是论六艺之书数,但有目无文。
[38] 见《康有为全集》第一集,第53页。
[39] 见《康有为全集》第一集,第53页。
[40] 见《康有为全集》第一集,第53页。
[41] 见《康有为全集》第一集,第53页。
[42] 见《康有为全集》第一集,第53页。
[43] 见《康有为全集》第一集,第53页。
[44] 见《康有为全集》第一集,第53-54页。
[45] 《教学通义》第三十一章题为“谏救”,可惜有目无文。
[46] 康有为对基督教的了解加深,是在戊戌变法失败他流亡海外之后。但即便如此,康有为终生并未对基督教进行过任何认真、深刻的研究。
[47] 《康子内外篇》,见《康有为全集》第一集,第111页。
[48] 余英时的“内在理路说”注意到了宋明性理之学与清代儒学的关联,但惜乎其对性理之学的意义不能充分认识,从而在刻画清代儒学的变化时强调了从性理之学走向史学的进路,而忽略了从性理之学返回经学的进路以及在西学东渐之前的史学与经学的密切关联。作为余英时的老师,钱穆虽然更重视宋明性理之学,但他亦囿于现代性观念及现代人文学科的设科理念,同样突出了史学的进路而忽略了经学的意义。我们或许会将钱穆、余英时的问题追究至章学诚,因为现代以来以经为史的看法从思想渊源上来说是来自明确以“六经皆史”立论的章学诚。但这么简单地下论断对于章学诚可能是不公平的。我们知道,章学诚梳理了一个浙东学术的谱系,自陈他是陆、王心学的继承者,又认为戴震等人的学问是朱子学的流衍。虽然这一看法还有很多方面需要进一步分析,但章学诚所谓的“六经皆史”并不是对经学的反动,而是对经学的一个解释,因而和现代以来认为六经皆为历史的看法有天壤之别。
[49] 见《康有为全集》第一集,第103页。
【下一篇】【闾海燕】乐水乐山:孔子对“比德”的增值
作者文集更多
- 唐文明 著《隐逸之间:陶渊明精神世界··· 02-17
- 李天伶著《誓起民权移旧俗——梁启超早期··· 09-03
- 【唐文明】论孔子律法——以《孝经》五刑··· 04-07
- 【唐文明】定位与反思——再论张祥龙的现··· 12-29
- 唐文明 著《极高明与道中庸:补正沃格··· 09-15
- 【唐文明】三才之道与中国文明的平衡艺术 01-06
- 歌曲孔子版《孤勇者》(唐文明填词并注··· 09-09
- 唐文明 著《与命与仁:原始儒家伦理精··· 07-21
- 【唐文明】敬悼张祥龙老师 06-09
- 【唐文明】沃格林与张灏先生的中国思想··· 05-27
微信公众号
儒家网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

微信公众号
儒家网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