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勇】关于美德的正义:儒家对桑德尔正义观的修正
关于美德的正义:儒家对桑德尔正义观的修正
作者:黄勇
来源:《南国学术》2017年第4期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十一月三十日戊申
耶稣2018月1月16日
《南国学术》编者按:黄勇教授认为:哈佛大学教授桑德尔反对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正义观,提出了一种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正义观。这种正义观,一方面强调正义是一种美德,另一方面又坚持一种以美德为根据并以目的论为导向的分配原则。具体来说,正义就是按照(相关的)美德来分配东西,以认可、尊重、祝贺和奖赏有德之人,并惩罚那些缺乏美德甚至具有恶德之人﹔而要确定哪些美德与所分配的东西相关,则要看所分配的东西所服务的目的。例如,分配大学的教职需要追问这些教职的目的。假如这些教职的目的是传授知识,那么,就应该将教职分配给那些具有有助于实现这个目的的美德之人,即那些拥有相关知识并能将这些知识传授给学生的人。在中国,儒家虽然同意正义是美德,但把作为个人美德的正义与作为社会制度的美德的正义区分开的同时,又强调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后者以前者为基础。相较于桑德尔以美德为根据的正义,儒家更强调关于美德的正义,即关于美德之分配的正义。当发现一个社会中有些人具有美德,而另一些人缺乏美德时,儒家并不像桑德尔主张的那样,通过对有德者与缺德者不平均地分配物品来奖励前者和惩罚后者。相反,儒家将有德者比作身体健康的人,而将缺德者比作身体有缺陷的人。正如人们不会奖励身体健康的人而惩罚身体有缺陷的人,而是会努力帮助身体有缺陷的人消除其缺陷从而成为健康的人一样;人们也不应该奖励有德者而惩罚缺德者,而是应该帮助缺德者克服其缺陷从而也成为有德者。由于儒家视有些人有德而另一些人缺德为一种非正义的现象,因此,关于美德的正义也就是努力使每个人都成为有德者。虽然桑德尔的亚里士多德主义正义观也认为国家有义务让其公民成为有德者,但与儒家的一个重要差别是,前者认为这种道德教育的任务主要是通过立法完成的,而后者则强调德教和礼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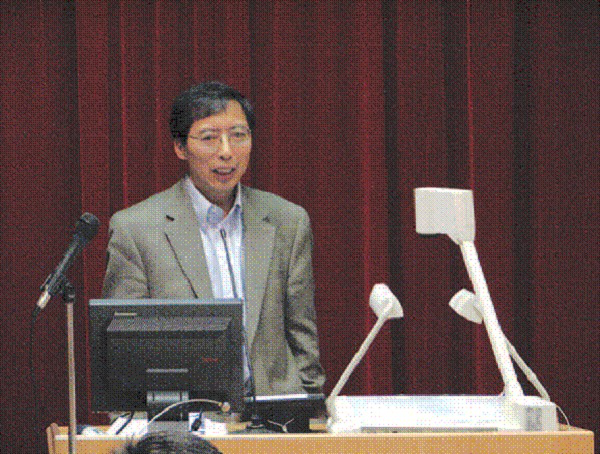
黄勇,1988年在复旦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96年任教于库兹敦大学,1998年在哈佛大学获神学博士学位,1999—2001年任美国中国哲学家协会主席,2006年任哥伦比亚大学宋明儒学讨论班共同主任,2010年任美国宗教学会儒家传统组共同主任,创办并主编Dao: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道:比较哲学杂志》,德国斯普林格出版社出版);现为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教授,主要从事政治哲学、伦理学、宗教哲学、中国哲学和中西比较哲学研究,代表性英文著作有《宗教之善与政治正义:超越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道德的动机》《孔子》,中文著作有《全球化时代的伦理》《全球化时代的宗教》《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等。
导言
在《正义:该如何做是好?》(Justice: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一书中,哈佛大学教授桑德尔(Michael J.Sandel)考察了三种正义观:(1)功利主义认为,正义是福祉或幸福的最大化;(2)自由主义认为,正义即尊重自由与人的尊严;(3)亚里士多德主义认为,正义是认可、推崇和奖励美德。对于这三种不同的观正义,桑德尔并非一视同仁。他认为,主导当代政治哲学的前两种正义观美中不足,他自己致力于提出一种亚里士多德主义理论。【注1】这种理论有两个主要特征,即“作为美德之正义”(justice as a virtue)和“依据美德之正义”(justice according to virtues)。
根据这样一种正义观,一方面,正义的作用不只是协调一个群体的活动并对由此产生的成果加以分配,否则一个黑帮内部推行的规则也可能被视作正义。因此,桑德尔在其早期著作中主张,“如果正义的增长并不必然意味着一种绝对的道德进步,那么,人们就会看到在有些情况下,正义并不是美德而是恶德”【注2】。为了确保正义是美德而非恶德,人们必须采用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目的论,把正义作为一种卓越品格,使人类发挥其独特的功能,实现其独特的完满。正是在此意义上,桑德尔认为,“有关正义和权利的争论,必然要依赖某种关于完满生活的特定观念,而不管我们是否承认它”【注3】;也正因为如此,他不赞成自由主义的看法(以罗尔斯为代表):对于宗教和形而上学的完善概念,人们的正义概念应该保持中立。
另一方面,桑德尔强调,亚里士多德(Αριστοτέλης,前384—前322)的政治哲学中有两个相关的核心观点:“其一,正义是目的论的。对于权利的界定要求我们弄明白所讨论的社会实践的目的(telos,即意图、目标或本性)。其二,正义是荣誉性的。为了思考或讨论一种行为的目的,至少有部分工作是思考或讨论它应当尊重或奖励何种美德。”【注4】在解释桑德尔的意思之前,有必要说明,他在这里谈论的目的论,不同于作为美德之正义所涉及的目的论。后一种目的论关注人类生活本身之目的,依据它可以把一种品格界定为善或恶。然而,前一种目的论关注的是特定社会实践的目的。例如,分配大学教职需要追问大学的目的。这就是桑德尔所认为的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的第一个核心观点。第二个观点与此密切相关,因为正是社会实践的目的告诉人们,一个人为了获得想要的东西应该具有何种美德。【注5】就一所大学来说,一个人必须在相关知识和教学技能方面出类拔萃才能获得教职。在这个意义上,正义就是按照(相关的)美德来分配东西,以认可、尊重、祝贺、奖赏有德之人,并惩罚那些缺乏美德甚至具有恶德之人。【注6】桑德尔举了很多例子来说明自己的观点,这里可以概述其中的两个。在正例方面,桑德尔提及“紫心勋章”(the purple heart)的分配:“除了能带来荣誉之外,这枚奖章还能使获得者在老兵医院享有诸多特权……真正的问题在于奖章的意义及其所推崇的美德。那么,相关的美德是什么呢?不像其他的军功章,紫心勋章推崇牺牲而非勇敢。”【注7】在反例方面,桑德尔提到美国政府对华尔街某些在2008—2009年金融危机中经营失败的公司实施救助。公众对救助计划感到愤慨,特别是因为一些资金被用于向那些公司的高管发放奖金。诚如桑德尔所言:“公众认为这在道德上是难以接受的。不仅仅是这些奖金,整个经济援助计划似乎都是在有悖常理地奖励贪婪的行为而不是惩罚它。”【注8】简言之,正义在此意义上要求奖善惩恶。
然而在我看来,讨论作为美德的正义时,厘清作为一种个人美德的正义与作为一种社会制度之美德的正义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而中国儒家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有着十分独特的贡献。因此,在讨论依据美德之正义时,本文将发展出一种“关于美德之正义”(justice of virtues)的儒家观点,以修正桑德尔的正义概念。
一、作为美德之正义
说正义是一种美德似乎没什么问题,而且中国儒学总体上认同这一点。不过,有个问题必须讲清楚。当人们说正义是一种美德而不是恶德时,所谓的美德、恶德,最初指的是个人的品格。正义的其他含义,都是由此派生出来的。例如,我们可能会说某一行为是正义的,这意味着这个行为来自具有正义品格的人;我们也可能说某一事态是正义的,这意味着它产生于具有正义品格的人(人们)。【注9】这与健康有点类似,健康最初的意思与人的身体有关。在派生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人吃的食物很健康,环境有益于健康,或者某人做了一个对健康有益的决定,这意味着它们都与人的身体健康有关。
就此而言,正义是一种个人美德。然而,当代关于正义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伦理学家罗尔斯(J.B.Rawls.1921—2002)《正义论》的启发,所谓正义——如果不是唯一的话——首先与社会正义有关。它所讨论的主要问题,不是一个人在与他人互动或处理互动的过程中正义与否,以及在何种意义上、多大程度上、如何正义;而是一个社会在治理成员之间的互动方面正义与否,以及在何种意义上、多大程度上、如何正义。正是在此意义上,罗尔斯有一句名言:“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美德。”【注10】因此,这里的正义不是个人美德,而是社会制度的美德。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如果正义作为一种美德有两种含义(作为个人美德的正义,作为社会制度之美德的正义)的话,那么,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呢?
莱巴尔(Mark Lebar)区分了连接二者的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认为个人美德具有逻辑上的优先性,个体之间的正义关系构成政治制度的正义。按照这一理解,我们首先看有德之人试图维持的与他人的关系是怎样的……然后追问何种制度和公共规则可以允许和维持这些关系”;相反,“第二种方式……认为,作为国家构成要素的制度、实践等等的结构之正义(国家这一政治实体是社会正义、制度正义或政治正义等属性的首要载体)才具有逻辑的优先性。这里,至关重要的是,我们知道正义的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根据其作为这个社会的成员所具有的义务和理由,我们可以从这个结构中推演出正义的个体所具有的责任”。【注11】第一种方式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注12】,而第二种则以罗尔斯为代表。不过,在我看来,这两种方式都是成问题的。
依照亚里士多德模型,社会制度的正义源自于个体正义。这正确地强调了政府促使人们有德(在现在这一特定的情形下则是正义这种德)的重要作用。然而,这种模式假定,当且仅当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正义地行动,社会正义才能实现。进一步的假定则是,无论是在分配方面还是在矫正方面,一切正义都由个体而非政府来完成。第一个假定显然是不现实的,因为如果这样,只要一人不义,社会就不可能正义。至于第二个假定,在一个古老的小城邦中或许确实还有一些合理性,但在一个当代的大型民族国家中显然是不可能的。例如,美国缅因州的一位农夫不可能知道,在旧金山是否有、以及有多少无家可归的人值得拥有他所生产的东西。在如此大型的社会里,资源的分配必须由国家来完成。仅有个体成员的正义是不够的;国家所做的分配和矫正也应该是正义的。
这似乎正是第二种模型的力量所在。该模式以罗尔斯为代表,强调正义是一种社会制度的美德。问题在于,它如何与作为一种个体品格的正义相关。罗尔斯的正义原则是人们在原初状态之下选择的,因此,人们或者可以说,这些正义原则反映或表达了这些在原初状态中的人的美德或正义品性。在此意义上,也可以说,罗尔斯的社会制度正义同样源自个体正义。然而,这一解释显然不成立。因为,如罗尔斯所述,原初状态的人首先都只关心自己的利益,而漠视他人的利益,因此不可能认为他们是有德的(在一般意义上)或正义的(在特定意义上)。【注13】正确的理解是,罗尔斯把原初状态作为一种决定社会制度正义原则的独立程序。在他看来,虽然我们知道以这种方式独立决定的规定社会制度的正义原则必须是正义原则,但是,如果社会中的个体不接受这样的原则,社会就会不稳定;因此,从童年开始培养个体的正义感就很重要。例如,罗尔斯认为,“当制度正义时……那些参与这些社会安排的人们就会获得相应的正义感和努力维护这些制度的欲望”【注14】。然而,即使罗尔斯的正义原则对社会制度而言确实是正义原则,由于推衍这些正义原则的过程丝毫没有考虑(使人成为人的)人类本性,运用它们来决定作为一种个人品格的正义这种美德本质上是成问题的。每一个体应该具有的美德乃是让他们成为完满之人的品格;如果不知道什么是人性,就不可能理解什么能使人成为完满之人;但是,在原初状态中选择正义原则的人那里,任何人性概念都被明确排除在外了。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莱巴尔对这样的政治正义概念有所不满,因为罗尔斯“可能会以始料未及的方式限制个体正义的可能性”【注15】。
鉴于连接两种正义的这两种方式都没有希望,莱巴尔哀叹:“我们可能无法看到,作为个体美德的正义概念可以和制度正义相一致。”【注16】然而,我认为有理由更加乐观地看待这一问题。这里,我想到的是美德伦理学家斯洛特(Michael Slote)的进路。依照他最新的美德伦理学,有德之人具有“同感”(empathy)能力,而“同感”被视作一种美德。为了解释那种关联,斯洛特认为,“一个既定社会的法律、制度和习俗就像该社会的行为”;正如个人行为反映或表达主体的品性,一个社会的法律、制度和习俗反映或表达创造它们的社会群体的品性:“因此,一种以同感关怀为基础的情感主义伦理学能够说,如果制度和法律、以及社会习俗和惯例可以反映出那些负责制定和维持它们的人所具有的同感的关怀动机,那么它们就是正义的。”【注17】斯洛特和亚里士多德都认为,作为社会制度之美德的正义由作为个人美德的正义派生而来。就此而言,他们的进路是相近的。其区别在于,在亚里士多德的模型中,作为社会制度之美德的正义旨在培养正义的人;而在斯洛特的模型中,作为社会制度之美德的正义确保个体之间的互动或交往是正义的。
中国儒家大体上会接受斯洛特的观点,认为社会制度的正义反映了领导人的道德品性。他们的“内圣外王”观念就表达了这个思想。外王,即政治制度,仅仅是内圣即道德美德的表现。例如,孟子(约前372—前289)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注18】“四书”之一的《大学》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这是说,政府是善的(一般意义上)或正义的(特定意义上),只是因为治理它的人是善的。孟子还说:“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注19】这里他强调,因为领导人有德,政府也就有德。
不过,中国儒家也不完全同意斯洛特的观点,因为他们的要求要高得多。斯洛特认为,一项法律如果体现或表达了立法者的同感动机就是正义的;但同时他也承认,“一项法律只要没有反映或表现出它的制定者之适当的同感关切之缺失,它也可能是正义的”。【注20】他解释道:“道德败坏的国家立法者,对同胞福祉和国家利益漠不关心,但可能通过一项不会体现或反映其贪婪和自私的法律。例如,如果他们通过在全国范围内允许车辆在亮红灯的路口右转的法律,那么这项法律还是正义的,或者至少不是不正义的。”【注21】斯洛特在社会的正义法律和个人的正义行为之间进行过模拟。如果回到这个模拟,我们便可以看到斯洛特作出以上让步的问题。斯洛特所想的是,不具备美德或者甚至具有恶德的立法者所制定的法律,如果没有反映其恶德,可能与那些体现并表达有德的立法者之美德的法律无异。这就好像一个具有恶德之人所做的事情,如果没有反映其恶德,也可能与一个具有美德之人的行为没有不同。我们知道,这种具有恶德的人的行为不能被视作有德的行为,而只能视为合乎美德的行为。然而,亚里士多德指出:“合乎美德的行为并不因它们具有某种性质就是(譬如说)正义的或节制的。除了具有某种性质,这个行为者还必须处于某种特定的状态。首先,他必须知道那种行为。其次,他必须经过选择而那样做,并且因那行为自身之故而选择它。再次,他必须出于一种确定了的、稳定的质量而那样选择。”【注22】他进一步指出:“有些行为之所以是正义的或节制的行为,是因为它们是以正义的和有节制的人所具有的方式做出的行为。一个人被称为正义的人或节制的人,并不仅仅是他做了这样的行为,而是因为他像正义的或节制的人那样地做了这样的行为。”【注23】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儒家总是强调一个人不仅应该做正直之事,而且应该由正直之心去做。因此,孟子赞扬圣人舜,说他“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注24】。
人们可能会问,一项内容相同的法律出自正义的人或不正义的人,二者之间究竟存在何种实际的差别。一个可能的回答,尤其是从儒家角度来看,是法律永远不可能完美,总是有漏洞。若把一项法律仅仅视作一项法律,我们倾向于从字面上对待它,因此可能会被引导去做一些明显不正义但并不违法的事情。相反,若把法律看作是立法者美德的表达和反映,我们倾向于强调它的精神,因此即使法律允许甚至要求我们去做,我们也不会被引导去做一些明显不正义的事情。这里就用斯洛特举过的例子:法律允许司机红灯时右转。如果只把它当作一项法律,那么,哪怕在交通拥堵红灯右转会堵塞路口时,或者在看到一辆车从相反的方向(非法)左转时,我们可能还是会试图在红灯时右转,因为这是合法的。然而,如果我们认为法律反映了立法者的美德,我们就不会这样做,因为我们可以理解,这样的行为不可能是有德之人愿意我们去做的。这里也可以用罗尔斯的差别原则作为另一个例子。假设这个原则是正义的,也就是说,它合乎立法者(或政治哲学家)的美德,但它并不是由一位有德的立法者(或政治哲学家)制定的。如果我是才华出众的人,该原则对我来说意味着,除非我的薪水比别人高,否则我就不充分发挥我的才能让平庸者获得最大的益处;如果我属于平庸之辈,该原则意味着,我不会允许一个有才华的人赚得更多,除非他充分发挥其才能让我受益。【注25】但是,如果我们认为该原则不止是合乎立法者的正义品性,而是实际上就是正义的;也就是说,它反映和表达了立法者的正义这种美德,那么,如果我才华出众,就会把该原则的意图理解为,我应充分发挥才能以最有效的方式让平庸者受益。因此,即使我的薪水不比别人高,我仍然会充分发挥我的才能(尽管不太容易说,平庸者该如何如何)。【注26】
二、依据美德之正义,抑或关于美德之正义?
接下来转向桑德尔的新亚里士多德主义正义观的第二个特征,我将其描述为“依据美德之正义”:分配某物,要根据其所认可、推崇和奖赏的相关功绩、卓越或美德。这一正义概念最适用的领域似乎是分配职位、尤其是政治职位和荣誉,但在分配经济利益方面却不尽然。例如,现在主要是以货币的形式分配经济利益。如果是长笛或其他特定的实体,它们还可能有一个目的,后者可以说明我们确定,在分配它们的时候何种相关的美德需要考虑。但是,如果追问货币的目的(用来买什么东西)和它所认可、推崇、奖赏的美德(擅长投资或讨价还价),便多少有点奇怪。社会机构提供的多种服务亦是如此。例如,医院的目的是提供医疗卫生服务,因此,应该向那些能够比别人更好地服务于这个目的人提供医生职位。然而,若问应该如何分配医院提供的医疗服务,以及病人应该具备哪些美德来获得这些服务,则显得有些奇怪。或许可以说,应该根据人们对社会的贡献程度分配财富和医疗(服务)。这种观点似乎合乎亚里士多德的逻辑。然而,罗尔斯会觉得这非常令人难以置信,因为偶然的自然和社会因素会影响人们对社会所做的贡献大小,不应该由此决定他们应该分配到多少。
桑德尔的一些主张让人觉得,他的“依据美德之正义”似乎是一种普遍的分配原则,适用于任何被分配的事物。【注27】不过,有时他似乎把它限定于荣誉和政治职位的分配。如上文所言,他的依据美德之正义在这些领域的应用最为合理。至少有两种迹象表明,桑德尔坚持这种受限较多因而也较为合理的观点。第一个迹象,他在比较亚里士多德和当代政治哲学家时认为:“今天我们讨论分配正义的时候,主要关心的是收入、财富和机会的分配。对亚里士多德来说,分配正义主要不是关于金钱,而是关于职位和荣誉。”【注28】人们有理由认为,桑德尔讲依据美德之正义,心里想的主要是职位和荣誉。第二个迹象在于,桑德尔肯定“应得”(desert)概念至少是公平分配的部分基础。众所周知,罗尔斯对基于应得的分配正义提出了强有力的反驳,因为他主张,由于偶然的自然和社会事件的影响,无人应得任何东西。桑德尔讨论罗尔斯正义理论的这部分内容时持非常赞许的态度。【注29】即使他(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试图捍卫“应得”概念,他仍然声称罗尔斯的观点在道德上是有吸引力的,因为“它打消了精英社会中人们所熟悉的那种自以为是的幻想:成功乃美德之冠,富人之所以富有是因为他们比穷人应得的更多”。【注30】当然他也主张,罗尔斯的观点“令人不安”,因为“从政治上或哲学上来说,我们不可能使关于正义的论证脱离关于应得的争论”。【注31】不过,当他提出这样的主张时,他所举的例子包括“就业和机会”【注32】,以及诸如“学校、大学、职位、职业、公共职位”等问题。事实上,整个讨论以大学入学政策结束【注33】。
不管怎样,即便是桑德尔正义观最言之成理的部分:根据职位(特别是政治职位)——依其目的——所认可、奖励、推崇的美德对职位进行分配,中国儒家也会深表疑惑。解释儒家这一疑惑的最好方法,就是强调儒家正义观的一个面向。它不仅与亚里士多德的正义观(包括桑德尔所发展的版本)相一致,而且实际上也可以成为其组成部分。我称之为“关于美德之正义”【注34】。简言之,如果桑德尔的“依据美德之正义”是关于依据美德来分配某些事物的正义,那么儒家的“关于美德之正义”便是关于美德自身的分配正义。换句话说,如果桑德尔的“依据美德之正义”认为政治职位是被分配的东西,那么,儒家的“关于美德之正义”把政治职位视为可以用来分配美德的工具之一。
在任何一个社会里,最可能的是,有些人具有美德,有些人缺乏美德或者具有恶德。换言之,人们并不同样地拥有美德。在讨论正义要求人们如何处理这样一种状态之前,首先需要了解美德以及恶德的本质。儒家的美德观采用了一种健康模型。根据这个模型,有德之人犹如健康的人,而恶人犹如身体忍受疾病折磨的人。例如,孟子把人皆有“四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比作有“四体”【注35】,把道德与身体联系了起来。王阳明(1472—1529)是明代最具影响力的理学家之一,他把一个缺乏美德的人或邪恶之人比作身处悬崖边的人。就像后者即便免于一死也将遭受巨大的身体伤害,前者将遭受内在的伤害。【注36】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人的内在健康即美德比外在健康即身体健康更加重要。因此,当二者发生冲突时,应当照顾前者而非后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孟子做了著名的“小体”(肉身)“大体”(道德心)之区分,嘲笑人们关心处理小事的小体而疏忽处理大事的大体:“体有贵贱,有小大。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养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注37】
这样的观点,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并不陌生。他也经常比较身体的健康和灵魂的健康。譬如,他认为,只听医生的话不会使病人身体健康;同样,只听哲学家的话不会使人们灵魂健康。【注38】《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关于正义的讨论甫一开始,亚里士多德便对一个做事正义的正义之人和一个健康步行的健康之人进行了模拟。【注39】事实上,当他对爱自己外在幸福的粗俗的自爱者与爱自己美德的真正的自爱者进行对比时【注40】,他的观点与儒家的观点相一致:人的内在健康比人的外在健康更加重要。
这样一来,就很明显,如果有人有美德而又有人有恶德,正义要求我们做的,不是奖赏有美德的人、惩罚有恶德的人,而是帮助后者摆脱恶德成为有德之人,正如当我们发现健康的人和病人时,正义要求我们所做的不是奖赏前者惩罚后者,而是设法治愈或减轻后者的疾病。也许有人会说,把身体上的健康与品性上的美德相模拟是不恰当的,因为人的健康超出人的控制范围,而人的品性则在控制范围之内。然而,这种说法并不完全正确。一方面,比如通过保持运动、远离烟草、摄入健康的食物以及保持充足睡眠,人的健康很大程度上在可控范围内;另一方面,人的品性并不完全在一个人的掌控之中。
关于第二点,儒家尤其是宋明理学家有过一个很好的解释。再以王阳明为例。在王阳明看来,一个人之所以缺乏美德或具有恶德至少涉及两个其无法控制的因素。首先,王阳明提到了与生俱来的“气”或“气质”。王阳明认为:“良知本来自明。气质不美者,渣滓多,障蔽厚,不易开明。质美者渣滓原少,无多障蔽,略加致力之功,此良知便自莹彻,些少渣滓如汤中浮雪,如何能作障蔽?”【注41】当代哲学家特别是受过西方哲学传统训练者,可能会发现王氏对“气”的形上学讨论很繁琐且难以理解,但很多人恐怕也同意他试图阐发的要点:正如人天生的自然禀赋存在着自然的不平等,人的先天道德质量也可能存在着自然的不平等。至少亚里士多德也持类似观点。例如,他区分了生性有道德感的人和天生不遵从羞耻感的人【注42】;当有人认为一个人好是天生的时,他回应说:“本性使然的东西显然非人力所及,而是由一些神圣的原因赋予那些真正幸运的人的。”【注43】他还说,应该对“天性低劣的人”实施惩罚和管束【注44】。
其次,王阳明强调环境影响对一个人道德品性的重要性。在引用“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泥,不染而黑”这两句古话之后,他接着说,民俗之善恶,是习性长期积累造成的结果,从而影响生活于其中的人的道德质量:“往者新民盖常弃其宗族,畔其乡里,四出而为暴,岂独其性之异,其人之异哉?亦由我有司治之无道,教之无方。”【注45】这包括缺乏早期的家庭道德教育,缺失良好行为的刺激,以及他们被他人的愤怒咒骂进一步推向邪恶。因此,王阳明断言,如果有人逐渐堕入罪恶,无论是有司(政府)还是父母和邻居都难逃其咎。如果王阳明认为人们天生的道德素质不平等的观点在某些人看来仍然颇具争议,那么,他关于环境影响人们道德教养的观点显然不存在争议。例如,罗尔斯认为,不仅人们天生的能力和禀赋容易受到自然事件和社会事件的限制,而且他们的美德也不完全是他们自己的:“有人认为,获得使我们能够去努力培养我们的能力的优越品性乃是我们自己的功劳,这样的论断同样是成问题的,因为这样的品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早期生活所处的幸运的家庭和社会环境,而对这些条件我们是没有任何权利去邀功的。”【注46】
然而,身体健康和品性美德之间的模拟在某些方面的确不能成立。一方面,如果一个人的身体存在严重的问题,例如身患绝症,那么在人类文明的现阶段、现有医疗技术水平之下,确实无计可施。即使正义要求人们平等地分配身体健康,也可能无法实现。相反,儒家相信,无论一个人由于何种原因而变得何等邪恶,这个人仍然可以变成有德之人。换言之,美德的平等分配总是可能的,这就是为何儒家认为人人可以成圣。另一方面,身体健康与美德相类似,而与长笛和金钱等物质的东西则不类似。在后一种情形之下,某人的长笛好则另一人的长笛就差些,某人金钱多些则另一人就金钱少些,因为这样的东西无论如何丰富总是有限的。相反,一个人越健康、越有美德,并不意味着另一个人的健康和美德就一定变得越差,因为它们的供给近乎无限。或许我还可以进一步争辩说,更可能的是,一个人变得越健康、越有美德,实际上越有益于另一个人变得更加健康和更有美德。不过,健康与美德之间仍可能有不类似之处。就身体健康而言,很容易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即使所有疾病都是可以治愈的,也会因一部分病人所需要的药品出现供应短缺而延误。这样就会出现这些药物如何分配的问题,一个人得到(更多)药物而变得健康,当然就意味着另一个人得不到(足够的)药物而无法康复。然而,如果是让没有美德或有恶德的人变得有德,就很难找到与药物短缺相似的情形。
三、“美德”可以分配吗?
在说明了人们之间正义或平等地分配美德的观点并不像它乍看起来那样荒谬之后,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何做到这一点?儒家思想提供了两种渠道。一方面,需要自我修养。儒家认为,尽管成为恶人并不完全是某个人自己的错,但这个人至少要部分地对自己成为恶人负责;此外,只要愿意努力,他也可以成为善人(诚然,一个人身处的自然与社会条件越是不良或不利,他就越是要做出更大的努力)。另一方面,正义要求人们做的——不管作为个体还是政治领袖——不是奖励善人惩罚恶人,而是帮助恶人克服他们的恶,从而使他们止恶成德。如此一来,美德就可以在所有人中间平等或正义地分配。这里一是修己(自我道德修养),二是立人(道德教育)。【注47】本文重点讨论第二个方面。因为,人们现在关心的是,当美德分配发生不正义即不平等时,正义要求人们怎么做?
儒家思想的一个独特之处在于,一个人之所以有德,不仅仅是因为这个人帮助那些遭受饥饿、寒冷、疾病或其他生理痛苦的人;而是因为这个人想让他人成为有德之人。【注48】阐明这一儒家思想的办法是,弄清儒家黄金律的独特之处,尤其是通过与其他传统中类似的道德律作比较。按照西方传统对于“黄金律”的理解,一个人应该像他愿意(或不愿意)别人对他做某件事那样对别人做(或不做)某件事。然而,道德黄金律并不要求一个想要遵循黄金律的人使别人也遵循黄金律。例如,一个人希望自己身处困境时有人帮助他,那么按照黄金律,他要帮助身处困境的人;不过,黄金律并不要求他促使别人也帮助身处困境的人。一个人不希望自己受到不公平待遇,那么按照黄金律,他不能待人不公;不过,黄金律并不要求他促使别人也不待人不公。然而,儒家的道德黄金律不止于此。一个人除了应该像他愿意(或不愿意)别人对他做某件事那样对别人做(或不做)某件事,孔子(前551—前479)还主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注49】。“立”的含义非常清晰,就是要培养或实现自我。在孔子那里,这意味着更多关注一个人的内在品性而非一个人的外在幸福。孔子列举自己重要的生命节点,说到“三十而立”【注50】。毫无疑问,他谈论的是自己品性的形成。关于“达”,孔子自己提供了一个定义:“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注51】所有这些都清楚地表明,“达”主要与一个人的内在幸福、道德质量有关。因此,一言以蔽之,儒家的黄金律从本质来讲就是,如果我想成为有德之人,我应该帮助别人成为有德之人;进而,如果我不想成为一个恶人,我应该帮助他人不成为恶人。
最有意义的是,孔子在这里用“直”解释“达”的含义。“达”之人也会帮助别人“达”,而“达”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直”。这种对“直”的理解可以帮助我们明白《论语》中两个包含“直”的困难段落,而如果能够正确理解它们,将有助于推进此处讨论的问题。在《论语·宪问》中,有人问孔子:“以德报怨,何如?”“以德报怨”是道家老子(前571—前471)所倡导的观点。【注52】孔子答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以直报怨”究竟如何理解?学术界存在争议,尽管孔子显然不认同老子或耶稣建议人们对待作恶者的态度,即以德报怨。有人把“直”解读为“值”,意思是“价值”,认为孔子所说的是,你应该以一种与怨对等的、大致与你受到的伤害差不多的价值来报答作恶者。【注53】不过,按照大多数学者的看法,孔子教导人们在道德上持中间态度。以怨报怨过于宽容,而以德报怨则过于严苛,中间态度就是以一个人当时真正的感受即直来回报恶行。【注54】
我对这两种解释都持反对态度。【注55】在我看来,孔子所谓“以直报怨”,就是做一些事情以帮助那个给我造成不当伤害的人即不正直的人,使之成为一个正直的人。不妨看一看孔子如何对比“直”和“枉”。他说:“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注56】在同一章中,弟子子夏阐明师意:“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同样,孔子赞扬卫国一位正直的大臣史鱼。史鱼病重,临死前告诉儿子,自己在朝未能说服卫灵公提拔贤臣遽伯玉而斥退佞臣弥子瑕。因此之故,他的葬礼不应该在正堂举行。不久他死了,儿子遵嘱治丧。卫灵公前来吊唁,问为何如此这般,儿子把父亲的遗命告诉了他。卫灵公闻之动容,接受规劝提拔了遽伯玉,罢黜了弥子瑕。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尸谏”故事,而史鱼不仅仅被视作“直己”,而且还“直人”(例子中的卫灵公)。孔子感叹:“直哉史鱼!”【注57】他显然在双重意义上理解“直”【注58】。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直”的独特性:一个正直的人不仅自己正直,而且还使别人正直。孔子说“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注59】,宋人邢昺疏曰:“正人之曲曰直。”孔子的追随者孟子也强调了直的这一特点:“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并认为,一个正直的人会使不正直的人变得正直。【注60】《春秋左氏传》也有正、直连用的表述:“正曲为直。”【注61】
“直”的这一含义,也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论语》中出现“直”的另一章有争议的文字。这章记录了叶公和孔子之间的对话。叶公对孔子说:“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没有表扬那个人,而是回应道:“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注62】这一章是《论语》解经史上的一大疑案,在过去十几年里还成为中国学者争论的一大焦点。争论双方都认为,这段文字把人们带入“孝道”和“社会正义”的两难困境。其中一方为孔子将孝道放在社会正义前面辩护,另一方则批评孔子没有把社会正义放在孝道前面。我曾经主张,争论双方都不对。【注63】理解这一章的关键也是“直”。人们已经看到,“直”意味着正枉、正曲。在该章中,父亲偷了邻居的羊,这一事实表明他是不正直的。一个正直的儿子应当使他不正直的父亲为人正直。问题在于,儿子不透露他父亲的偷窃行为,在何种意义上有利于父亲变正直。孔子只是说,正直在于儿子的隐,而不是他的隐本身是正直的。
孔子为人们提供了一条线索。他说:“事父母,几谏。”【注64】当父母做了不道德的事,一个人应该和颜悦色、轻声细语地规劝。这句话意味深长。首先,如果父母做了不道德的事情,儿女们不应该只是袖手旁观,当然更不应该跟着行不善。相反,他们应该规劝父母不行不善;如果为时已晚,就要敦促父母纠正这种情况。因此,如果父亲偷了一只羊,一个正直的儿子就应该劝说他加以纠正。这表明,孔子在该章中并没有提倡以社会正义为代价行孝道。其次,劝说父母不做坏事,在这里被视为一种“侍奉”父母的方式。换句话说,规劝是行孝的子女应该做的一件重要的事情。遵行孝道并非一味服从父母。例如,孔子的弟子子贡问孔子,是否服从父母即是孝,正如臣下服从君王即是忠。孔子回答道:“鄙哉赐,汝不识也。昔者明王万乘之国,有争臣七人,则主无过举;有争臣五人,则社稷不危也;有争臣三人,则禄位不替;父有争子,不陷无礼;士有争友,不行不义。故子从父命,奚讵为孝?臣从君命,奚讵为贞?”【注65】类似的文字也见于《荀子·子道》。这表明,孔子并不以孝道为代价促进社会正义。以上两点合而表明,对孔子来说,孝与社会正义之间并不存在两难困境。再次,要想规劝成功,就必须温和地进行。其原因在于,如果父母将要做或已经做了某些不道德的事情,这说明父母不是有德之人,所以责骂他们当然不会让他们意识到错误,从而克服自己的恶习。如果父亲偷了一只羊,儿子向公共机关报告,父亲肯定会生儿子的气,他也不可能听从儿子的规劝。因此,在我们一直在讨论的这段文字中,孔子说一个行孝的儿子不应该透露父亲偷了羊(这并不意味着掩盖事实或妨碍公共机关调查它),这是为了创建一个可以更有效地纠正他父亲恶德的良好环境,而这恰恰是“直”的含义:使不正直的人变得正直。【注66】
按照儒家的“关于美德之正义”(即平等分配美德的正义)的要求,人们不是要奖善惩恶,而是应该帮助恶人克服他们的恶习从而使他们变成有德之人,正如按照正义的要求,人们不是要奖励健康的人而惩罚病人,而是应该帮助病人克服疾病变得健康。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应该对违法者作宽大处理或原谅他们的错误行为。【注67】儒家认为,如果有恶人,人们不应该指责他们未能成为有德之人,而是努力帮助他们祛恶。如果他们依然行恶,那么,人们应该反省自己,看看在努力帮助他们时是否有做得不当的地方,看看如何提高自己以帮助他们。【注68】然而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儒家坚持认为,不能让恶人继续行恶,因为他们缺乏美德而别人却拥有美德就是不公平或不正义,就像有人健康而有人生病乏人照顾就是不公平或不正义。
四、儒家如何不同于亚里士多德主义者
儒家“关于美德之正义”的核心在于,具有正义这种美德的道德主体——无论是个人还是政府,都应该把培养人们的美德作为自己的目标。然而,这听起来与桑德尔的亚里士多德式的正义并无多大差异。桑德尔指出:“对于亚里士多德而言,政治的目的并不在于建立一套中立于各种目的的权利框架,而是要塑造好公民,培育好质量。”他还引用亚里士多德的名言来支持自己的观点:“任何一个真正的城邦,而不仅仅是名义上的城邦,必须致力于促进善这一目的。否则,一个政治机构就沦为一个单纯的联盟……而不是它应当成为的那种能使城邦的成员变得良善和正义的生活规则。”【注69】因此,我相信桑德尔也会接受儒家的“关于美德之正义”。不过,儒家的关于美德之正义观与桑德尔的亚里士多德主义的依据美德之正义观还是有一些细微但又很重要的差别;事实上,正因为感受到这些差别,我才认为儒家对后者会有一些保留意见。
首先,尽管儒家和亚里士多德都认为应该让有德之人担任政治职务,但他们这样做的理由至少不尽相同。桑德尔强调,这些职位的存在是为了认可、奖励和尊敬有道德的人。这一点在他运用亚里士多德关于如何分配最好的长笛的例子中可以看得最为清楚。人们可能会同意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应当把最好的长笛分配给最好的长笛演奏者。但“原因何在?”桑德尔自问自答:“嗯,你可能会说,因为最好的音乐家能演奏好长笛,创造人人都喜欢的音乐。这是一个功利主义的理由。但并不是亚里士多德的理由。他认为,最好的长笛应当给予最优秀的长笛演奏者,因为这是长笛的目的——被很好地演奏。长笛的目的在于产生动听的音乐,那些能够最佳地实现这一目的的人应当拥有最好的长笛。”【注70】把最好的长笛给最佳演奏者,同样,把最有影响力的职位给最有德的人,桑德尔区分了功利主义的理由和亚里士多德的理由。就此而言,我认为儒家会采取功利主义的理由:【注71】让有德之人担任政治职务的理由不是奖励、尊重或认可他们,而仅仅因为担任这些职位能够使他们更好地发挥其使别人有德的作用。无论如何,有德之人之所以有德,不是因为他们要寻求认可、奖励或尊重。这些东西即便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也是外在的东西,是庸俗的自爱者追求的东西,而真正的自爱者愿意在必要时牺牲这些外在的东西,因为他们所关心的是属于他们内在幸福的自身的美德。
其次,关于身居政治职位者使人有德的方式,儒家可能也不同意包括桑德尔在内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者的观点。亚里士多德认为,论辩不会起作用,多数人“按其本性所听从的都不是羞耻感而是恐惧。他们不去做坏事不是由于这些坏事卑鄙,而是因为他们惧怕惩罚”。【注72】因此,政治领袖通过制定法律来完成他们使人有德的工作。他指出:“如果不让其在健全的法律下成长,就很难有正确的方式让一个年轻人变得有美德。因为过节制的、忍耐的生活并不快乐。所以,他们的教养和职业要在法律指导下进行。……因为多数人服从的是法律而不是论证,是惩罚而不是高尚感。”【注73】桑德尔似乎同意亚里士多德的看法,他抱怨说:“对于自由社会中的许多公民来说,道德法律化这一观念是令人厌恶的,因为它陷入缺乏容忍和强迫的危险。”他紧接着说:“然而,正义社会认可某些美德以及完满生活的观念……在意识形态领域中激发了许多政治运动和争论。”【注74】在另一个地方,桑德尔问道:“一个正义的社会谋求推进其公民的美德吗?或者,法律是否应该中立于各种不同的美德观念?”【注75】其言外之意,公民的美德可以(如果不是仅仅)通过法律得到提升。
我们已经看到,儒家同意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观点,认为使人民有德是政府的重要职能;他们也同意,这种工作不能纯粹由论辩来完成。然而,通过立法和实施惩罚性法律使人民有德,这样的观点与儒家格格不入。孔子在《论语·为政》中有句名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一段落的前半部分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截然相反,而我认为孔子显然是对的。惩罚性的法律不管多么严厉,或许可能阻止人们去做不道德的事情,但却不能使恶人成为有德之人,因为,亚里士多德自己也讲,他们“不去做坏事不是出于羞耻,而是因为惧怕惩罚”【注76】。所以,当确信他们的行为不会被发觉并由此不会被惩罚,他们就不会不去做坏事;而且,当他们控制自己不去做非常愿意做的事(坏事),或者尝试去做他们不乐意做的事情(好事),他们还将不得不经历内心的挣扎。这当然不利于他们成为有德之人。在该段落的后半部分,孔子建议改用礼仪规范和美德使人有德。礼仪规范不同于惩罚性的法律。如果人们违反这些规则,不会受到惩罚,但会被人看不起,因而感到羞愧。而所谓德治,孔子指的是政治领袖的典范德行。【注77】
由此引出儒家和亚里士多德主义之间的第三点差异。二者都认为政府具有使人有德的功能,而且那些担任政治职务的人应该拥有美德。不过,这些政治官员究竟应该拥有哪些相关美德,二者的看法并不一样。亚里士多德强调立法者对于制定能阻止人们做坏事的惩罚性法律的重要性。这样的法律,或许不仅能阻止人们做坏事,还能使人变得有德。但问题在于,哪种人有资格成为立法者。换言之,人们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美德才能被这样的政治职位所认可、奖赏和尊重呢?有意思的是,亚里士多德拿医生作模拟。假设你的孩子生病了。一方面,作为父母,你知道很多关于孩子的细节。另一方面,有一位医生,他从没见过你的孩子。你会自己设法治好你的孩子,还是去看医生?当然是后者。为什么?因为医生“具有一般性的知识,懂得对于每个人或某类人什么是好的”。【注78】一个人成为一名能够治病的医生,不是因为医生本人是健康的或者至少没有病人所患的疾病,而是因为医生拥有治疗疾病的相关知识和技能。同样,亚里士多德认为,要使一个孩子有德,是立法者而非父母的工作。立法者可以发挥这样的作用,除了他们是立法者这样简单的事实而具有的权威之外,还因为他们拥有立法的知识和专业技能,能够让所立之法有效地达到预期的目标,而不仅仅因为他们拥有他们想使人们拥有的美德——因为其他很多人也拥有这样的美德。事实上,我们可以把亚里士多德的模拟往前推进一步(这样做,应该是合理的):立法者通过制定法律来训练人们具有美德,而他们是否具有这样的美德并不重要。医生可以治病人的病,不是因为他自己没有病,而是因为他有相应的知识和技能。如果没有这样的知识和技能,无论医生多么健康,他都无法治疗病人的病;有了这样的知识和技能,即使他自己有同样的病,仍然可以治愈病人。同样,即使一个人没有政府希望其人民拥有的美德,只要这个人有足够的知识和技能,了解什么法律可以使人有德,这个人仍然有资格成为一名立法者。
对孔子来说,使人们变成有德之士的,并非政府所制定的法律,而是那些拥有政治职位的人透过其行为所表现出来的典范性美德;政治领袖必须具有他们努力使人民具有的美德。这可以在《论语》中找到许多根据。孔子对政治统治者的建议一再强调有德的重要性。例如,他说:“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注79】其中,“政”是“正”的同源词。又如,季康子问政,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季康子进一步问,是否要杀不循道的人,孔子答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注80】在孔子看来,统治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注81】;“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注82】。《孔子家语·王言解》中有一大段文字把这一点说得很清楚:“上敬老则下益孝,上尊齿则下益悌,上乐施则下益宽,上亲贤则下择友,上好德则下不隐,上恶贪则下耻争,上廉让则下耻节,此之谓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凡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则何物不正?”
总之,孔子认为政治领袖应该具备的美德恰恰是他们希望人民拥有的美德。例如,如果想让人民“诚”,他们必须首先有诚的美德;如果希望人民“仁”,他们必须首先有仁的美德;如果想让人民“义”,他们必须首先有义的美德。【注83】相比之下,按照桑德尔的亚里士多德主义,政治职位的目的是尊重、认可和奖赏人们,因为他们拥有制定、执行和宣布可以使人民有德(例如,诚实、仁慈、正义)的法律的美德或技能和能力。有时候桑德尔称这种美德为公民美德【注84】。不过,我认为他将治理国家称为“灵魂塑造”时描述得更为准确【注85】。有人也许会为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辩护说,既然政治领袖的工作是使人有德,那么在理想状态下,只要他们能对灵魂进行有效的塑造就够了,但他们自己不一定要有德。就像一家汽车公司的首席执行官(CEO),不需要任何制造汽车零部件或把不同部件组装成整车的知识或能力。他只要具备管理不同的人以最有效的方式去做不同的事情的知识、技能和能力就够了。【注86】这种对亚里士多德的辩护,没有注意到道德教育和管理与非道德事情的训练之间存在重要区别。如果有人教我打篮球,我唯一关心的是他能否教我把篮球打得更好;至于他自己篮球打得好不好,我并不关心。然而,如果有人教我诚、仁、义,而他自己却不诚、不仁、不义,那么,如果我还没做到诚、仁、义,那我就不太可能认为它们是我应该拥有的美德。
比照儒家“关于美德之正义”与桑德尔亚里士多德式的“依据美德之正义”,我们最后且聚焦在它们各自对于矫正之正义的看法。先从以下问题开始:一个善恶之人共存的社会为了实现正义应该做什么?关于这个问题,前面已经从儒家的角度提出了“关于美德之正义”的独特概念。并且把善/恶与健康/疾病相模拟,认为某些人比其他人更有美德是不正义的,一个正义的社会应该重新分配这些美德,从而使人人都能平等地(和最大化地)具有美德。有趣的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儒家的关于美德之正义也可以视为矫正之正义:不具有美德的人或恶人在此被视为有道德缺陷的人,他们类似于有身体缺陷的人。把美德分配给他们,也就是使他们有德,这在本质上是对他们进行矫正。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孔子与亚里士多德之间的第四点差异。这也是我要讨论的最后一种差异。
亚里士多德认为不正义本身就是不平等,矫正之正义旨在恢复原有的(有比例的)平等。例如,假设张三和李四之间原本是有比例地平等的,现在如果张三从李四处偷了东西,张三就会得到李四失去的东西,从而导致不平等。矫正之正义要求,张三把所得的东西归还李四以恢复最初的平等。同样,如果“一方打了人,另一方挨了打,或者一方杀了人,另一方被杀了,做这个行为同承受这个行为两者之间就不平等……法官就要通过法律的惩罚来达到平衡,要剥夺行为者的所得”【注87】,如此一来,平等又回来了。显然,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就是现在所谓矫正正义的“报应”(retributive)理论【88】。这一理论与功利主义理论形成对比。报应理论是向后看的:恢复被不正义行为所扰乱的最初的平等;功利主义理论则是向前看的:防止将来发生不正义的行为。为了实现这一功利的目标,仅仅恢复原来的平等还不够;有必要要求在不正义的交易中已经有所获得的当事人,也就是那个不道德的人、罪犯,放弃比他所得更多的东西,这样才会阻止他及其他潜在的不道德的人和罪犯将来再做出同样的行为。
众所周知,这两种理论各有利弊。报应理论不能可靠地防止将来同一个人或其他人继续发生不正义行为,而这正是功利主义理论的长处。然而,功利主义理论也难以证明,为什么我们可以迫使一个已做了一个不正义行为的人,不仅放弃他不应得到的东西,而且还要被用作工具,放弃比所得更多的东西,从而阻止他自己将来再犯同样的错——更成问题的是,阻止其他人将来犯同样的错。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儒家“关于美德之正义”的意义。作为一种矫正理论,这种儒家的观点既非报应性的也非功利性的,而是还原性的、恢复性的或治疗性的。【注89】这一观点的最为独特之处在于,虽然它也旨在矫正,但它要矫正的是不正义行为的根源,即不道德的主体,而大家熟悉的两种理论的矫正对象则是不正义行为的结果。这种儒家的矫正之正义优于报应理论和功利主义。矫正不道德的主体,也就是说,治愈其疾病,恢复其内在健康。如果做到这一点,一方面,他不仅不会再做出同样的不道德行为,而且会成为其他可能犯下同样不道德行为的人的道德楷模。这样一来,我们不使用功利主义的手段就可以达到功利主义的目标。另一方面,如果不道德的主体治好疾病,恢复道德健康,从而成为道德的主体,那么,他们自然会放弃他们不应得的东西,把它们归还受害者。如果不能恢复受害者的损失(例如,如果他们不道德的行为造成受害者失去身体的某些部分甚至生命),他们也会努力作一些适当的补偿,同时也会为不道德的行为感到自责、内疚和遗憾。因此,这样一来,我们不使用报应论的手段就可以达到报应论的目标。
结语
通过着重探讨桑德尔的新亚里士多德主义正义理论的两个主要特点,即“作为美德之正义”和“依据美德之正义”,本文提供了解读这一理论的一种儒家视角。为了进行比较,同时展示儒家思想对当代正义话语的潜在贡献,我尽量突出儒家思想和亚里士多德主义之间的差异,而不是它们的相似之处。不过,尽管在台湾和香港仍有一些深受牟宗三先生(他可能是最具影响力的当代儒家了)影响的学者尤其是儒家学者,认为儒家在康德的道德哲学框架内可以得到更好的解读,但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包括我自己在内,认为儒家与亚里士多德哲学最为契合。因此之故,我完全有可能在本文中夸大了他们的分歧。所以,如果我误解了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尤其是桑德尔所理解的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和儒家的观点其实完全一致,那么我也会完全接受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注90】如果二者之间仍有一些差异,那么,我将站在儒家一边,不是因为我是挂牌的儒者(我不是),而是因为本文所给出的理由,除非有朝一日我被相反的理由所说服。
注释:
注1:Michael J.Sandel,“[Distinguished Lecture on]Justice: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Boston University Law Review 91(2011):1303.
注2:Michael J.Sandel,Liberalism and the Limits of Justic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34.
注3:Michael J.Sandel,Public Philosophy:Essays on Morality in Politics(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5),28.
注4:Michael J.Sandel,Justice: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x,2009),186.
注5:尽管这是两种不同的目的论,但是,我们必须以一种适当的方式把二者联系起来。与特定社会实践相关的目的论必须服从于与人类目的相关的目的论,因为首先是后者决定一个特定的社会实践是否应存在。否则,我们都可以分配窃贼团伙的领导权了(既然窃贼团伙的目的是偷盗,就可以奖励、尊敬和承认与此目的相关的品格)。克劳特(Richard Kraut)说得很好:“亚里士多德认为……,诚然,功绩(merit)是解决特定问题的基础,但是,究竟应该把何种功绩纳入考虑则须参考整个共同体的共同善……一种分配物品(goods)的制度之正义涉及两个方面:首先,制度必须有助于共同善;其次,分配所根据的功绩标准必须从所要达到的共同善来看是适当的。如果一种制度破坏了共同体的福祉,那么它就不符合正义的目标,即使它成功地按照它所使用的功绩标准来分配物品”(Kraut 2002:147)。
注6:桑德尔用的案例大都是关于奖励善而非惩罚恶,不过他确实说过,“我们认为,那种趁火打劫的行为应当受到惩罚而非奖赏”(Michael J.Sandel,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9)。
注7:Michael J.Sandel,Justice 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10.
注8:Michael J.Sandel,Justice 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14.尽管桑德尔认为,那些高管得到政府救助资金不是因为他们的贪婪,而是因为他们的失败。
注9:正是在此意义上,帕克洛克(Michael Pakaluk)指出:“英语中的‘正义’一词意味着:(1)正义的事态,即一种安排或状况是正义的……(2)采取行动的意图……或(3)品格或美德状态,它引导某人带着正义的意图瞄准正义的事态。在希腊语中有不同的字对应这三种不同的含义。”(Pakaluk 2005:200)
注10:John Rawls,A Theory of Justice(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3.
注11:Mark LeBar,“The Virtue of Justice Revisited”,In The Handbook of Virtue Ethics,edited by Stan van Hooft.(Bristol,CT:Acumen,2014),270-271.
注12:桑德尔似乎赞同这一观点,因为他曾说,“为了实现一个正义的社会,我们必须一起思考完满生活的意义,并创造一种对不免产生的分歧持友好态度的公共文化”(Sandel,“[Distinguished Lecture on]Justice: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1310)。
注13:当然,也可以说,既然罗尔斯把原初状态设计为一种能够衍生出正义原则的程序,那么,罗尔斯作为这个状态的设计者的正义的美德就反映或表达在他的正义原则之中了。不过,罗尔斯显然并没有在此基础上论证他的观点。
注14:John Rawls,A Theory of Justice,398.
注15:Mark LeBar,“The Virtue of Justice Revisited”,274.
注16:Mark LeBar,“The Virtue of Justice Revisited”,272.
注17:Michael Slote,Moral Sentimentali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125.
注18:《孟子·离娄上》。
注19:《孟子·公孙丑上》。
注20:Michael Slote,Moral Sentimentali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126.
注21:Michael Slote,Moral Sentimentali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126.
注22:Aristotle,“Ethica Nicomachean Ethics”,The Works of Aristotle 9(1963):1105a28-35.
注23:Aristotle,“Ethica Nicomachean Ethics”,The Works of Aristotle 9(1963):1105b5-8.
注24:《孟子·离娄下》。
注25:G.A.Cohen,If You’re an Egalitarian,How Come You’re So Rich?(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Chapter 8.
注26:本节中的论证,利用了法律和个人行为之间的模拟。正如正义的行为反映并体现了行为者的正义这种美德,正义的法律表达并反映了立法者的正义这种美德。不过,有一不相似之处:正义的行为源自个人,而正义的法律源自一群人,即立法者。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在何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谈论一群人的美德,即所谓的集体美德或制度美德。这一问题无法在本文展开讨论。关于该话题的一些有意义的讨论,可参见Byerly 2016,Gregory 2015,Fricker 2010,Sandin 2007,Ziv 2012。
注27:例如,桑德尔提出以下问题:依据美德之正义是否只适用于荣誉而不适用于繁荣的成果?他接着指出,“争论经济安排的是非曲直经常把我们带回到亚里士多德的问题,即人们在道德上应得的是什么,以及为何如此”(Michael J.Sandel,Justice: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13);然后,他立即掉头讨论上文提到的政府救市问题。
注28:Michael J.Sandel,Justice: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192.凯伊特也有类似的观点:“对亚里士多德而言,分配正义首先关心政治权威的分配……其次才是财富分配”〔David Keyt,“Distributive Justice in Aristotle’s Ethics and Politics”,Topoi 4(1985):24〕;克劳特也说:“正义的首要问题,他(亚里士多德)认为是:谁应该拥有权力”;正因为此,亚里士多德“忽略了一点,有时候分配不是基于功绩,而是基于其他某个标准。如果食物和其他资源可供分配给需要的人,那么正义则要求把更多的钱给予那些有更大需求的人”〔Richard Kraut,Aristotle:Political Philosophy(Oxford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147,146〕。
注29:Michael J.Sandel,Justice: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153-166.
注30:Michael J.Sandel,Justice: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178.
注31:Michael J.Sandel,Justice: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179.
注32:Michael J.Sandel,Justice: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178.
注33:一般认为,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讨论了两种特殊的正义,即分配正义和矫正正义。与此不同,斯旺森(Judith A.Swanson)认为,亚里士多德“承认三种(正义):分配、经济和惩罚(正义)。政府关心分配正义,因为它分配职位和荣誉、权利和特权”〔Judith A.Swanson,“Michael J.Sandel’s Justice: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A Response of Moral Reasoning in Kind,with Analysis of Aristotle’s Examples.”Boston University Law Review 91(2011):1377〕。虽然斯旺森不同意桑德尔和凯伊特等人,主张经济正义是亚里士多德的核心关注,但她也主张,亚里士多德的经济正义原则不同于他的分配正义原则和惩罚正义原则。
注34:既然儒家的“关于美德之正义”观念旨在替代桑德尔的“依据美德之正义”,它同样与经济利益的分配无关。
注35:《孟子·公孙丑上》。
注36:《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第2卷,第80页。
注37:《孟子·告子上》。
注38:Aristotle,Ethica Nicomachean Ethics,1105 b,第四章末尾。
注39:Aristotle,Ethica Nicomachean Ethics,1129 a.
注40:Aristotle,Ethica Nicomachean Ethics,1169 a..
注41:《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第2卷,第68页。
注42:Aristotle,Ethica Nicomachean Ethics,1179 b5-515.
注43:Aristotle,Ethica Nicomachean Ethics,1105 b21-23.
注44:Aristotle,Ethica Nicomachean Ethics,1180 a8.
注45:《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第17卷,第599页。
注46:John Rawls,A Theory of Justice,89.
注47:在儒家那里,修己和立人往往共同起作用,甚至密不可分。就此而言,斯洛特-加龙省的以下观点为是:修己是不充分的;而他的以下观点则非:儒家仅仅着眼于修己。他的后一观点来自他对杜维明与艾文贺的解读,他们都认为儒家以道德自修为核心〔Michael Slote,“Moral Self-cultivation East and West:A Critique”,Journal of Moral Education 2(2016):192-206〕。
注48:Huang Yong,“The Self-centeredness Objection to Virtue Ethics:Zhu Xi’s Neo-Confucian Response”,American Catholic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84(2010):651-692.
注49:《论语·雍也》。
注50:《论语·为政》。
注51:《论语·颜渊》。
注52:《道德经》,第63章。
注53: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第62页。
注54:李泽厚:《〈论语〉今读》(香港:天地图书公司,1999),第346页。
注55:Huang Yong,Confucius:A Guide for the Perplexed(London:Bloomsbury,2013),38-39.
注56:《论语·颜渊》。
注57:《论语·卫灵公》。
注58:其他文献记载孔子如是说:“古之列谏者,死则已矣,未有若史鱼死而尸谏,忠感其君者也,不可谓直乎?”〔《孔子家语·困誓》(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
注59:《论语·阳货》。
注60:《孟子·滕文公下》。
注61:《左传》(北京:中华书局,2007)襄公七年。
注62:《论语·子路》。
注63:Huang Yong,Confucius:A Guide for the Perplexed,139-143.
注64:《论语·子路》。
注65:《孔子家语·三恕》。
注66:黄勇:“正曲为直:《论语》‘亲亲相隐章’新解”,《南国学术》3(2016):366—377。
注67:我要感谢德莱弗(Julia Driver),她的一个评论促使我想到了这个问题。
注68:只有置于这样的脉络之中,《论语》中的某些章节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比如,“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论语·卫灵公》);“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攻其恶,无攻人之恶“(《论语·颜渊》);“乐道人之善”(《论语·季氏》),“恶称人之恶者”(《论语·阳货》)。在所有这些段落中,孔子不是说,我们自己有德就够了,不需要做任何事情让别人成为有德之人。相反,孔子是说,如果别人无德,我们就要责备自己,正如孔子所引的那句据说出自周武王的话:“百姓有过,在予一人。”(《论语·尧曰》)。
注69:Michael J.Sandel,Justice: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193.至少根据辛加诺的解释,这一意义上的关于美德之正义对亚里士多德来说其实并不完全陌生,而在我看来,辛加诺的解释是有道理的。因为对于亚里士多德,正义即平等,辛加诺认为亚里士多德对何为平等的回答是美德,而“道德美德是正确制度中正义的衡量标准。为了让正义行于整个城邦,城邦必须为公民提供休闲及其他前提条件”(Marco Zingano,“Natural,Ethical,and Political Justice.”,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Aristotle’s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209-210)。他援引亚里士多德为证:“无论是对于个体还是城邦,最好的生活是一种美德生活,同时配有参加美德活动所需的充分资源”(Politics VII 1,1323b40-24a2;Zingano 2013:209)。
注70:Michael J.Sandel,Justice: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18.桑德尔在其他地方提出更具包容性的主张。例如,他说,有德之人“应该拥有最高的职位和荣誉,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会制定明智的政策,使每个人都生活得更好。也是因为政治共同体的存在,它至少部分地是为了尊重和回报公民的美德”(195;黑体为笔者所加)。
注71:也许,它与其说是功利主义的,不如说是后果论甚至目的论的,因为儒家的目的在于追求最佳后果或目的:使尽可能多的人成为有德之人。显然,儒家总体上属于美德伦理,而后果论只在其美德伦理的总框架内发挥作用,而美德伦理的总框架是目的论的而非后果论的。
注72:Aristotle,Ethica Nicomachean Ethics,1179 b5-10.
注73:Aristotle,Ethica Nicomachean Ethics,1179 b31-1180 a4.
注74:Michael J.Sandel,Justice: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20.
注75:Michael J.Sandel,Justice: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9.
注76:Aristotle,Ethica Nicomachean Ethics,1179 b10.
注77:当然,这并不是儒家道德教育仅有的两种方式。在别处,孔子提到了其他措施。例如,他也说道德发展“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季伯》)。此处,除了礼仪规范之外,孔子还提到了诗和乐,二者皆属于情感教育。除此之外,孔子并不是绝对反对惩罚性法律,因为他意识到有时惩罚性法律是必要的。然而,他认为,在理想情况下,这种法律仅仅是在场的,而不是被运用;当确实需要运用它们时,它们只是临时起到补充作用。无论是在不得不运用这种法律手段之前或之后,都必须要用其他道德教育手段。
注78:Aristotle,Ethica Nicomachean Ethics,1180 b13-15.
注79:《论语·子路》。
注80:《论语·颜渊》。
注81:《论语·子路》。
注82:《论语·为政》。
注83: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儒家认为道德美德是政治领袖所必须拥有的唯一东西。除了使人民变得有德之外,政府的目标还促进社会正义,特别是正义地分配经济利益,这就要求政治领袖具备相关的专门知识。当然,在儒家看来,道德美德对政治领袖来说不仅是必要的和最重要的,而且它自然会引导政治领袖探寻能够正义而有效地治理社会的专门知识。
注84:Michael J.Sandel,Justice: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194.
注85:Michael J.Sandel,Democracy and Its Discontents:America in Search of a Public Philosophy,326.
注86:感谢德莱弗(Julia Driver),她的评论促使我想到了这个问题。
注87:Aristotle,Ethica Nicomachean Ethics,1132 a7-9.
注88:因此,他说:“人们总是寻求以恶报恶,若不能,他们便觉得自己处于奴隶地位。人们也寻求以善报善,若不然,交易就不会发生,而正是交易才把人们联系到一起。”(1132b34-1133a2)
注89:应当指出,不言自明的是,我们的意思不同于与桑德尔的刑事正义治疗理论。在桑德尔那里,治疗诉讼“把惩罚看作是受害者的一种安慰,一种畅快的表达,一种终结。如果惩罚是考虑到受害者的利益,那么受害者在决定罪犯该受何种惩罚时就有发言权”(Michael J.Sandel,Public Philosophy:Essays on Morality in Politics,106)。简言之,在桑德尔那里,接受治疗的人是受害者;而在孔子那里,接受治疗的人是加害者。
注90:这是完全可能的,桑德尔有时也会提出类似的主张。例如,他在讨论一位受欢迎的新生拉拉队队长斯马特(Callie Smartt)的事例时说:“在选择自己的拉拉队队长时,高中学校……表达了它希望学生们去钦佩和效仿的质量。”(Michael J.Sandel,Justice: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186;黑体为引者所加。)他还把亚里士多德对于正义的进路描述为“分配物品以奖励和促进美德”(Michael J.Sandel,Justice: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108;黑体为引者所加)。因此,当桑德尔说分配政治职位以尊重、奖励和认可相关的美德,我们应该将之更好地理解为,他是在说,经由分配促进相关美德,需要通过尊重、认可和奖励那些拥有相关美德的人,这样别人就会效仿他们。如果是这样,我们可以说,桑德尔的观点和儒家的观点完全相同。然而,即便如此(似乎如此),我们也不能忽视它们之间的一些细微差别。一方面,按照桑德尔的理论,其他人会效仿有德之人,因为有德之人得到了政治职位这样的奖品。如果他们对这样的政治职位不感兴趣,他们就会缺乏效仿有德之人的动机。而按照儒家理论,有德之人应该掌管政治职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典范行为可以更好、更广泛地为普通百姓所效仿。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回答一个问题:这些政治领袖要具备什么样的相关美德?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桑德尔的亚里士多德模型中,因为这些政治职位所要奖励、承认和尊重的美德,是那些与立法者相关的美德,它们也必须是政府促进和鼓励人们去效仿的美德。但是,考虑到任何社会在任何时候都只需要少数人来制定法律,每一个公民真的都需要有这样的美德吗?相形之下,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儒家模式中,政治领袖应该具有的美德和他们想让普通人拥有的美德乃是道德美德。无论是政治领袖还是普通人,为了成为一个健康的或没有缺陷的人,都必须具备这样的道德美德。
作者注:2016年3月,本文初稿在华东师范大学举办的“桑德尔与中国哲学国际会议”(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andel and Chinese Philosophy)上宣读。会上,桑德尔教授提出了富有挑战性的问题和评论,这使我的论文修改受益良多。2016年8月,在湖北大学举办的“国际美德伦理高端论坛”上,德莱弗(Julia Driver)教授在评议拙文时提出了一些有意义的问题,我的有关思考现已融入到定稿之中。斯洛特教授出席了后一次会议,本文(尤其是第二节讨论其观点的部分)也受益于与他的交谈。同时,本文亦感谢李晨阳教授的评论。该文的英文稿2018年将发表于Encountering China:Michael Sandel and Chinese Philosophy(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8),Edited by Michael J.Sandel,Paul J.D'Ambrosio;Foreword by Evan Osnos.经原编者、作者和哈佛大学出版社授权,在《南国学术》先行刊出中文稿,由华东政法大学校报编辑崔雅琴翻译。
相关链接
责任编辑:姚远
【上一篇】【桑德尔】亚里士多德、孔子与道德教育——对黄勇教授的回应
【下一篇】儒家网2017年度十大好书揭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