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斯提卡·布拉达坦】乔治·贝克莱:主教、怪杰、和经验主义者
乔治·贝克莱:主教、怪杰、和经验主义者
作者:科斯提卡·布拉达坦 著;吴万伟
来源:译者授权儒家网发布
本文探讨爱尔兰最著名哲学家深刻的唯灵论。
汤姆·琼斯《乔治·贝克莱的哲学人生》,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图片文字:苏格兰裔美国画家约翰·斯米伯特(John Smibert)1728年的作品“百慕大小组”(贝克莱主教及其随从)的细节,右边站立者为乔治·贝克莱(George Berkeley)。
贝克莱主教拥有哲学家中也很罕见的天赋:真正的怪异性。在提到其物质不存在的主张(其形而上学的基石)时,他的更明白事理的同代人之一的确说过那是“进入任何古代或现代狂人脑子里的最无法容忍的怪念头”。因为通常的养育方式和需要获得社会的认可,也因为被单独挑出来清除掉的原始恐惧,我们很少有人喜欢持有完全离经叛道的新颖观点。遭遇全新的观点往往令人不知所措、怒火中烧、甚至生活体验统统被彻底颠覆。相比之下,随波逐流往往更安全,报酬也更丰厚。坚持熟悉的东西往往增加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持续存在和繁荣的机会。难怪在任何社会,真正的怪人都是濒临生存危机的珍稀物种。
但是,我们根本离不开这些怪异性。只要活着,我们就有一种将生存程序化和模式化的倾向,那是我们精神死亡的方式。怪异者是裂缝,新生活通过这些裂缝闯入我们这个僵化观点盛行的世界。先知、宗教创始人、政治眼光卓越者、社会改革家和伟大艺术家都在进行“怪异化”(weirdification)这个世界的事业。这些令人紧张不安的怪杰让历史变得更加充满活力,让生活变得更容易。
乔治·贝克莱可能是爱尔兰最著名的哲学家了。他出生于1685年,在都柏林三一学院求学和教书。在伦敦和欧洲大陆以及北美洲呆了一段时间之后,选定牧师职业安定下来,担任爱尔兰克洛因(Cloyne)教区的主教,直到他1753年去世之前不久才从这个职位上退下来。在哲学问题上,贝克莱拥有很多非传统的观点。在很多人看来,规范性的假设是我们的周围环绕着外部世界,我们通过自己的感知来认识这个世界。而贝克莱则将其完全颠倒过来。他认为,感知本身(卓越心灵的行为)是现实的根本方面,它们之外根本没有物质世界。他写到,“存在就是被感知”(拉丁语就是esse est percipi)。贝克莱问到,就拿“房子、大山、河流”为例,它们是“我们感官感知的东西和我们依靠观念或感觉来认识到的东西”,除此之外,还能是什么?引发这些感知体验的是上帝而不是外部世界。因此,对象的存在是上帝心灵和我们心灵共同操作的结果,根本没有什么物质现实。
贝克莱不仅否认物质世界的存在,他还相信我们生活在上帝之中:他喜欢宣称,“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请参阅:《使徒行传》17章28节(《圣经:简化字现代标点和合本》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2001年,第241页。——译注)。在其早期(影响最大的)书,如《人类知识原理》(1710)和《海拉司和费罗诺斯的三大对话》(1713)等专著中,他论证说,上帝通过我们周围看到的东西持续“对我们说话”;在他看来,能够看见的整个世界不过是物化了的神圣话语。在“启蒙”时代,贝克莱兴致极高地沉浸在深奥的、神秘的、炼金术般的设想中。在其最后一本主要著作《西里斯》(Siris)(1744)中,他提出一种焦油水形式的灵丹妙药(炼金术士的古老梦想)建议,令同代人大为震惊。他是热衷莫尔,热衷乌托邦的人,希望在百慕大创建教育上的理想世界。贝克莱从来没有踏足那里,根本不知道现实中的种种不方便,他相信此地乃“尘世天堂”,不仅是基督教和西方的未来,而且是整个人类的未来。学生们能在那里长大,必要时可采取强制措施,因为这样做对他们有好处。切断与人类社会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的联系,摆脱尘世的所有诱惑安全无虞,贝克莱及其乌托邦同行者来追求一种专心学习、修炼美德和虔诚信仰的生活。18世纪的时候,人们很难想到比这更怪异的想法了。
这种复杂人物在当今时代恐怕很难生存下来。与成功改变人类叙事方式的其他伟大怪杰(想想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德国哲学家尼采、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法国女哲学家西蒙娜·韦伊(Simone Weil)不同,贝克莱最终只是说服了少数人接受了他的世界观。当今哲学经典中的贝克莱,学校中讲授和学术期刊上讨论的“经验主义者”对“语言哲学”和“认识论”(他并不了解这些时髦的术语)做出了某些贡献,提出了有关感知、抽象与数字、首要特征和次要特征等方面的观点,这些已经相当可观了。与贝克莱这个历史人物的丰富性相比,经典作品中的思想家看起来有些滑稽:他已经被戏剧性地驯化、被做了防腐处理,成为没有生机、没有活力、没有味道、没有色彩的人。位于其思想核心的旺盛精神性(连同其柏拉图主义的、基督教的、甚至神秘主义的根源)基本上都被忽略了。鉴于当今主流哲学的无神论敏感性,贝克莱的上帝令人感到尴尬。一些可敬的学者已经在试图证明这个以上帝为核心的哲学即使将上帝因素清除出去仍然能够说得通。不过,这样做就像试图将利奥纳多·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解释成为在讲述公元一世纪巴勒斯坦的餐饮风俗一样滑稽。
这就是汤姆·琼斯的《乔治·贝克莱:哲学人生》有这么多让人喜欢的东西的原因。这本新传记挖掘此人全貌的努力令人印象深刻:贝克莱的作品,无论多么隐蔽,琼斯没有一页不翻动,没有一份弥撒不总结,没有一张不重新认识。他用不辞辛苦获得的细节解释贝克莱的哲学,将其置于更广泛的历史背景下,将其与所有节点连接起来,并得出必要的结论。这是接近于崇拜盲从的辛苦付出。
因为琼斯从内部考察贝克莱的思维方式,将上帝的核心地位作为出发点,他的书显示“从形而上学和神学视角看,这意味着什么。贝克莱相信幸福的人类生活应该有神圣性的充分参与。”这样一种充满同情的途径允许作者在贝克莱的著作和生活之间找到压倒性的一致性。他观察到,神圣性的参与“与贝克莱的多样性活动的目标和作为哲学家和教士做善事的决心是一致的。”应该承认,琼斯这样做是与当时学术研究截然相反的,强调了贝克莱的上帝观无法避免的重要性。在琼斯看来,这个途径不仅是个人信仰问题,而是学术诚信问题。他写到,“贝克莱哲学世界中的上帝具有个人的、现在的、积极的、话语的特征,并非他的很多近期追随者共享的概念或信仰”(我并不属于这个群体)。但是,“必须承认,如果我们要准确地从这位哲学家身上推断出任何东西的话,这个上帝的存在对贝克莱的哲学及其个人事业都必不可少。”在当今理解哲学过去的尝试中,人们或许希望看到更多人采取这样的态度。
虽然同情其传主,但琼斯对于贝克莱的错误和局限性从来没有视而不见。他注意到,贝克莱有一种“扼杀其职业生涯的高超才能。”笼统地说,他的专业记录“显示直接参与人类多样性的活动相对少,”因为这个哲学家“对于不同种类的人的生活差异相对缺乏好奇心。”比如,当他生活在意大利港口城市里窝那(Livorno)时,贝克莱作为英国商人小圈子的圣公会传教士牧师,对该圈子之外的意大利人丰富多彩的生活很少表现出任何兴趣。两个世纪之前,米歇尔德·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曾经对新世界的文化活动(包括最残忍的形式吃人习俗)都表现出浓厚和持久的兴趣,贝克莱即使生活在北美洲时也没有这种爱好。引人注目的是,他是所处时代和地域的产物,他对政治和社会事物的立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当时的社会地位塑造而成的。琼斯注意到,贝克莱“居住在奴役他人实行奴隶制的殖民地,可能还从事在欧洲推广奴隶制的活动。”贝克莱或许是个伟人,但是像很多“伟人”一样,他也常常有低劣、怪异、和令人失望之处。贝克莱对此人及其历史背景做了细腻的、平衡的、和了不起的全面描述,同时还谈及他的哲学及其思想源头、目标和更广泛的应用等。这种里程碑式的著作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里成为研究贝克莱的重要文献。
“怪异者是裂缝,新生活通过这些裂缝闯入我们这个僵化观点盛行的世界。”
但是,人们忍不住感受到贝克莱的怪异性让琼斯有些坐卧不安。琼斯注意到,贝克莱的思想“既高度传统又极其乖僻怪异。”(乖僻怪异似乎是琼斯表达“选择”时使用的委婉语)他注意到“主要著作《西里斯》里呈现的观点似乎极其乖僻怪异,谈及贝克莱的“乖僻怪异习性”以及他处理某些哲学问题的“乖僻怪异”做法。在揭露了贝克莱的乖僻怪异性之后,琼斯似乎并不十分清楚该怎么办。在过去一个世纪,一直有各种尝试来探讨贝克莱著作的怪异性,包括阿根廷作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探讨其唯心主义(作品《特隆》(Tlön)、《乌克巴尔》(Uqbar)、《奥比斯·特蒂乌斯》(Orbis Tertius))还有散文《对时间的新驳斥》(Nueva refuta-ción del tiempo)、布兰卡·阿尔西(Branka Arsić)对其视野理论的更新和更具创造性的新解释。汤姆·琼斯虽然声称要穷尽所有研究,该书根本没有提及这些成果。
这再次证明,谁也不能说怪异很容易。
译自:Empiricist, bishop and weirdo The deep spiritualism of Ireland’s best-known philosopher By
https://www.the-tls.co.uk/articles/george-berkeley-philosophical-life-tom-jones-book-review/
作者简介:
科斯提卡·布拉达坦(Costica Bradatan),得克萨斯理工大学文科教授,澳大利亚昆斯兰大学哲学荣誉教授。著有《生死之间:哲学家实践理念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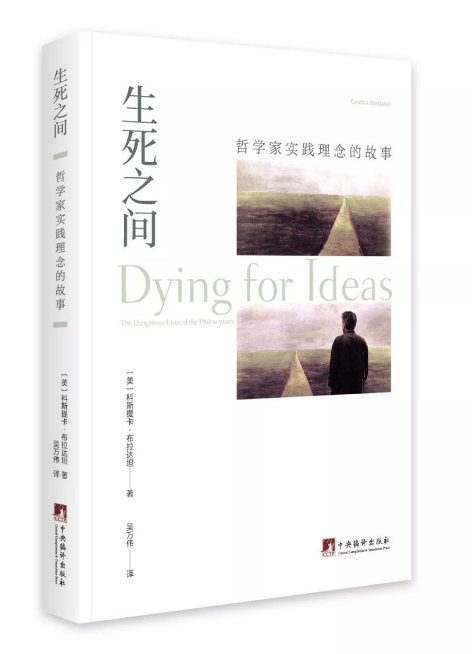
【上一篇】【万百安】柏拉图主义者为何这么好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