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义虎】重铸文明自信的一代儒宗——蒋庆先生的学思历程及其时代意义
 |
齐义虎作者简介:齐义虎,男,字宜之,居号四毋斋,西元一九七八年生于天津。先后任教于西南科技大学政治学院、乐山师范学院。主要研究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和儒家宪政问题,著有《经世三论》。 |
重铸文明自信的一代儒宗
——蒋庆先生的学思历程及其时代意义
作者:齐义虎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原载于台湾《国文天地》杂志2017年第1期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二月初九壬辰
耶稣2017年3月6日

一、学思历程:从词章之学到义理之学
蒋庆先生,字勿恤,号盘山叟,1953年生于贵州省贵阳市,祖籍江苏省丰县,与汉高祖刘邦为同乡。父亲早年参加八路军,在冀鲁豫一带进行抗战,国共内战时随刘邓大军挺进大西南,从部队转业后安家于贵阳。受文革影响,蒋先生初中毕业即辍学入工厂。做工之余颇好古典文学,醉心词章,有诗人之志。后参军入伍,在军营苦读马列著作,慨然有澄清天下之怀。退伍时适逢恢复高考,一举考取西南政法学院。有感于当时反思文革之风气,蒋先生在大学得以广泛阅读西方著作,尤其热心于人权学说,撰《回到马克思》一文,以人道主义解析马克思主义,由此遭学校长达一年之批判。此时之蒋先生不啻一信仰自由民主的热血青年,但由于屡遭政治打压,遂心灰意冷,不问世事,虽几经辗转得以毕业留校任教,但常以佛经、耶经为伴,由外在之社群思考转入内在之生命体悟。
从醉心词章、苦读马列,到热心人权、泛滥佛耶,虽归于寂寞却并未平复其心。直到1984年蒋先生读到唐君毅先生的书,才豁然开朗,心有戚戚,后更遍求港台新儒家之书。1985年过北京得拜访梁漱溟先生,受梁先生指点,开始研读阳明学著作。1989年发生六四学运,遭此国变,蒋先生之思路亦为之一变,但所变者与同时代的大陆知识分子却决然不同。由于党化教育的影响,大陆知识分子之所谓觉醒一般只是从马列主义意识形态的旧堡垒跳入西方自由民主理路的新窠臼,从苏俄式的西化走向欧美式的西化,不过是现代性下之左右立场的转换,并没有超脱现代化思维的整体性笼罩。蒋先生则不然,立足古典、反思现代,左右双遣、归宗六经,从心性儒学开始转向政治儒学的思考。就反思现代性而言,如果说近年来大陆学界从西方现代学转向西方古典学可以算作“齐一变至于鲁”的话,那么蒋先生从西学回归六艺则是“鲁一变至于道”,而且在时间上要更早于前者。于此亦可见蒋先生当年的远见卓识。

《公羊学引论》,蒋庆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公羊学引论》[修订版],蒋庆著,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
蒋先生以研究“春秋公羊学”著名,撰有《公羊学引论》一书,可谓经学家;同时又以通经致用的视野思考现代人类社会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以提出政治儒学而独树一帜,可谓思想家。经学乃其思想之根本,思想则是其经学之发用。蒋先生之学体大思精,然限于篇幅,下文将摘选其中四个主要方面进行介绍,以期管窥先生学术思想之全貌。
二、方法论:以中国解释中国
晚清以来,随着列强的不断入侵,中国屡次败于军事和政治,于是渐渐失掉了文明的自信。我们不光在政治、经济上任人宰割,在学术、思想上也同样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一边是打倒孔家店的傲慢咆哮,一边是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谦卑渴望。物质性的失败犹可挽回,精神性的失败无可救药。时至今日,虽然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已经跃居世界第二,科技水平也已名列世界前茅,但深藏在中国人内心深处的崇洋媚外的自卑感依旧挥之不去。一个民族如果不能挺起脊梁就不可能真正地扬眉吐气,自立于天地之间,可以说这是关系中国复兴的根本所在。蒋先生在2004年和2009年分别有《论以中国解释中国》和《再论以中国解释中国》两篇文章探讨了这一问题。
在蒋先生看来,西方近代以来的世界霸权大体经历了五个阶段,分别是军事霸权、政治霸权、经济霸权、科技霸权和学术霸权。前四个是显性的,易于察觉;后一个则是隐性的,极具迷惑性。其表现就是,西方的学术成为“语法”和标准,中国的学术则成为任其切割的材料对象和受其规约的“词汇”。中国像世界其他地方一样沦为西方学术的殖民地。所以为今之计就是要重建中国学术自身的义理结构和解释系统,对儒学而言便是要从文史哲三分以及国际汉学的范式回归传统的整全的经学范式。

《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蒋庆著,三联书店2003年版。

《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修订版],蒋庆著,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
考察历史,中国儒学的解构与殖民化开始于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说”。正是由于张之洞把体-用、理-势、群-己割裂开来,才使得西学有机可乘、趁虚而入,逐步蚕食了儒学的解释系统。体用本来不二,有其体自有其用,有其用自有其体。中学有体无用,必将挂空飘荡;西学由用而体,终于鸠占鹊巢。理-势的区分体现了中国的历史观:“理是势的最高道德评判标准,势是理的具体评判对象。”儒学的理想便是“以理转势”,其次是“以理判势”,但绝不能“屈理就势”乃至“以势僭理”。即便如孙中山先生这样的近代伟人,也震烁于西方现代化的排山倒海之“势”,告诫国人“世界大势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则亡”。但仔细想想,趋势再强也不等于普遍之理,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怎么可能是世界公义呢?于是“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成了‘理’隐退而‘势’横行的历史”。延续理与势的断裂,张之洞进而认为个人可以讲理讲道德,国家则不能讲理讲道德,否则就会亡国灭种。但为了救亡而不择手段,最后亡掉的则是天下和文明本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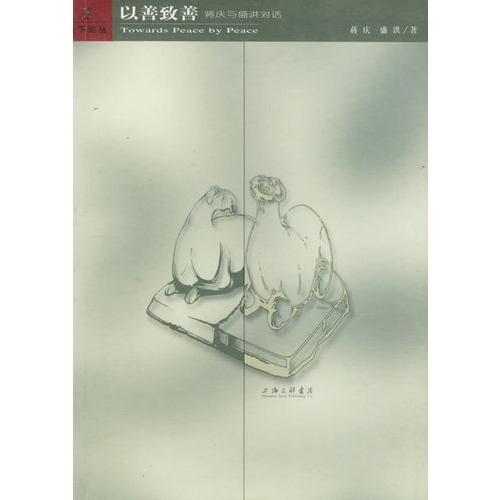
《以善致善:蒋庆与盛洪对话》,蒋庆著,三联出版社2004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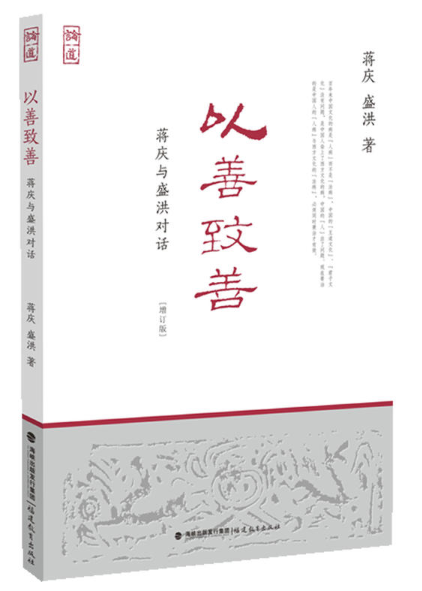
《以善致善:蒋庆与盛洪对话》[修订版],蒋庆著,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
除张之洞之外,“康有为用自由主义哲学的普遍人类公理解释儒学,梁漱溟用伯格森生命哲学解释儒学,胡适用杜威实用主义哲学解释儒学,冯友兰用新实在论哲学解释儒学,中国的马列主义者如侯外庐等用唯物主义哲学与启蒙哲学解释儒学,牟宗三用黑格尔哲学与康得哲学解释儒学,李泽厚用哲学人类学与唯物主义哲学解释儒学,罗光则用汤玛斯•阿奎那经院哲学解释儒学,现在又有学者用存在哲学与后现代哲学解释儒学。”“就算比较纯粹的熊十力与马一浮,也要用援佛入儒的方式与比附时学(西学)的方式来解释儒学。”“牟宗三先生说不懂康德就不懂孔子,说康德哲学是支撑儒学的钢骨,这些话最典型地说明了中国儒学已被西方哲学解构并殖民。”
从洋务运动中体西用的半撤退,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全盘西化的整体溃败,不过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后虽有梁漱溟、熊十力等新儒家为传统文化辩护,亦无力扭转西学碾压性的笼罩氛围。换言之,五四以来的新儒家只能在现代性的整体框架下为儒学争取一个类似于印第安人保护区那样的地盘,而不敢公然挑战这个体系本身。不管是熊十力先生寻求社会主义和儒学的共同点,还是杜维明先生探索儒学对资本主义的促进作用,儒学都只是一种依附性的价值学说,而丧失了其看待世界和人生的独立性。所以牟宗三先生才要千方百计以良知坎陷的曲通方式开出自由民主的新外王,以此来证明儒学并不是现代价值的反对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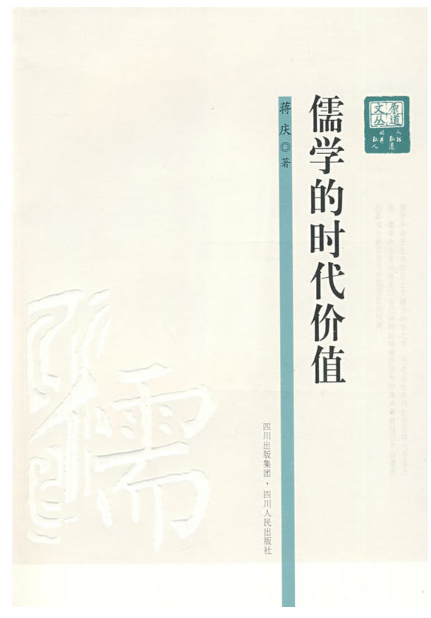
《儒学的时代价值》,蒋庆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蒋庆先生与以上思考方式皆大异其趣。经过二战后几十年的现代化发展,现代性已经越来越暴露出其价值上的根本缺陷。用蒋先生的话来说就是“极端世俗化、平面化、人欲化、庸俗化、现世化、非道德化、非历史化与非生态化”。与后现代颓废、荒诞、无力的反抗方式不同,蒋先生在儒学中看到了拯救人类的希望。蒋先生与五四以来的新儒学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新儒家们追求的是一种“现代化的儒学”,而蒋先生追求的则是一种“化现代的儒学”。现代化的儒学不免自我审查、舍己从人。化现代的儒学不等于反现代,而是要破除对现代化与西方普世价值的虚幻美化和迷信崇拜,直面其现实病症,以古典智慧化解现代危机,调和古今。从膜拜现代化到反思现代化,恰好为今日大陆儒学的复兴奠定了一个与前辈学者不一样的新起点。而以中国解释中国,乃至于以中国解释西学、解释世界,重建中国人的学术自尊和自立,便是极其必要的前提性和基础性的方法自觉与文化自觉。
三、判教论:政治儒学与心性儒学
《庄子》尝言,夫子之道至大至全,内圣外王不可割裂。蒋先生认为,“儒学有两大传统,一为心性儒学即生命儒学传统,一为政治儒学即制度儒学传统。”二者皆由孔子开出,心性儒学传承于曾子与子思子,发扬于孟子,宋以后之性理学与阳明良知学为其巅峰;政治儒学则主要蕴藏于“春秋公羊学”,传于子夏、公羊高、荀子,汉代之董仲舒、司马迁、何休为其大宗。心性儒学来自于实存性焦虑,志在成德成圣,属于内圣之道;政治儒学则来自于制度性焦虑,志在改制立法,属于外王之道。
然而随着科举取消、帝制覆灭,五四以来之新儒家对于昔日的外王传统多讳莫如深,而转以西方民主为新外王之道。只有钱穆先生本乎史家之温存敬意,对于传统政治制度多有辩护发明,不过钱先生自称非属新儒家阵营。故近代新儒家的成就多偏于发明心性儒学,接续宋学传统,但亦存在以西解中的问题。蒋先生自道,他之所以提出“政治儒学”,根本原因就是“要克服百年以来中国政治在义理上的偏差与在文化上的歧出,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政治的合法性危机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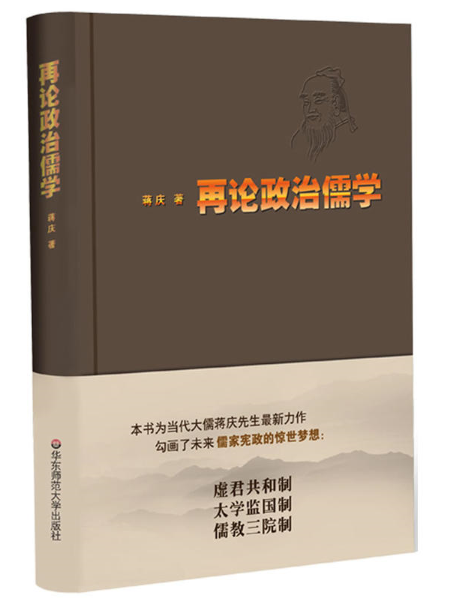
《再论政治儒学》,蒋庆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关于政治儒学与心性儒学之划分,时人多存在两大误解。一是误认为蒋先生要以政治儒学替代和贬低心性儒学。其实蒋先生公开表示过,他并没有因为提倡政治儒学而放弃心性儒学,更没有贬低心性儒学。他甚至说:“在我的内心深处,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相比,是更为重要的儒学传统。”他把心性儒学看作儒学传统中的“第一义谛之学”,而政治儒学只是儒家“第二义谛之学”。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在儒学传统中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只是为适应不同时代的需要,所强调的重点不同而已。就蒋先生个人而言,他在心性儒学上服膺的阳明良知学,在政治儒学上取法的则是春秋公羊学,二者集于一身,并无偏废。
另一个误解是,把大陆儒学视作政治儒学,把港台及海外儒学视为心性儒学,将儒学类型的划分变成了地域之争。其实大陆儒学的学统在1949年后难免中断,近二十多年的儒学复兴受惠于港台海外儒学者甚多,自然不乏港台新儒学的同调者,以蒋庆先生为代表的政治儒学只是异军突起的一支,并不足以涵盖大陆的整个儒学界。故大陆儒学界不能等同于政治儒学。同样,港台及海外新儒学也不能等同于心性儒学。因为在蒋先生看来,“心性儒学在本质上是生命体认之学与德行修为之学,而不是哲学思辨之学与概念推理之学,这是心性儒学作为中国儒学区别于西方哲学的根本特质”。“故心性儒学有切实的修身工夫问题,必须通过工夫才能证悟本体,而西方哲学则无修身工夫问题,只是以概念的思辨推理为能事。”可惜的是,港台新儒家从牟宗三先生开始,恰恰走上了以知识论替代工夫论的西化歧途。借助于德国古典哲学的解释系统,他们所建构的心性儒学已具有强烈的西方哲学色彩,把心性儒学变成了哲学思辨之学与概念推理之学,从而消解了心性儒学的工夫问题。蒋先生借用克尔凯廓尔的话批评其为“建构了儒学的大厦,自己却住在心性的茅屋里”。如此看来,偏离了实践工夫、只剩下一堆概念体系的港台新儒学与传统的心性儒学也已名实不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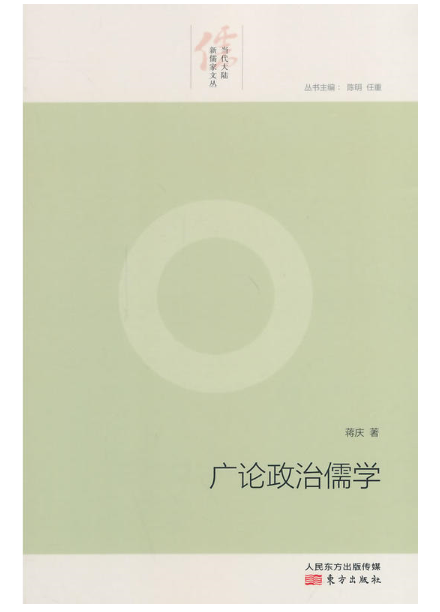
《广论政治儒学》,蒋庆著,东方出版社2014年版。
尽管如此,蒋先生仍然高度肯定港台新儒家“在中国文化花果飘零、学绝道丧的天崩地裂时代,以大悲心、大愿力切断举国反儒的恶浪浊流,守护儒家不绝如线的灵根慧命”之巨大历史功绩。在阳明精舍的复夏堂,既供奉有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三先生的牌位,亦有唐君毅、徐复观、钱宾四、牟宗三四先生的牌位。这代表了蒋先生对近代新儒家先贤们的崇高敬意。故对于今日之中国而言,不仅政治儒学需要重建,心性儒学同样需要重建。通过复兴“心性儒学”以挺立国人的道德生命,通过复兴“政治儒学”以建构国家的王道政制,只有二者并建,儒学才能振翅高飞。
四、政道论:以三重合法性超越民主独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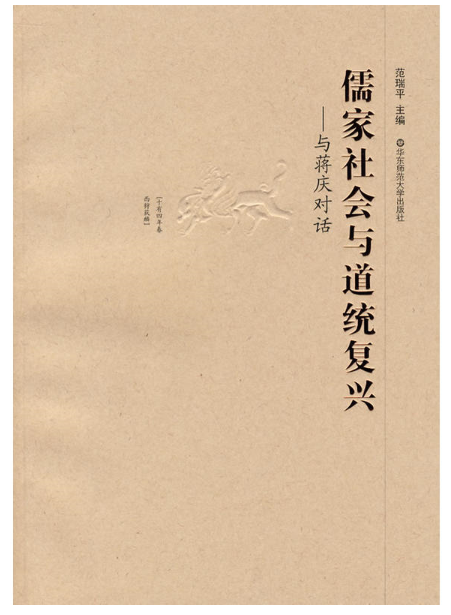
《儒家社会与道统复兴——与蒋庆对话》,范瑞平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孙中山先生说,政治就是管理众人之事。那么怎样才算是好的管理呢?政治权威从哪里来?其得以成立的理据是什么?评价其好坏的标准又是什么?对中国而言,这就是政道问题;对西方来说,便是政治合法性(又译作正当性)问题。在今天这个号称民主的时代,只有经过人民同意的政治才具有合法性,这似乎已经成了一种政治常识。但人民的投票意向是可以被诱导的,民意的选择也是常常会失误的,从政治实践的效果来看,投票选举其实并不那么理性。故选举只是一种程序合法性,不等于实质合法性。黑格尔曾说:“所谓的常识,往往不过是时代的偏见。”如今这种偏见已经根深蒂固,即便在现实政治中很多国家都已遭遇代议选举的糊弄和民粹主义的苦恼,但人们还是愿意相信这只是实际操作中的偏差,而不是民主理论本身的错。有的人为了追求形式上的民主甚至不惜把国家带入动乱、内战的深渊,这种对民主的迷信和执着已经十分接近邪教。
现代民主其实就是一种数人头的政治游戏,卑之无甚高论。在蒋先生看来,由于主权在民、人民最大,民意在权源上就具有了高于一切的独一性。但人民很容易疯狂,多数决也会犯错,一旦缺少制衡,就会走向暴民政治,这便是民意合法性一重独大的危险所在。对于从正态之民主政体败坏为变态的暴民政体,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早有过提醒。现代议会的两院制设计也正是防止议会专制、多数暴政和草率立法。蒋先生敏锐地指出,西方的三权分立只是治道层面的权力制衡,而不是政道层面的权源制衡。民意作为政治权力的唯一源泉,不仅有暴民政治的危险,同时也导致了政治的世俗化、平庸化、人欲化和功利化,彻底沦为一种小人政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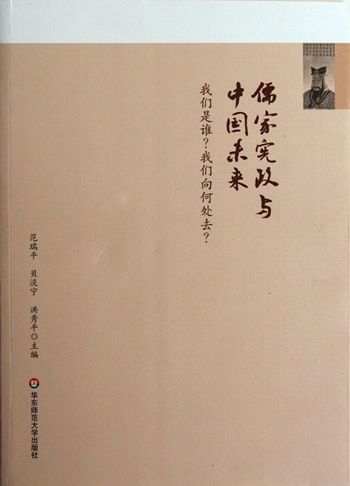
《儒家宪政与中国未来》,范瑞平,贝淡宁,洪秀平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为了应对民主政治的以上问题,蒋先生以儒学的三才之道为义理基础,提出了三重合法性的学说。儒学主张天人合一、法天而治,人立于天地之间,天覆地载、仰观俯察、父天母地,与天地共存共生,绝不是一种孤立的任性的存在。故不仅主权在人(在民),同时亦主权在天、主权在地。人间的政治应该同时受到天道、地道、人道的规范,而不是只有一层单薄的人道主义。天道体现为超越神圣的合法性,地道体现为历史文化的合法性,人道则体现为人心民意的合法性。超越神圣性代表着永恒不变的实质性价值,历史文化性代表着因地制宜的形式性价值,人心民意性则既包含实质性价值又包含形式性价值。将三才之道贯而通之便是王道政治。相比之下,“民主政治的最大问题就是其正当性不能来自天道性理的超越神圣的道德价值。”与民意独大的一重合法性相比,集合了天地人之道的三重合法性更为平衡,可以有效制约民意的向下沉沦和胡作非为,从而以道制欲、调适上遂。古人论述汤武革命的合法性就在于“顺乎天而应乎人”,即天道与人道的双重肯定。近代人简单地将民意等同于天意,把两者混为一谈,实际上是以人僭天从而取消了天道。
需要注意的是,天地人三才之道之间并不是平等并列的关系,而是立体的等差性分殊,即天高于地,地高于人。在蒋先生看来,由于自由民主制只具有“民意一重合法性”,只照顾到建立在世俗利欲上的短暂民意,而没有照顾到神圣超越的永恒天道与永续长存的族类历史。故自由民主制只具有“最低合法性”,而建立在“三重合法性”上的政府或政治,显然要比建立在“一重合法性”上的政府或政治更公正。这里体现了“政治传统性”(或曰政治古典性)与“政治现代性”的古今之争,也即“神圣与世俗之争”。用朱子的话说,就是“天理与人欲之争”;用政治儒学的话说,就是“除魅与复魅之争”。复魅就是要恢复政治的道德神圣性,以克服政治的现代性困境。蒋先生其实并不是反对民主,而是反对民主独大;不是反对现代性的个别要素,而是反对现代性的总体结构。对于某些正面的“政治现代性”价值,蒋先生主张可以工具性地具体而零散地加以吸取。三重合法性对民主合法性的超越便是如此,二者并不是排斥与对立关系,而是包容和含摄的关系。
五、治道论:以儒教宪政落实王道理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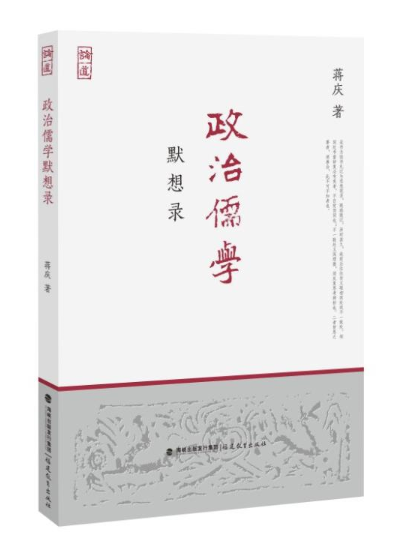
《政治儒学默想录》,蒋庆著,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
三重合法性只是一套政道义理,还需要将其落实为一系列的制度安排,这就是治道。优良的政治应该做到选贤举能、天下为公,但民主体制并不能实现贤能政治。在蒋先生看来,民主选举虽可产生精英政治,但并不能等同于贤能政治,因为前者只是“按照民众的生物学本能、个人的欲望权利与人民的公共意志来进行统治”,把政治变成了利欲之事而非道德之事。只有奠基于三重合法性基础上的儒教宪政才能真正实现贤能政治。用蒋先生的话说:“儒教”是中国文化特色,“宪政”是西方文化特色,中西结合的“儒教宪政”体现了古老的儒教文明在今天既守护传统又积极创新的“时为大”精神。
儒教宪政共由五个部分组成,即代表道统的太学监国制,代表国统的虚君共和制,代表法统的儒教司法制,代表政统的议会三院制和代表治统的士人政府制。太学拥有监督权力,虚君拥有国家权力,法院拥有司法权力,议会拥有政治权力,政府拥有行政权力。在合法性上,道统高于国统,国统高于法统,法统高于政统,政统高于治统。目前蒋先生已经对前三种制度作了比较详细的阐释和论述,后二种制度的具体构想则尚未见发表。
儒教宪政与儒家宪政仅一字之差,但内涵上却有着很大的不同。使用儒家宪政之名的学者以儒学为文教,不同于一般的宗教尤其是西方的基督教。蒋先生则赞同康有为的国教论,主张道在山林、道统高于政统,认为儒家不应再过多地依附于政府,而要有自己独立的组织体系,这样才能保持道统对政统的超越性和批判性。未来之中华宪政当以儒教为国教,一如英国以圣公会为国教一样。用蒋先生的话说,“儒教宪政就是在政治中‘存天理而制人欲’的政制安排”。
议会三院制是蒋先生最先发表也最为人所熟知的宪政设计。所谓三院即代表天道的通儒院、代表地道的国体院和代表人道的庶民院。通儒院由民间贤儒和科举选拔的儒士组成,以推举与委派方式产生;国体院由历代圣贤后裔、历代君主后裔、历代历史文化名人后裔、历代国家忠烈后裔、大学国史教授、国家退休高级官员、社会贤达以及道教界、佛教界、回教界、喇嘛教界、基督教界人士组成,以世袭或指定方式产生;庶民院由一人一票之普选与功能团体选举产生。三院虽各自独立,但不是平面化的平等关系,而是一种立体性制衡关系。所有议案分为强性议案和弱性议案,强性议案须三院一致通过,弱性议案只需其中两院通过即可。强性议案原则上永远有效,弱性议案可以考虑十年或二十年复议一次,重新确定其效力。另外通儒院因代表天道而在议会整体中处于优先地位,拥有对议案的“积极延宕否决权”,可以最终否决其他两院提出的议案。其他两院对“通儒院”提出的议案也可联合否决。三院制对现代民主制下议会的民意独大形成有效制约,可以避免大众民主的群氓统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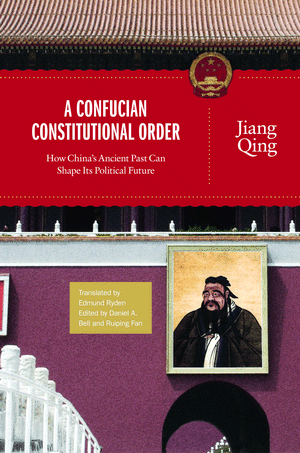
《儒教宪政秩序》(英文版),蒋庆著,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太学监国制源自传统的“以学治国”精神,体现了道统高于政统的超越性。用蒋先生的话说,儒教宪政的根本特征就在于太学监国。与议会三院不同,太学本身是国家最高学府,代表道统和学统,不参与具体政务的处理。故太学之治是“虚治”而非“实治”。儒教宪政的议会之上有太学,一如民主宪政的议会之上有人民。议会与太学不是相互制衡的关系,而是议会受太学监督的关系。太学祭酒(即校长)以古圣王的名义行使最高国家监督权力即“太学监国权”,实际上就是在国家制度层面代表“道统”与“学统”对“政统”(议会)与“治统”(政府)行使批评与制约的最高精神学术权力。太学共有六项权力,即最高监国权、最高养士考试权、最高礼仪祭祀权、最高罢免权、最高仲裁权和最高维持风教权。此外太学还有权派出史官对重大国事的讨论决策过程进行实录,以保证其公开透明;为已逝之国家领导人议定谥号;定期为国家最高领导层进行经筵讲课等。太学由祭酒一人与若干大学士组成,大学士由祭酒任命,祭酒则由选举产生。先由通儒院与全国儒林共同推举30名清议所归的学、行、品、识兼优的儒家学者组成“儒学家委员会”,再由“儒学家委员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出太学祭酒。此类似于罗马公教枢机主教团选举罗马教宗和伊朗“伊斯兰专家委员会”选举伊朗精神领袖的方式。太学祭酒任期终身,若因疾病或他故可自愿去职。“儒学家委员会”对太学祭酒有罢免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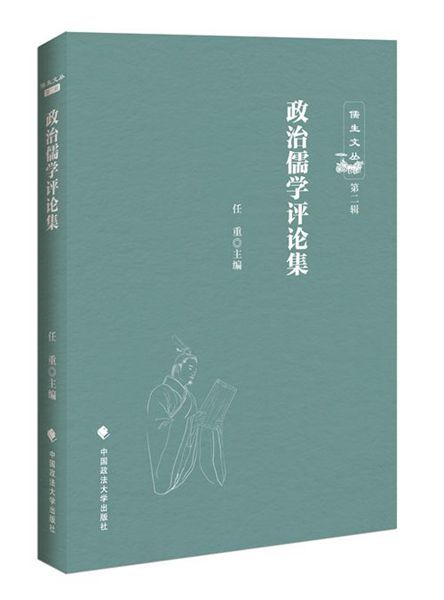
《政治儒学评论集》,任重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儒教宪政中存在着一横一纵两组三才之道,议会三院制是横向的天地人,太学、虚君、政府则是纵向的天地人。太学代表天道,体现了儒教宪政的“教”,对应于议会中的通儒院。虚君代表地道,体现了国家的历史性和持续性,对应于议会中的国体院。这就是作为国家元首制度的虚君共和制。英国宪政是“王在议会中”,儒教宪政是“王在议会上”。虚君共和制继承了君主制的根本精神——长久有效地代表国家的历史性与持续性;扬弃了君主制的表现形式——排他地不受制约地独自占有与行使实质性的政治权力,体现了儒家的中和精神。蒋先生认为,目前中国只有作为孔子后裔的衍圣公最有资格担任这一职务。作为虚君,主要行使两大类权力:一是政治外交性职权,二是宗教文化性职权。前者包括签署法律、派遣使节、接见外宾等,后者包括主持各种典礼祭祀等。此外虚君还有任命国体院议长和议员的权力。虚君由于不参与实际政务,可超然于党争之外,政府虽有更迭,国体则稳如泰山。
六、结语
以上便是对蒋先生之学术思想所作的简单介绍。如果把百年来儒学的兴衰比作抗战的话,清末的废科举、民初的废经学可谓九一八事变,五四新文化的彻底反传统则升级为七七事变,新儒家的文化保守可谓战略防御与相持阶段,蒋先生开启的政治儒学则进入到战略反攻阶段。蒋先生的思想魄力,不仅在于其因时损益的原创性,更在于其扭转学术风向、重铸文明自信的开创性。在遭遇了一百多年的西方挑战和自身危机之后,古老的儒学终于走出了低谷,刊落腐朽、重焕生机,再次散发出智慧的光芒。而蒋庆先生正是这一儒学历史新征程当之无愧的旗手和起点。
责任编辑:柳君
【上一篇】【余东海】儒家十诫
作者文集更多
- 【齐义虎】正名:所谓“中东”应该叫“西亚” 10-12
- 【齐义虎】《春秋》大一统的天人双重意涵 10-23
- 【齐义虎】敬挽张祥龙老师 06-09
- 【齐义虎】《礼记·王制》之官制研究 06-28
- 【齐义虎】儒家的“三民”主义 02-09
- 【齐义虎】我们需要怎样的统一?一国两··· 11-09
- 【齐义虎】法治中国化是依法治国的第一··· 08-10
- 【齐义虎】优化一国两制,亟需修法补洞 07-27
- 【齐义虎】中美政治体制的共同秘密:都··· 04-10
- 天津国学社团联合举办学术讲座,齐义虎··· 02-21
微信公众号
儒家网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

微信公众号
儒家网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