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纪】畸形儒家观和病态中国文明观——葛兆光“大陆新儒学”批评驳议
 |
丁纪作者简介:丁纪,原名丁元军,男,西元一九六六年生,山东平度人,现为四川大学哲学系副教授。著有《论语读诠》(巴蜀书社2005年)《大学条解》(中华书局2012年)等。 |
畸形儒家观和病态中国文明观
——葛兆光“大陆新儒学”批评驳议
作者:丁纪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表,首发于钦明书院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六月十六日丁酉
耶稣2017年7月9日
对大陆新儒学的学术格调,葛教授多处流露不屑。比如,他说:“作为一个历史与文献研究者,我不想一一挑剔这些‘有志图王者’历史论述和文献诠释中的错误,尽管这些错误既明显且荒谬。”
本来做这种指谬,正是一个“历史与文献研究者”之所擅长,也是他的本分所在,是他维护“历史论述与文献诠释”工作严谨性的职责所在。如果他的批评真从这方面开展,哪怕他把他的批评对象批判得体无完肤,相信大陆新儒学也无可辩白,只得自惭学力不济,反而不得不承认葛教授批评工作之建设性的,然而葛教授却放下他这份本分承担而别作他图。既不想“一一挑剔”,便不当多说此一句“既明显且荒谬”的话,以损其长厚之风的,葛教授却又不然。
葛教授对他的用意有进一步的说明:“我愿意同情地了解他们的政治立场和现实关怀,因此,我并不想过于学究气地从历史与文献这方面攻错。我倒是更愿意提醒读者注意,他们在谈论古代儒家传统和现代政治设想的时候,不时显露的用世之心,那种毫不掩饰的急迫和焦虑,似乎充满了字里行间。”
葛教授这种“愿意同情地了解”之用心,其真诚性或许不容怀疑,乃至可以相信,他不惜放下自己本来既擅长又应当看重的“历史与文献方面的攻错”,就是为了体现这种真诚性而付出的牺牲;但是,这段话也未必不流露出,葛教授有他自己的“急迫和焦虑”,不是那种“毫不掩饰的”,然而相信葛教授自求其隐微,对此也一定不是不能自觉的。
葛教授所流露的,正是他自己有一份表达“政治立场和现实关怀”的冲动,当他为这种冲动所驱使,去从事一种哪怕是对于“政治诉求”方面的批评工作时,就使得其“同情”既无法“同情”、其“了解”也无法“了解”,一种“同情之了解”的自我期许就只能停留于口头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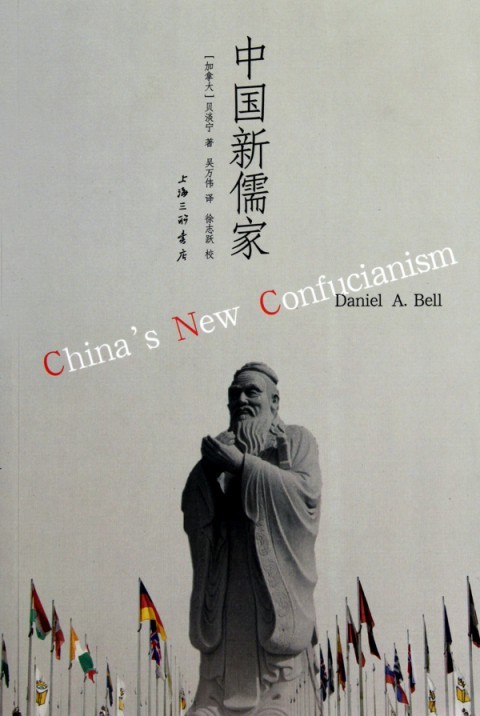
葛教授用心方面每失所准衡,陷于某种不能持中平允、态度方法方面不对称不均等的状况之中。举其两例:
例一,针对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等,大陆新儒学每欲指出其西方历史文化乃至宗教的成色而予以批判、拒斥,葛教授则惟乐以“现代普世价值”相承;但是当说到儒家仁义礼乐、王道理想的时候,葛教授却往往惟以举证“历史事实”的手段,将此尽归于儒者之矫妄与虚构,此等不但不是“现代普世”的,甚至连“价值”的地位也不具有。
葛教授惯于说“在历史上”、“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他们应当看看历史”如何如何,在他那里,儒家成了“古代儒家”,儒家经典成了“古代经典”。葛教授何不自思,为什么在你那里,中国只有“历史”,而西方却满满的都是“价值”?你批评大陆新儒学不把所谓“普世价值”当“普世的”而且“价值”,而你,只不过把你认为大陆新儒学对着“西方价值”所做的事情,转过手来在真正的中国价值身上从头做了一遍而已。
例二,针对大陆新儒学以为承认“普世价值”本质上就是“自我夷狄化”的观点,葛教授说:“‘夷狄化’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指控,因为它把分歧不仅看作是价值观的差异,而且提升到了文明与野蛮的冲突,甚至变成种族与文化之间的绝对对立。”
在儒家的话语系统中,诚然,夷狄化是一种非常严重的指控。但是,如果将此不适当地纳入其他话语系统中,意味就会转变。比如,将此纳入种族论视野中,那就严重到种族歧视的程度,葛教授在这里就有意无意地做了这种转义;将此纳入现代论视野中,那就可能成为某种“既明显且荒谬”的荒唐之论;但也未必没有某种视野之下,夷狄化直是一种“戏说”,则一点儿严重性都不剩下。
然则儒家本身话语,难道没有一种正当性之边界,使得任何非法的理解,都类同于“戏说”,都在摒除之列吗?葛教授出于平生从事“历史论述与文献诠释”工作所积累的功力,到这里真应该表现出更多审慎与尊重。但不管怎么说,夷狄化确实是儒家的一种严重指控;那么,反过来要问的是,当葛教授以“专制主义”定位大陆新儒学的时候,“专制主义”在葛教授的话语系统中,是一种非常严重的还是十分轻忽的指控呢?
当葛教授觉得,是他所要指斥的对象已然严重到不用“专制主义”这样严重的指控则不足以对应之,这时候,他实可以相应生一分理解,原来有一种对儒者而言极端严重的情形业已发生,则虽夷狄化之指控极为严重,但已到了无可避忌的时候,不然,儒者亦何乐于动辄以夷狄化谮人哉!
本来像葛教授这样注重思想学术严格性、敏于辨析的学者,对诸如此类自家用心失衡处,都不难自我侦知而得以随时发为自我修正之力的,竟不见有任何相应之表现。葛文甫一发表,引来一片喧腾和对于大陆新儒学的围殴态势,牵连至于儒家本身,这种效应,亦当是葛教授为文之初可以料见,却无所顾惜、不为苟避,可见真实用心。
“普世价值”之拥趸,和知识理性、衣冠斯文的依托主张者,与世道间一股西化浊流相倚成势,亦久矣已成人情常态;但当其所对立之面向上稍发噪音,或亦逗引得一二群众跳踉不已、与鼓与呼,此必以为与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相沆瀣,倘不以诸如“五毛”、“吃冷猪头肉”詈之,已经要自叹其客气、自服其修养了!此适为彼等论者心地欹侧偏失之又一征象。
循儒家思想文化传统,夷狄化含义亦不难乎理解,其实葛教授话里也已说到,第一是“价值观的差异”,第二是“文明与野蛮的冲突”;但是,到此为止,没有什么“甚至”!“种族与文化之间的绝对对立”,这是葛教授义外添义,并不属于儒家。
不是所有“价值观差异”都可以上升到夷夏之辨的高度、强度,但是,有价值观导向文明、有价值观导向野蛮,关乎文明与否的价值观差异,或曰,价值文明与否的差异,就直接生成为“文明与野蛮的冲突”。所以,“价值观差异”的极致化表现就是“文明与野蛮的冲突”,而“文明与野蛮的冲突”其实质就是“价值观差异”到不可调和而根本抵触对立,这说的也并非是两种东西。
说到底,文明,就是要过人的生活;野蛮,就是不要过人的生活。夷夏之辨最高的表义即在于文明与野蛮之辨,而文明与野蛮的冲突是人类间所可能发生的一切冲突中最严重的冲突。
但是,夷狄化或“自我夷狄化”语意上实有内在化、外在化两种指向:
假如为了接受自由、民主、平等等等,而将我们祖先所有的生活方式及其意义设定都看做“非自由”、“非民主”、“非平等”的,接受自由、民主等的理由当然可能是为了过一种“文明”的生活,然而为此却将我们自身既往的生活及其内生本具之价值都看做“不文明”亦即“野蛮”的,儒者必以“自我夷狄化”斥之。这是“自我夷狄化”的内在语意向度,是要首先说出的一个向度。
自我夷狄化就是为了过一种貌似“文明”的生活,而发一种自轻自贱、自污自渎,延而至于将本身文明所具之一切文明品格概以卑下化、虚无化视之,倒文明为野蛮的这种奴性的、失却人之自尊的精神表现。此必儒者绝不容忍、深所唾弃者,不仅因为这一派“自我野蛮化”的景象意味着叛卖、其中掩埋着被深深辜负的圣贤,也是因为此实一条自绝于文明之路,由“自我野蛮化”而欲趋向任何文明皆绝无可能。
其次才说到外在的,亦即对某种价值、观念、文化、生活方式论之以究系文明的或是野蛮的,亦即到底属夏属夷之评价向度的问题。葛教授颇觉奇怪地说:“批评‘普世价值’,把自由、民主与人权统统弃之如敝屣,并送还给‘西方’的论调,在中国大陆一直不罕见,不过,把这种思路引上‘华夷’之辨,大陆新儒家倒是独一份。”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地方啊,因为夷夏之辨,是惟儒家所禀有的精神资源和文明自觉!向以人类学、“思想史”、“小传统”之眼光待之,诚不能对此有所心会。
对于“为什么新儒家的思想会从中外一家,变成严分华夷”的问题,葛教授亦表示不能理解。他不知道,中外一家从来不能离了严分华夷讲,由夷夏之辨,到以夏变夷,然后才有中外一家;不然,难道中外一家讲的竟然是夷夏一家、文明与野蛮一家、人与非人一家吗?
正因为在这个问题上隔膜深重,葛教授全力抗拒之余,一不留神,也犯了个“历史论述与文献诠释”的错误。他说:“为什么赞同‘普世价值’就是‘夷狄化’?难道说,仅仅是因为现在的‘普世价值’来自西方?让人很难相信,有人居然至今还抱持‘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即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种观念。”
“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两语旨意相反,不构成“即所谓”关系。但我相信葛教授学养精深,此惟千虑一失而已,不必吹求。借此两语言之,“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支持起来中外一家的观念,“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支持起来夷夏之辨的观念。知其心异,则不轻与之;知其性同,则不显绝之。惟如此,方不至于一说天下一家就落入空泛矫情,一说严辨夷夏就沦为自锢锢人的地步。
当然,葛教授说“新儒家的思想从中外一家变成严分华夷”这句话,并不是说大陆新儒学自身已然经历这种曲折变化两阶段,这里的“新儒家的思想”,是包港台新儒家和大陆新儒学而言的,他恰恰以港台新儒家当中外一家、以大陆新儒学当严分华夷。
看看葛教授是怎么说港台新儒家的:“尽管担心中国文化精神的衰落和飘零,但是仍然要尊重现代世界的普世价值或者国际秩序,尽管这些强调民主、自由和平等的普世价值确实最先倡自近代西方,而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也确实最早奠定于近代欧洲,但这并不妨碍中国人接受这些‘好东西’。”
请注意“尽管担心”那句话,它的意思是说,我宁可让中国文化精神死了,也要表达对“普世价值”和“国际秩序”的尊重,因为那是些“好东西”。不消说,这个可以任其死了的东西,一定不是“好东西”,至少不那么好;如果有人竟然要把它说成“更好”,乃至指出它竟是决定我们如何能够识别任何一种“好东西”之为“好东西”、决定我们如何能够去接受任何“好东西”的基源性之物,那简直令人惊诧莫名,要啧啧感叹于“有人居然至今还抱持这种观念”了!
葛教授用与夷夏之辨决裂对峙的中外一家观、用宁可死了中国文化精神的心态去说港台新儒家,是否准确我不敢断定,此虽不能起牟宗三先生于地下,犹可以询诸李明辉先生以问其首肯与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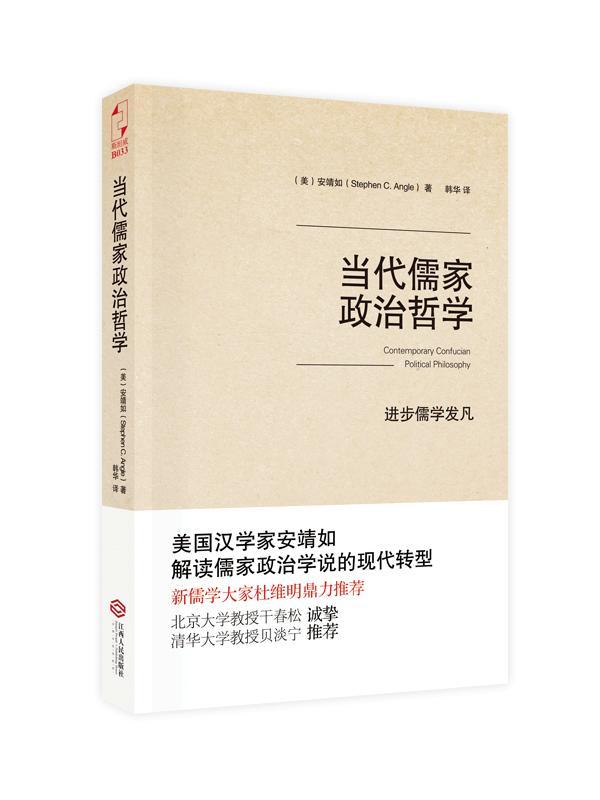
但我以为,对全体儒家,也包括对大陆新儒学学者而言,葛教授在这里简直提供了一种片面抱持中外一家观的最坏例证,是哪怕用最激烈的矫枉过正也一定要痛加反对、遏止的情形。我们是哪怕因为对这个“普世价值”和“国际秩序”的不尊重而百死,也要守护得中国文化精神使其不死的!因为这中间有一种深沉的文明在我的自信在,而一丝不为任何文化自卑心理所扰乱。
儒家天下一家、夷夏之辨两边要合着讲,单讲任何一边都有病;但两下里义理之关系,实可以做出清楚厘分。以为单取天下一家,竟可以引向对“普世价值”之认同、证成其立场,恐亦是一厢情愿的发挥和误读。
港台新儒家因为被葛教授说成中外一家,是不是就被他打了高分、从他那里获得了真正的认同感,不知道;但现在想来,葛教授说“让人很难相信”那句话,并非是不信有人仍持“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观,仅是指有人竟然仍信“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话而已。“让人很难相信有人居然至今还抱持这种观念”,一旦有人出乎葛教授的“相信”之外,居然真的抱持这种观念,葛教授会怎么办,葛教授没说,我也不好瞎猜,大概这种人出来,是最令如葛教授者挠头的事情了。
葛教授这个表达的对应式表达,是“让人很难相信有人居然至今还不肯抱持那种观念”。这个不用猜,这属于“文献诠释”,可以很牢靠地解读出来。“那种观念”,指的就是“普世价值”。说到“普世价值”,这是葛教授最敏感、最在意,也是他对大陆新儒学最为愤愤不平的所在,因为这正是他自己的“政治立场和现实关怀”之所在。所以他会质疑大陆新儒学:“如果按照他们设想的‘风俗与礼乐’建立起来的社会,还会容忍平等、自由、民主和人权这些现代价值吗?”他会以“容忍平等、自由、民主和人权这些现代价值”为一种思想学术工作、社会生活追求的前提,而且不知如何会错了意,竟也以为这是他与大陆新儒学不言而喻的共同前提。
不知大陆新儒学正是以批判这些“现代价值”为前提,或至少要否决它们的天然前提地位,在这种批判、否决的姿态之中,也可以包含一种反向发问:“以这种自诩为平等、自由、民主和人权之现代价值建立起来的社会,还会容忍仁义礼乐、文明自尊、人之自本自根与无限上达的可能性吗?”只不过如此一问,必然又会激起葛教授“让人很难相信”之类的反应了。
葛教授基于他自己的“政治立场和现实关怀”,从一个很远的角度上,确实对大陆新儒学做出了“同情之了解”的尝试,可是,这种了解的结果,是在一定程度上使大陆新儒学“普世价值化”,或者这样说,大陆新儒学有限的一些可理解性,只能来自于它的“自由民主化”。这充分证明了我前面所说葛教授这种“同情之了解”的失败,因为“同情”是要放下自己的成见去同人之情,而葛教授则是如果不先强人就我,就很难同情、“很难相信”的。
比如,他说:“大陆的一些儒家学者面临严峻的政治压力,试图表达一种与主流政治意识形态不同的立场和路径,不能不抛弃温和的或理性的学院化方式,这毫无疑问表明了一种反抗绝望的勇气”、“(由蒋庆一文)可以看到,大陆新儒学试图在政治上不认同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在思想上另寻立场和起点的意图。”
回到一九八〇年代整个国家民族的创痛记忆,儒家从道义上当然无条件地与直接蒙受损害者站在一起;但是说到“绝望”,在那个争锋面上所展现的两种对立的文化政治路数与方向,其实同样深刻造成儒者的“绝望”,而不仅仅是对哪一方面的“绝望”。
葛文引到蒋庆一句话,“儒家并不是对现世政治持绝对的反抗态度与不合作态度”,但似乎未能多加注意。说到底,儒家对“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看待方式与应对方式,是根本非自由主义化的,对此不能有恰当之理解,就可能把适值此时而兴起的大陆新儒学的种种表现,仅仅看做是策略性的,或应激式的反应,而忽略其发于儒家本身精神的当然性和当代儒者应对其思想文化处境的由衷性;进而,基于这份误会之下所生的“同情”、“感同身受”,就会把儒者后来不如其所期、对自由主义呈现离合乃至决绝态势的表现,一概视为首鼠两端、投机逢迎、鱼龙变化。
如果对“普世价值”、“自由民主”只取一种拥趸心态,确实就“很难相信”、很难容忍即便是它们也必须承受某种批评的事实;但是,如果自己先稍稍祛其拥趸心态,如果对他人也不首先寄予一种“普世价值观念共同体之当然成员”的虚幻印象,则一种异己成分的真实存在、一种源自相异方向上的批评的不期而至,真的是那么不可以想象吗?
你不妨先用一种不可思议的口吻反诘到:“批评‘普世价值’,把自由、民主与人权统统弃之如敝屣并送还给‘西方’的论调,在中国大陆一直不罕见”、“为什么赞同‘普世价值’就是‘夷狄化’?难道说,仅仅是因为现在的‘普世价值’来自西方?”
但这话说过之后,学者的使命就来了,你还是要用辩理的方式向我们表明,这些“来自西方”的东西,是何时、以何种方式,蜕去其西方出身的印迹,而成功登上“普世价值”的高格。这项辩理工作的任务,不会因为前面的天真一问,就自动被豁免了的。如果这种辩理工作不能成功表现其说服力,那么,我据它们“来自西方”这点,再把它们“送还给西方”,这似乎算不得多么出格的事情吧?
蒋庆批评现代西方民主制的“现世民意独大”,因倡为“三重合法性”说。葛教授质疑之,而谓:“政治合法性如果不经由现存国民的意志表达,那么,有谁能证明那个既超越现世现存的人心民意,又赋予当下政治合法权力的‘天地人’,有永恒性、绝对性或神圣性呢?”蒋庆并没有要求“三重合法性”都具有“永恒性、绝对性或神圣性”,三者之中,“现存国民的意志表达”首先要排除其有“永恒性、绝对性或神圣性”。
葛教授其实也意识到这一点,假如葛教授的文字对他思想的传达是精准的,那么我认为,他的“政治合法性如果不经由现存国民的意志表达”这句话还是颇堪玩味的。
它的意思,首先是说,在以种种理由将诸如“历史、封禅、符瑞、德运甚至神话”等等(兹据葛教授列举)纳入不可证明的、因而被排除出有效的合法性根据范围之外以后,“现存国民的意志表达”就成为各种可能的合法性来源中唯一可证明的一种;
其次,由现存民意所达成的政治合法性证明,有其不饱满、不理想性,只是一种消极的、底限意义上的证明,仅仅因为“如果不经由现存国民的意志表达”,现实政治就将失去任何合法性根据之支持,亦即,仅仅是为了避免政治不能获得任何一种合法性支持的局面发生,才设此“现存国民的意志表达”为一种合法性之根据。这当然不但是一种有限理性主义,而且遵循的是一种结论先行的论说逻辑。
葛教授的意思与一句流行语旨趣相通:民主不是最好的政治,只是最不坏的政治而已。但是葛教授在这里却陷入一种自相矛盾之中。
他有两句话,第一句:“从学理上说,所谓‘合法性’必须有不言而喻的来源,只有这个来源具有权威,它才能成为合法性依据。”第二句:“合法性来源本身之合法性,究竟来源于哪里呢?”
这两句话,大概可以看做是他试图对合法性根据之正当与否提供一些形式判别原则,但这些说法都带着严重问题。
第一句,什么叫做“不言而喻的来源”?我理解,葛教授想说的是像公理那般具有自明性的绝对前提。但是据前,“现存国民的意志表达”作为合法性根据,是需要被证明的,它并不具有自明性,只不过按葛教授的看法,它是可以被证明的而已。这也就表明,民意不是一种政治合法性“不言而喻的来源”。
第二句,这种发问方式,其实更多不是问向“合法性之合法性”,反而极可能导致“合法性问题”的瓦解,所以葛教授会说到“这个来源具有权威”,“权威”当然可以是一种“合法性”,但诉诸权威而非诉诸合法性,即表明合法性追问已失效。
退后一步说,既然要作如此发问,那当然就要公平地面向民主理论和非民主理论,也就是说,“现存国民的意志表达”作为合法性依据之合法性,也是需要被追问的,而不能以为被追问的仅是“三重合法性”。如果承认民意合法性需要被追问,那为什么会看不到,“三重合法性”思想正包含有这种追问的意义呢?
要用“现存国民的意志表达”去达成政治合法性证明,则先要对“现存国民的意志表达”本身求得一种合法性证明;而且,即使依“现存国民的意志表达”完成一种政治合法性证明,这种证明也必是犹有遗焉、若有憾焉者,而非对政治合法性证明的各种可能性的穷尽。
这个意思,相当程度上可以这样表达:现存民意既不是理想的政治合法性根据,由它所支持起来的政治也不会是理想性的政治。但这恰恰是民主政治及其理论的一大特征或“优长”,作为“最不坏”而非“最好”的政治,它是成立于经验主义基础上的、非理想化的政治途径与进路,它内在地包含一套自我试错机制,从而应当容纳乃至要求着无论来自于民主内外的各种可能的批评。
在政治合法性问题上,这种批评恰恰可能表现为,对于能够赋予现存民意合法性根据地位的真正自明性前提的追溯,以及,对现存民意之外政治合法性根据的更加丰富的想象和探求。蒋庆所说“三重合法性”中,“天”、“地”所包含的合法性根据含义,绝对富有自明性。任何时代的“现存国民”,都不可能不直观地立身于这个“天”与“地”之间,因此,它们即便不是直接、狭义的政治合法性根据,也是那个唯一可证明的政治合法性根据之“合法性来源”,是更广义、更基层的根据之根据。
我在前面说,葛教授喜欢说“历史”如何如何,似乎他只是在做以“历史”抵消“价值”的事情;但是,当我看到他在列举中国历史上种种“不可证明的政治合法性来源”的或虚伪或神秘、总之无不出于政治功利主义或功能主义的表演,与封禅、符瑞、德运等等并列且置于首位的竟然是“历史”的时候,忽然意识到,葛教授虽然作为“历史与文献研究者”,但他的工作目的并不在于证成“历史”,恰恰在于解构“历史”,在这一点上,他对“历史”倒确实不比对“价值”更偏袒些、更多些钟情。
在他那里,虚构叙事的“本体表现”似乎倒在于“历史”,历史虚构的进程只是附带地形成了一套价值虚构,因而,他对价值的批判倒只处在一种边角之地。看来,在他这一次的批评中,还回荡着疑古与信古、“小传统”与“大传统”相摩相荡的余波。
但是,如果基于这种史观去把“现存国民的意志表达”之类强调到壅遏直观、昏惑自明的程度,使本来仅为一世之民者忽尔竟如“永恒、绝对、神圣”的永世之民,使政治成为截断人之超越化、历史化存在向度之一途,这时候,对于“普世价值”、“自由民主”之类的主张与接受,此非人之“夷狄化”又是什么!
当一种民主论证要把“现存国民的意志表达”从具有、甚至可能是唯一具有可证明性,进而要把它说得像是个政治合法性“不言而喻的来源”,这就成为极端民主论,甚至未必不可以说其心态上流露一种“民主原教旨主义”倾向。
从论证角度讲,蒋庆当然不用证明“三重合法性”都具有“永恒性、绝对性或神圣性”,只用证明“天”以及“地”有此性即可;而极端民主论者则需要证明,民意实具此“永恒性、绝对性或神圣性”,这个论证难度,比较蒋庆可以说只高不低。
葛教授批评大陆新儒学有极端化倾向,无可讳言,大陆新儒学实未能免此。但是,孰不有极端?
世间极端也有两种,有强者的极端、有弱者的极端,或曰,有得势者的极端、有失势者的极端。得势者的极端,可以粉饰之以“普世价值”;失势者的极端,却只能被宣布成为“极端主义”,到头来迫得只能用一种挑衅、叛逆、不合作、破坏性的方式一拍两散。
说到底,所谓极端主义其实只是不肯被“普世价值”所驯服的一群人而已,虽然有此未必是什么世间幸事;但当对某种情形可以轻易发一种极端之指责,不表示他自己不也是个极端之身,倒是可见他在世道间谋得了个怎样的势头。
中国的民主论者还有一种论调,即认为当前中国连民主尚且没有,遑论反对民主。如葛教授亦曰“尽管现实中国并没有西方式的民主制度”云云。但论说的逻辑有时就是这么吊诡,如果没有民主就不能有对民主的批评、反对,那么同理,没有民主也就不能有对民主的主张、赞成,若此将奈何?
如中国虽没有西式民主,但是已经有对民主的种种依托假借,民主的这种口实化、幌子化亦即“伪民主化”,即不但提供对于虚假民主,亦提供对于民主本身的充分的批评理由。所以,即便发于对民主的最大辩护热忱,也要随时提醒自己,拒斥对民主的批评,把凡是这种批评的发出都看做出人意表、匪夷所思的事情,其本身就未必不包含一定反民主性。
葛教授对照港台新儒家与大陆新儒学对“普世价值”等的不同态度,意在说明儒家思想资源中并非没有与此相接通的可能,但他也如实指出了这种接通努力之困难,比如表现在牟宗三“开出说”上。他引述余英时教授对港台新儒家的看法,以为他们企图建立的是“教”而非“学”,“他们绝不甘心仅仅自居于哲学的一个流派”;葛教授自己也说:“他们原本只是做‘素王’,在文化和思想上重建国人信仰。”
果如此,在教不在学、做素王,则大陆新儒学所取于港台新儒家者必多而必敬意备具。惟是这种自我意识,在现代新儒家第一、二代中最多或有一二人当得,就其全体之文化视野与精神承担而言,如此基本理会不着,所以才会有诸如“没出息”之苛评。
“没出息”之语确实难听,毫无儒者温醇宽大之气,尤非可以加于前辈者,但是,儒者本具的整全文明视野和根本教化论之眼光抱负,确系由大陆新儒学极力凸出、张扬起来,从失落此文明与教化之意义而论,或至少不能如儒家本实地予以显明彰著,而每对“普世价值”等等行一种过避过让之举,人虽不言,恐“没出息”之叹未必不密在齿颊间。
说回到大陆新儒学的学术格调,要说从这方面看大陆新儒学一开始就展现出成长为伟大事物的潜质,我亦不敢必;但是,他们学术方面的努力与既已达成的实绩,也诚不容无视。
“回到康有为”起始不无与“回到牟宗三”对提的口号意义,但随着这种标帜,一批渐渐被现代中国思想界陌生或遗忘的身影正被重新开掘出来,不只是康南海,还包括章太炎、张南皮、曹元弼以至曾文正等等,这中间其实包含一种借助重回中国近代化起点以重思近代化道路方向以及中国文明本身所禀有之天命的努力。
如葛文也数次提及西汉、晚清两段,将个董子说得不是个失落、可怜的董子,似乎就只能走向叔孙通、公孙弘化,如此局狭与奚落,再看大陆新儒学学者所呈现的西汉儒者治理方略和理想图景,不得不承认,这确实更加宏阔和正大,要远远有出息得多。
但大陆新儒学的学术着力点,首先选取比如君主制、儒教论、宗法制、性别观等等方面,这是自中国近代化历史开启以来,儒家被丑诋最深、也是近代中国人民普通心灵之间被塑造得对儒家隔膜最重的方面,因而大陆新儒学起手就使自身陷入一种说理为艰、聚讼最重的地步。
谓之说理艰难,好比西汉一代儒者要说出此等,背后义理根据、心灵养成、习尚风俗等等,都在不言而喻中,可以一动皆应;但随着晚清儒者努力的失败,后经长达百余年的摧残凋丧,此等背后,全部不言而喻的成分都成为言犹不喻、蠢顽不灵,义理根据等等深深消隐,则大陆新儒学承此颠仆,仅以一套君主制观念等等为说,势不能不使人如对鬼垒妖窟,见之惊心,更不用说亲之信之,则其说理前景实不容乐观。
然而说到勇气,为人所不敢为,拂逆一世之讪笑,大陆新儒学学者之勇气正首先表现于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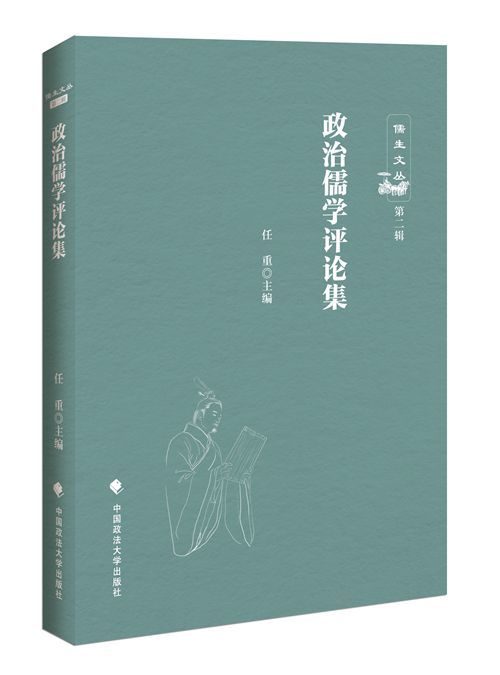
葛文中有一段话,试图集中谈出他对大陆新儒学的印象和评价:
“一般来说,他们并不在乎历史与文献的准确与否,他们对儒家经典与思想的诠释策略是:第一,改变近代以来把‘经’作为‘史’来理解的立场和趋势,重新捍卫儒家‘经’之神圣性,把原本已经学术化的现代经典研究,重新回到绝对信仰化的经学解读和义理阐发;第二,因为他们引经据典的目的在于介入现实和指导政治,因此,他们往往把古代经典作过度诠释,不是抽离其历史语境,就是进行有目的的引申;第三,由于他们把儒家(或儒教)作为信仰,故而有宗教信仰者般的绝对立场,形成逆向‘东方主义’的思路。也就是说,为了对抗和抵销西方的文化、制度与价值,因此,凡是据说被西方形塑、强调或批判的‘东方’,反而要特意格外高扬……”
这中间很多内容,前文都已分头评述,故此处不再详论,只大略言之。这里涉及的每一个问题,其实都可以返还给葛教授自己:
第一,“近代以来把‘经’作为‘史’来理解的立场和趋势”、“原本已经学术化的现代经典研究”,请问,是谁的“立场和趋势”、它是如何形成的?这个“立场和趋势”完全不容变动吗?儒家经典本身是不是只配得着这样一种“现代经典研究”,而以捐损其神圣性为代价?中国人民之生活与心灵,是否也只以得着这个“现代经典研究”为满足而不问其他,或当有其他方面之要求时,亦惟有求得一种外向式之满足?这些问题,希望葛教授都能去其“历史与文献研究”本位立场,不自私地思之。
第二,“历史与文献的准确与否”,我想大陆新儒学学者不至于“不在乎”,然而学力不济诚有之,此无可自讳,需要尽速成长。但是说到“过度诠释”,“有目的的引申”未必就属“过度诠释”,而把经典一味坐实于“古代”、使其泥于“历史语境”而不许稍稍拔起,这却可能连最起码的“诠释”工作都算不上。
第三,如果凡被“东方主义”想象过的东西就格外予以高扬,葛教授谓之“逆向东方主义”,那么,是不是可以说,凡是被“东方主义”想象过的东西,自家本来明明就有、本来自信而突出,却偏要羞之涩之、隐之晦之,以避“东方主义”、“逆向东方主义”之讥,这其实只不过是一种“反逆向东方主义”呢?
当然,即便葛教授对大陆新儒学批评如许,也还是会说:“大陆新儒学从文化儒学转向政治儒学、从道德伦理阐发转向政治制度设计、从思想学说转向意识形态,逐渐与自由主义、社会主义鼎足而立,在二十一世纪成为中国大陆政治与思想舞台上绝对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大陆新儒学理想所在,固决不限于与某家某派并立而为一种皇皇之“主义”,但经年勤苦,得葛教授此言以为旁证,亦尽可以为今后增气增信。
我不属于大陆新儒学,我的立场,以葛教授文前说明所分,大概“对儒家思想有认同”一语似稍说得着然实嫌太弱。我是立足中国大陆,对儒家思想有坚定认同与持守,而视大陆新儒学为儒门别派的人。过去对大陆新儒学,一向持审视、质疑态度,既以为所谓大陆新儒学者,“不过数人耳”,其设为讲坛,“亦不过一二省市之内耳”(仿黄梨洲《东林学案总序》语),乃至以为,虽“大陆新儒学”之名义亦未必成立。
得葛教授此文之映照,反而发现自己与大陆新儒学学者共禀许多信念前提。葛教授文前说明的意图,或许是想更清楚地界定其批评对象、不欲牵涉过大,但其分类既不谨,涵盖亦不全,加之论说过程动辄越界,自己先就不曾认真对待自己的这个说明。
在他对大陆新儒学的批评中,时时透露出他对儒家本身的恶感恶评。
如曰:“自古以来,儒家都希望在庙堂里为‘帝王师’,在政坛上‘以经术缘饰吏事’,至少也要在祭礼中‘端章甫为小相。’”
如曰:“‘使天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儒家历来口气很大,气魄不小,这也是新儒家的一贯家风,从二程、朱子、陆象山一脉宋代新儒家,到梁漱溟、熊十力、牟宗三以来的现代新儒家,都有很大的勇气和抱负。”
如曰:“从‘内圣’到‘外王’说说容易,一旦进入实际操作领域,习惯于道德伦理教化,最多能够提出礼乐制度的儒家往往措手无策,无奈之下,他们往往只能移形换位、改弦易装,由公开的儒家变成隐藏的法家,或者干脆从法家那里挪用资源。”
如曰:“‘儒家经典’就一定是真理,并且可以治理好国家吗?‘四书’、‘五经’在现代,仍然可以作为考试与任职的依据吗?”
凡此之类,葛教授都敢自信地说,是在批评大陆新儒学,或为批评大陆新儒学的论说之所必须,而非故为此株连,而暗输其“评法批儒”、“批林批孔”时期之所养成的畸形儒家观和病态中国文明观吗?

我甚至怀疑,当葛教授在写到梁漱溟“被毛泽东痛斥并压在了五指山下”这句话的时候,内心其实是充满了某种快感的。则文前加说明,亦一已遍见于全文的掩饰之手法而已。
如谓“异想天开”、“痴人说梦”乃至“借尸还魂”等等,儒者大可以以此自况,此亦未必讽刺得着我。就像“丧家狗”之类,我也不妨说,你也不妨说,说之适以见彼此怀抱不同而已。所以作为此文,非欲龂龂以对,惟以葛教授之批评,徒见其偏见相抵、意气相争,凡其所施之讥弹,概皆不先之以自反,此于当前之中国学界,非足以垂范,适足以垂戒,故为此缕缕。
虽然,葛教授不亦曰乎:“儒家历史上真正的政治批判者与思想阐发者,恰恰应当与政治权力保持距离,也就是应当‘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什么距离是适当的距离,见者各异;且所阿之“世”,西方为一“世”也,西化浊流为一“世”也,岂徒“政治权力”之为“世”哉!
惟“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真可以三复斯言,而愿与大陆新儒学诸君子,亦愿与葛教授共勉。
丁酉六月十一至十四日
相关链接 【葛兆光】异想天开:近年来大陆新儒学的政治诉求
作者文集更多
- 【丁纪】《中庸》首章说 08-15
- 【丁纪】知与识 11-25
- 【丁纪】《启颜录》儒家类七条 11-17
- 【丁纪】关于“腐儒”的三条备注 06-10
- 【丁纪】腐儒、伪君子与丧家狗 05-30
- 【丁纪】莫我知也夫 02-23
- 【丁纪】须从根本求生死,莫向支流辩浊清 02-09
- 【丁纪】主一无适续 01-29
- 【丁纪】是礼也 09-30
- 【丁纪】玩畏 09-09
微信公众号
儒家网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

微信公众号
儒家网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