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文明】儒教在现代中国国家建构中的意义——辛亥革命后康有为的孔教思想
 |
唐文明作者简介:唐文明,男,西元一九七〇年生,山西人,北京大学哲学博士。现任职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著有《与命与仁:原始儒家伦理精神与现代性问题》《近忧:文化政治与中国的未来》《隐秘的颠覆:牟宗三、康德与原始儒家》《敷教在宽:康有为孔教思想申论》《彝伦攸斁——中西古今张力中的儒家思想》《极高明与道中庸:补正沃格林对中国文明的秩序哲学分析》《隐逸之间:陶渊明精神世界中的自然、历史与社会》等,主编《公共儒学》。 |
儒教在现代中国国家建构中的意义
——辛亥革命后康有为的孔教思想
作者:唐文明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表
选自作者所著《敷教在宽:康有为孔教思想申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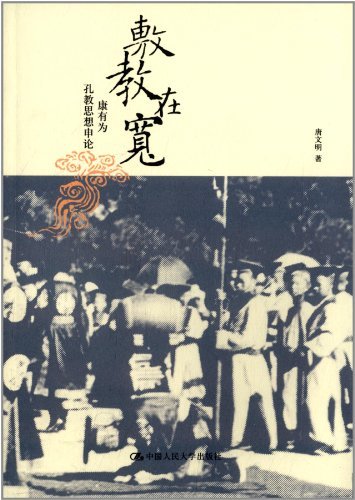
既然国教折可以代表康有为戊戌流亡后的孔教思想,对应于其君主立宪的政治思想,那么,在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康有为的孔教思想又有什么新的变化呢?
鉴于康有为的孔教建制主张与其政治主张具有紧密关联,而他又以君主立宪与虚君共和分说其辛亥前后的政治主张,我们需要先来看看君主立宪与虚君共和之间的异同。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康有为提出虚君共和的直接动机并不是想在君主立宪之外另倡导一种新的政体理论,而是为了解释辛亥革命后实际发生的政治事件。
1911年10月10日,武昌之变爆发。随后各省纷纷响应,宣布独立。为应对时局之变动,清政府命令资政院迅速起草宪法。在宪法颁布之前,资政院先行拟定了作为立宪指导原则的“重大信条十九条”,并于当年11月3日正式公布,即为历史上著名的“十九信条”。康有为的虚君共和论即因十九信条而发。
在写作于1912年1月的《汉族宜忧外分勿内争论》中,康有为以禅让理解十九信条的意义,且根据十九信条的第六条认为禅让的对象是国会:“夫自十月六日,誓庙煌煌,颁十九信条,岂非禅让大典之册文耶?但非禅让于一人,而禅让于国会耳。”[1]
于是他指出,十九信条意味着“汉人已灭满而立共和国”,辛亥之变可称为一次“禅让革命”。[2]且正是因为有十九信条,才使得康有为对于这次禅让革命有相当高的评价:“使于九、十月间,十九条颁后,和议即定,或少迟乎十月十六日摄政王废后,和议即成,中国得完全共和之宪法,又可得汉、满、蒙、回、藏无缺之金瓯,岂非尽美而尽善哉?”[3]
析言之,康有为之所以称此次禅让革命为“尽美而尽善”,是因为他认为——基于十九信条——这次禅让革命至少取得了三个重要的成果:
一是中国并没有因为革命而分裂,新的中国是继承大清帝国的国统而来的;
二是中国从此成为一个立宪政体的共和国;
三是中国仍保留君主制。
在此文中他对十九信条进行了详细解读和阐释,除了担心他称为“让皇”的宣统帝及皇室的安危而申说“夺皇权而存皇统,实暗合《春秋》之义”的文明之道外,主要目的就是要阐明保存君主制的重要性。鉴于当时袁世凯以类似于代理总统的身份而摄政,康有为发挥其虚君共和之说、阐述虚君共和之美善曰:
“若今中国乎,其为有虚君之总统共和国乎?又一新共和制也。有虚君,则不陷于无政府之祸,一善也。无美洲争总统之乱,二善也。无法国之总统、宰相争权,致百政不举之失,三善也。总理居摄无道,国会可去之;若其有道,可久留,四善也。”[4]
不过,鉴于当时汉人民族革命论的强势,康有为虽然对以君主立宪为精髓的十九信条评价甚高,但其时他并没有顺此主张立清朝的皇帝为新的共和国的新君主,而是提出一个非常特别的主张,即立衍圣公为新君主。
在写作于1911年11月的《救亡论》中,康有为说:“中国乎,积四千年君主之俗,欲一旦废之,以起争乱,甚非策也。……以中国四万万人中,谁能具超绝四万万人而共敬之地位者?盖此资格,几几难之,有一人焉,则孔氏之衍圣公也。”[5]
而其理由则曰:“孔氏为汉族之国粹荣华,尤汉族所宜尊奉矣,舍孔氏亦无他人矣。主民族革命者,应亦同心而无词矣。”[6]
康有为更将衍圣公与日本天皇、罗马教皇相比:
“夫衍圣公乎,真所谓先王之后,存三恪者也。以为圣者之后,故其恪久存而永不绝,其公爵世家,历二千四百余年。合大地万国而论之,一姓传家,只有日本天皇年历与之同,其无事权而尊荣亦略同,又皆出于我东亚国也。若罗马教皇乎,亦可谓东西两大教宗,略相类者也。然教皇事权太大,又公举而非出一家,仍不若日本天皇尤为坚固矣。且立宪君主,实非君主而大世爵耳,不过于公之上加二级为皇帝耳。孔子尝有尊号曰文宣王、文宣帝,衍圣公不过加二级,袭此文宣帝之爵号耳,仍是大世爵也。”[7]
于是我们看到,其时康有为提出的救亡主张是:“今各省公尊孔氏衍圣公为帝,或曰文宣帝,或曰衍圣帝,迎主北京,或迁都山东、南京、苏州。移资政院从之,即改为国会,先召集各省咨议局议员与资政议员,并为国会议员,公议大政,公举百揆(即总理大臣),公订外约。则秩序不紊,争乱可泯,中国犹可保存也。”[8]
在稍后的《共和政体论》中,康有为又对“立衍圣公为帝”的主张作了一点修正,主要是将原来设想的帝号改为监国摄政王或监国总统之号,而其主要关切则是康有为念兹在兹、强聒不已的合满、汉、蒙、回、藏一统之而为一新中国之义:
“虽然,衍圣公尊为帝,合于汉族之人心矣,惟虑非所以合蒙、回、藏诸族之心也,则彼拥旧朝而立国,必且托保护于俄,终则折而入焉。果若是,恐失三千四百万方里之地,且增北顾之忧矣。夫蒙、回、藏之地,几三倍于中华内地,且有千数百万之同胞焉。为争一冷庙木偶,而弃三倍内国之地与千数百万之同胞焉,物价太不值也,甚非策也!若尊为监国则两无碍矣。存皇帝之大世爵,而一切不相关,以保全蒙、藏,岂非策之至哉!夫今者举国皇皇,或断脰亡家,或竭思焦肺,皆以救中国而已。仆之素志,以为能保全中国者,无论何人何义,皆当倾身从之;苟不能保全中国者,无论何人何义,必不可从也。且夫中国者,兼满、汉、蒙、回、藏而言之,若舍满、汉、蒙、回、藏乎,则非所以全中国也。此义乎,尤吾国人所宜留意也。”[9]
如果关联于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时以衍圣公为孔教会之总理的设想,我们在此可以从其立衍圣公为共和国新君主的主张读出其国家建构理念的某种特别意谓。国教折中表达出来的政教思想一言以蔽之曰“政教并行,双轮并弛”,即政治制度方面开国会立宪法,教化制度方面立孔教为国教加信仰自由,而此处立衍圣公为共和国新君主的主张其实表明,康有为坚持中国应保留君主制,除了大一统这个最重要的政治关切之外,更多的考虑还在教化方面。
质言之,在康有为那里,即使是现代意义上的共和制国家,也绝不仅仅是一个政治概念,更是一个教化概念,而国教作为两千年来中国的一个实际存在的事实,作为中国之所以成为中国的内在根源,恰是中国这一国家之教化本质的直接体现,从而也是建设一个新的共和制中国所必须认真对待、充分重视的。[10]
于是我们看到,康有为正是根据这一点区分了“亡君统”与“亡国”:“然一国之存立,在其历史、风俗、教化,不系于一君之姓系也。……我中国虽屡更革命,而五千年文明之中国,礼乐、文章、教化、风俗如故也。自外入者,入焉而化之。……易朝改姓者,可谓之亡君统,不得以为亡国也。”[11]
其论亡国之道有四则曰:
“夫如何而谓之亡国乎?其道又有四。第一则尽灭其文字,绝其先民之感,以聋盲于新国之中。如西班牙之于墨西哥是也。班将葛爹之灭墨,取墨人之书史图画而尽焚之。今墨全国人,不复知有祖功宗德,不复知有先哲先民圣贤豪杰咏歌记载,今其所记诵咏歌尊法,皆班人也。此为亡国之第一等事也。第二则禁其旧文旧教,奴隶其人,苛酷其民,圈禁出入,不得仕宦,不预政权,如法之于安南。此为亡国之第二等。第三则奴贱苛征其民,讥禁其出入,其人民不得为头等医生、律师与夫大商、大工、仕宦,文官不能至县令,武官不得至千总,议院不得参政权。如英之待印度、缅甸,荷之待爪哇,而台湾人亦无仕宦政权。此为亡国第三等。第四则或禁其语文,或禁其买地,或禁其仕宦为政,如俄、德之待芬兰、波兰。此为亡国之第四等。”[12]
又论中国若亡则仅可免于亡国之第一等而不能免于亡国之第二、三、四等则曰:“若中国今日而亡国于外人乎,则必为芬兰、波兰、印度、安南、缅甸、爪哇、台湾,必不得为北魏、金、元与本朝之旧,可决之也,以今外人皆有文明化我故也。”[13]
我们知道,顾炎武当异族入主、朝代更替之际区分亡国与亡天下,亦是关联于教化之隆废,康有为当古今嬗变、列国竞争之时仍以教化之隆废区分亡君统与亡国,与顾炎武辞稍异而心极同。
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康有为主张新的共和制中国应当保留君主制,还有一个更直接的政治考虑,就是反对总统制而主张议会制。他根据他所了解的外国实行共和制的经验和教训,提出总统制实乃争乱之源,而设立一个没有实际政治权力的君主则可以“止争总统之乱源”,“令人但以笔墨口舌争宰相而已”。[14]
而且,他还指出,即使考虑到总统制容易招致争位之祸的问题而设立一个民选的总统,“以总统代表虚王,而不执政权,乃立宰相以执政,令政党但争宰相而不争总统,内阁变而总统不变”,以免于陷入无政府之祸与争总统之祸,亦非良策。在这一点上他举的例子当然是法国。[15]
关于虚君必以世袭而民选之总统不能当之之义,康有为言之昭昭:“盖虚君之用,以门地不以人才,以迎立不以选举,以贵贵不以尊贤。夫两雄必不并立,才与才遇则必争,故立虚君者,不欲其有才也,不欲其有党也,然后宰总百官以行政,乃得专行其志,而无掣肘之患一也。夫立宪之法,必以国会主之,以政党争之。若无虚君而立总统,则两党争总统时,其上无一极尊重之人以镇国人,则陷于无政府之祸,危恐殊甚。故虚君之为用,必以世袭,乃为久确而坚固。又必禁由于公选,乃无大党,而不必有才,乃不与宰相争权,而后内阁乃得行政,而后国乃可强。”[16]
此真可谓得古代“尊尊”之政道理念之精义也,又可与黑格尔的君主立宪思想比观。
回到君主立宪与虚君共和的异同这个问题。在写作于1911年12月的《共和政体论》中,康有为针对有人以“欧人分立宪、共和二义”为根据而提出的君主立宪非共和的看法,澄清君主立宪与虚君共和之间的关系。他首先指出,世界各国的立宪君主,“皆有命相之权,有特命上议院议员之权,有国会提议改正否决解散之权,更有统陆海军之权,而国会不能限制之”,即使是在被誉为“为万国之至良者”的英国宪法中,君主仍“实有各大权,无成文以限之”,只不过因“无成文之宪法”而使英王之权“久不行用”。
接着,他论及十九信条,指出十九信条之下的君主其实是像土木偶神、留声机器一样的共和之虚君,而不可谓之立宪之君主:“若吾国九月十三日所闻,十九条誓庙所颁,君主一切无权,如同土木偶神,如同留声机器,实同无君,岂能谓为立宪君主哉?故只得谓共和之虚君也。”[17]
然后,康有为提出虚君共和乃为共和之一新政体,乃在“欧人立宪、共和二政体”之间,其与专制政体则若冰炭相反:
“夫但以君主论之,则专制与立宪皆有之,岂不相近哉?以民权论之,则立宪与共和实至近,虽有君主,然与专制之政体实冰炭之相反也。若共和之君主,其虚名为君主虽同,而实体则全为共和。夫凡物各有主体,专制君主,以君主为主体,而专制为从体;立宪君主,以立宪为主体,而君主为从体;虚君共和,以共和为主体,而虚君为从体。故立宪犹可无君主,而共和不妨有君主。既有此新制,则欧人立宪、共和二政体,不能名定之,只得为定新名曰虚君共和也。此真共和之一新体也。”[18]
由此可见,在康有为看来,虚君共和与君主立宪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或者说虚君共和乃是君主立宪在制度安排方面的更彻底的推进。
以英国的君主立宪制比之,就其对君主权力的限制方式而言,康有为所谓的虚君共和制是以成文宪法的方式明确限制君主的权力,而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则在很多方面还是通过不成文宪法,但就其对君主权力的限制程度而言,康有为所谓的虚君共和制与英国的君主立宪制没有多大差别或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与此相对应的是,辛亥以后康有为的孔教建制主张与国教折中所反映出的他在戊戌流亡以后的孔教建制主张在实质性上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国教折中表达出的“政教并行,双轮并弛”的核心思想,也是康有为辛亥以后的核心思想。
相比于戊戌流亡后的孔教思想,辛亥以后康有为孔教思想的变化首先表现在前后思想之侧重点的移动上。我们知道,康有为从一开始在《教学通义》中提出孔教建制主张,主要关切的是庶民的教化问题,而其思路则是通于治理而言教化,因此其孔教建制主张一直是从国家设置敷教之官的角度提出的。如果将后一点关联于康有为孔教建制主张的国家关切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从《教学通义》时期到戊戌变法时期,再到国外流亡时期,再到辛亥以后,康有为孔教建制主张中的国家关切越来越凸显,而其庶民关切则一仍旧贯。这一侧重点的移动自然与历史情境的变化有关。
在戊戌前后君主制的权威尚未被动摇的情况下,虽然国家设置敷教之官一直是康有为提出孔教建制主张的核心思路,但孔教在国家建构中所发挥的意义功能不是很突出;而在辛亥前后君主制的权威被彻底动摇的情况下,国家建构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从而孔教在国家建构中所能发挥的意义功能也会凸显出来。
具体来说,辛亥以后康有为的孔教思想主要是围绕共和建设的问题而展开的。关于共和建设的要目,在写作于1912年4月的《共和建设讨论会杂志发刊词》中,康有为有一个简明的回答,其中多项内容皆与孔教问题有关:
“大夫猎缨前席而问于学士曰:‘共和建设若何而可安全中国乎?’学士曰:‘必自统一之。’曰:‘若何而能统一之?’曰:‘必自中央集权,得强有力之政府始矣;必自各省勿分立,军民分权始矣;必自合五族,保辽、蒙、回、藏始矣;必自废军政,除强暴,遣冗兵,复民业始矣;必自定金币,拓银行,善其公债、纸币,奖实业始矣;必自奖教育、崇教化始矣;必自定良宪法,成大政党,得国会内阁之合一政党始矣;外之能适于万国之情形,内之能起国民之道德。’”[19]
在写作于1912年5、6月间的《中华救国论》中,康有为通过对“中国之旧法”中所立的“一统之制”的刻画,来说明包括中央集权、合五族、与民自由等义在内的中国“立国之本原”,所针对的则是暴民政治无视中国立国之本原而对共和的可能破坏:
“夫中国之旧法,虽有专制之失,而立一统之制,其所得者亦甚多也。盖非前朝能为之,实中国数千年政俗所流传也,经累朝之因革损益,去弊除患,仅乃得之。今亦不暇枚举,但言今所最反之四事焉:其一则各省咸奉中央之命,故千年无悍将、叛吏、骄兵争变之事也。其二则行政宽大,禁网疏阔,民得自由,故士农工商咸安其业也。其三则纪纲虽不严整,而人自懔威,法律虽未完备,而人自畏法,故下之无遍地劫掠之事,上之无属吏劫上司、匹夫乱公议之事,人民生命财产,皆得保全也。其四则蒙、藏辑和,虽为强邻所窥,统犹一于声灵也,即官吏不用本地人,亦经二千年鉴戒,而后立此制焉。其所缺者,物质文明、民权平等耳。虽未能盛治,然能保人民之生命财产,则先得立国之本原,而为今暴民政治所不及矣。”[20]
就是说,在康有为看来,除了物质文明和民权平等这两个方面需要多加借鉴、采用西方的经验之外,其他方面则必须认真对待、充分考虑“中国之旧法”的积极意义。[21]
而孔教作为两千年来中国的国教显然也属于“中国之旧法”的内容之一。在《中华救国论》中,康有为再次重申了他在国教折中的主要思想。
其论中国宜行政教分离曰:“故各国皆妙用政教之分离,双轮并弛,以相救助。俾言教者极其迂阔之论以养人心,言政者权其时势之宜以争国利,两不相碍而两不相失焉。今吾国亦宜行政教分离之时矣!”[22]
其论立孔教为国教不碍信仰自由曰:“盖孔子之道,敷教在宽,故能兼容他教而无碍,不似他教必定一尊,不能不党同而伐异也。故以他教为国教,势不能不严定信教自由之法。若中国以儒为国教,二千年矣,听佛、道、回并行其中,实行信教自由久矣。然则尊孔子教,与信教自由何碍焉?”[23]
其论全国宜遍立孔教会、宜以旧学人士不欲入政党者为教官之任曰:“然则今在内地,欲治人心、定风俗,必宜遍立孔教会,选择平世大同之义,以教国民。自乡达县,上之于国,各设讲师,男女同祀,而以复日听讲焉。讲师皆由公举,其县会谓为教谕,由乡众讲师公推焉;其府设宗师,由县教谕公推焉;省设大宗师,由府宗师公推焉;国设教务院总长,由大宗师公推焉。夫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今若上之政府举之,收效可速,不尔则国之志士,守死善道,应以为任矣。夫今之人士,多有笃信好学、砥行尚节、不能适于新世之用者,彼不欲哗世竞争,则不入政党,而选举亦不能及焉,是亦有遗贤之憾也。若以任教,则不废其才能,可益厉其学行,世道人心,获益多矣,可不务乎?”[24]
值得指出的是,在《中华救国论》中,康有为还发一新义,即将政党建设与孔教关联起来。
他首先指出政党内阁“为立宪治之极轨”,而政党内阁的形成端赖大的“良政党”。
鉴于辛亥以来政党像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的实际状况,康有为以阴阳之义“推国会之天理”,提出国会中的政党不要太多,最好只有两个大的政党:
“要而论之,党少者国安,党多者国危,党尤多则国可亡。若仅两党,则人与天合,国以富强,在朝在野,旗鼓相当。以大党立朝,则党势坚而行政强;以大党在野,则朝党不敢专制而为殃。且凡政党者,必持其一政策也,而时势变易,前策或有未宜者,他党代之,策适以相反而相补救,于以救国胹民,适得其和,如五声之异响而相宜,五味之异和而成调,协阴阳之宜、寒暑之变,岂不谐哉!故国宜有两政党而不可多政党,宜有大政党而不可多小政党也。”[25]
那么,如何才能建成“勿存私心,勿矜意气,专念国家之急”的大的“良政党”呢?
康有为说:“今吾国人将欲成良政党乎?其道有二:一曰输进通识也,一曰崇奖道德也。”关于“输进通识”,康有为强调,既然我们“生当海通之世,为共和之国”,则应当“知万国之情状”,方可“解共和之真义”。[26]
关于“崇奖道德”,康有为首先引孟德斯鸠、勃拉斯等人的看法指出道德对于共和建设的重要性:“共和国尚道德。……无道德则法律无能为。……盖共和自治者,无君主、长上之可畏,则必上畏天,中畏法,内畏良心;有此恭敬斋戒之心,然后有整齐严肃之治。不然,则暴民横行而已,盗贼乱国而已。自由自由,由此而死,何共和之足云?我大夫君子、邦人诸友,必立此道德之严戒,而后可受共和之幸福也。”[27]
接着他指出,舍孔教则不能崇奖道德:“夫将欲重道德之俗,起畏敬之心,舍教何依焉?逸居无教则近禽兽,今是野蛮之国,犹有教以训其俗,岂可以五千年文明之中国,经无量数先圣哲之化导,而等于无教乎?今以中国之贫弱,及前清之失道,人民慕欧思美,发愤革而易其政可也,然岂可并数千年之教化尽扫而弃之?今者邦人,慓悍恣睢,礼俗荡然,无所率由,人心发狂,无所敬忌,上类于无政府,下类于无教,虽无诸文教之国,以相比较,以相窥迫,亦所谓与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28]
由引文可见,康有为在此是将孔教作为建设优良政党的精神资源,或者说孔教在此是被他作为一种优良的政党教化或更广泛意义上的政治教化来看待的。在戊戌之前和流亡之后,康有为曾发起、建立过一些组织、团体,这些组织、团体大都非常重视孔教的意义,而在不同程度上又都具有政党的性质。
辛亥以后,康有为鼓动陈焕章建立孔教会,其中也有建立政党的考虑,确切地说,他鼓动陈焕章建立孔教会的一个动机正是有鉴于建政党之难。
在1912年7月30日就建立孔教会一事写给陈焕章的信中,康有为说:“今为政党极难,数党相忌,以任之力半年而无入手处。弟海外新还,始附党末,我始为仆,几时树勉难矣。昔弟在美,以行孔教为任,研讲深明。今若以传教自任,因议废孔之事,激导人心,应者必易,又不为政党所忌,推行尤易。凡自古圣哲豪杰,全在自信力以鼓行之,皆有成功,此路德、贾昧议之举也。及遍国会,成则国会议员十九吾党。至是时而兼操政党内阁之势,以之救国,庶几全权,又谁与我争乎?”[29]
关联于他立孔教为国教的主张,我们可以顺此概括说,共和时期康有为的孔教论至少有三义不能忽视:
其一,孔教为中国成立、得以维系的历史根源,即国魂;
其二,孔教为建设优良政党、成就政党内阁的精神资源,即政党教化;
其三,孔教为振起国民道德、改善社会风俗的文明本源,即国民教化。
以孔教为国魂的看法,多见于康有为辛亥以后的论述,其中最全面的一个论述见诸1913年2月11日的《<中国学会报>题词》:
“夫所谓中国之国魂者何?曰孔子之教而已。孔子之教,自人伦、物理、国政、天道,本末精粗,无一而不举也。其为礼也。陈之以三统,忠、质、文之迭代也;其变易也,通之以三世,据乱、升平、太平之时出也。体之以忠信笃敬,而蛮貊可行;张之以礼义廉耻,而国维不败;推心于亲亲仁民爱物,则仁覆天下矣。立本于事天、养心、尽性,则天人一致矣。其直指本心,至诚无息,必自慎独发之,无使隐微之有馁也;其原本天命,上帝临汝,则必自照临有赫,无使旦明之贰心也。自其中庸言之,则以人为道,被服别声,饮食男女,不离人以为道。故曰道不可须臾离也。自其深微言之,则原始反终,而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而知鬼神之情状。故自鬼神、山川、昆虫、草木,皆在孔教之中,故曰范围天地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也。善夫庄生之尊孔子为神明圣王也,曰‘本天地,育万物,本末精粗,四通六辟,其运无乎不在’。故据一端、执一说以论孔子者,若戴五色之镜,以论日月之青黄也;如测浑天之仪,以论恒星、游星之形体也。其茫茫无睹,不待言矣。”[30]
孔教国魂义亦关联于康有为对主权的看法。康有为认为在列国竞争的世界局势下,主权在民论不合时宜,主权在国论最值得提倡:
“夫政治之体,有重于为民者,有重于为国者。《春秋》本民贵、大一统而略于国,故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盖天下学者多重在民,管、商之学专重在国,故齐、秦以霸。法共和之时,盛行天赋人权之说,盖平民政治,以民为主,故发明个人之平等自由,不能不以民为重,而国少从轻也。及德国兴,创霸国之义,以为不保其国,民无依托,能强其国,民预荣施,以国为重,而民少从轻。夫未至大地一统,而当列国竞争之时,诚为切时之至论哉!日本采德制,以国为重,故秩序纪纲严整,税租甚重,一战胜我及俄而取高丽焉。今以美之共和,而自麦坚尼、罗士福以来,亦复大昌霸国之义。”[31]
虽然这里的考虑主要是政治方面的,即对外有鉴于列国竞争的世界局势而推重霸国之义,对内为免于暴民政治而主张强有力的政府,但既然孔子之教为中国之魂是康有为由来已久的一个看法,且康有为很早就将保教与保国紧密联系在一起,那么,康有为选择主权在国论而非主权在民论自然也与孔教国魂义密切相关。
与上述三义都有一定关联的,是康有为孔教论的另一义,即他非常重视在政治的层面看待孔教的意义,以孔教为能够培养优良政治风气的政治教化。此义见诸写作于1913年3月的《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
在谈到国会两院之设立“取法于权衡”而以“得其中平”为上时康有为以他对西方政治制度的了解刻画了两院之差异与其相反相成之用:
“夫国会只为发民意耳,然不为一院制而立两院制者,其原理正为取法于权衡也。下院议员来自田间,阅历浅而意气盛,故勇于更革,其去淤更新所长也,偏激妄诫易致倾危,此其短也;上院议员出自贵族、大僧、重臣、硕学、富商,皆老成阅历,多于保守,其谨慎稳重所长也,而守旧太过,或失进化,此其短也。二者如水火之相反而相成,如舟车之异器而同用,如车之以双轮而能驰也;偏重则倾,失一则不能行矣。凡国之立法,与人之用情,未有能外于进化与保守者也。二者调和而得其中,则国与民受其福,若英是也;有一偏重,至合立法、行政为一,则亦惟英为宜,施于他国,非惟不能,亦未必宜,或恐乱也。”[32]
然后,康有为以英国之政俗为例,指出优良的共和实有赖于有德之君子,若以平等之名而抹君子野人之别则难免于“暴民之乱”这个共和的最大危险:
“英人之俗,以旃度冕(Gentlemen)为尚,所谓养成士君子之器,以学问知识、器宇门阀自别异于齐民。故其都人士在下院者,皆旃度冕之尤秀者为之,实一国之上流人也。其属地殖民遍日月所出入,既富则皆归于伦敦,而效旃度冕之风俗行为,否则不齿于中流。所谓既富则教,而化行俗美也。吾中国地大民众,十倍于英,未行强迫之教,又无工商之富,民生贫愚,暴贼满野,其程度低于英之齐民不知其倍数也。其在旧俗,有君子、野人之别,皆以君子治野人,以野人奉君子。自顷谬效共和,妄言平等,旧俗官僚人士,皆俯首低心,降而师彼暴民之俗矣。故酿成大乱,今后未已也。夫比户可封,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可谓平等矣;苟未至比户可封、人人有士君子之行时,古今万国,未有不以君子治野人者也。苟漫曰平等,而以野人治野人,或以野人治君子,能无乱乎?……吾国既未能化野人为君子,则必宜以君子治野人。”[33]
我们知道,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有一个独特的看法,即认为宗教是“美国最重要的政治机构”。此处康有为“宜以君子治野人”的思想与在他出生一年后去世的托克维尔的看法可谓异域同声,更何况,康有为还认为,与佛、耶诸教相比,孔教的政治关切更强:
“佛、耶二教虽美,而尊天养魂,皆为个人修善忏罪之义,未有详人道政治也,则于国无预也。惟孔教本末精粗、四通六辟,广大无不备,于人道尤详悉,于政治尤深博,故于立国为尤宜。”[34]康有为也多次申言为国若仅言政治不言宗教或教化则不足为计。在写作于1909年的《孔教总会弘道募捐序》中,康有为说:“夫佛教精微而寂灭,不宜于为治;基督尊天爱人与孔教近,而不事祠墓与中国俗异。若孔教以人为道,而铸范吾国数千年人民、风俗、国政者也。夫人之立身养魂,必于其习熟得所归宿。故父不父,子不子,夫不夫,妇不妇,乱舞傞傞。故在国则乱于国,在家则乱于家,在身则乱于身,以求危亡,岂不殆哉?故夫今之为国,必非仅言政治所能为计也。人皆无耻,奚政之为?”[35]
在应陈焕章之请而写作于1912年10月7日的《孔教会序》中,康有为说:
“或者慕欧思美,偏知政治之为国也。夫人有耳目心思之用,则有情欲好恶之感,若无道教以范之,幽无天鬼之畏,明无礼纪之防,则暴乱恣睢,何所不至。专以法律为治,则民作奸于法律之中;但以政治为治,则民腐败于政治之内。率苟免无耻、暴乱恣睢之民以为国,犹雕朽木以抗大厦,泛胶舟以渡远海,岂待风雨波浪之浩瀚汹涌哉?若能以立国也,则世可无圣人,可无教主矣。”[36]
与此相关的一点是,对于辛亥以来的共和危机,康有为的反应和判断与新文化运动的引领者们正好相反,形成鲜明对照。陈独秀认为“孔教与共和乃绝对两不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
“分明挂了共和招牌,而国会议员居然大声疾呼,定要尊重孔教。按孔教的教义,乃是教人忠君、孝父、从夫。无论政治、伦理,都不外这种重阶级尊卑三纲主义。……若是用此种道理做国民的修身大本,不是教他拿孔教修身的道理来破坏共和,就是教他修身修不好,终久要做乱臣贼子。我想主张孔教加入宪法的议员,他必定忘记了他自己是共和民国的议员,所议的是共和民国的宪法。与其主张将尊崇孔教加入宪法,不如爽快讨论中华国体是否可以共和。若一方面既然承认共和国体,一方面又要保存孔教,理论上实在是不通,事实上实在是做不到。”[37]
康有为则认为教化革命正是共和在中国之所以难行的根本原因:“外人谓,夫中国之难行共和也,以今兹之革命,非止革满洲一朝之命也,谓夫教化革命、礼俗革命、纲纪革命、道揆革命、法守革命,尽中国五千年之旧教、旧俗、旧学、旧制而尽革之;如风雨迅烈而室屋尽焚,如海浪大作而船舰忽沉。故人人彷徨无所依,呼吁无所诉,魂魄迷惘,行走错乱,耳目不知所视听,手足不知所持行,若醉若狂,终之惟有冷死沉溺而已。若今之中国,其情实已然也。”[38]
从后来的历史看,以批孔、废孔为主要关切的新文化运动导致的结果是共和根本不可能行于中国,从而成为中国走向党—国体制的重要原因。
在《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中,康有为在宪法的框架中再一次提出了立孔教为国教的主张,其内容与国教折相同处甚多而又发新义,更特别强调了孔教“敷教在宽”的特点。草案第十一章为“人民”,其中第九十六条曰:
“凡国民苟不扰治安,不害善俗,不妨民事政事之义务者,许其信教之自由。而以孔教为国教,惟蒙藏则兼以佛教为国教。其特别之制,以法律规定之。”[39]这里比较特别的是康有为在主张立孔教为国教的同时提出“蒙藏则兼以佛教为国教”。
对此,他举“瑞士常奉三教为国教”为例并进一步申论说:“君子治国,不求变俗,谨修其故而审行之。佛之博大精微,又能明罪福以劝戒,入中国久远,相安久矣。故在中国,以孔子为国教,在蒙藏兼以佛为国教,并得其宜,有何碍哉?”从康有为的角度来看,自然这一点也是孔教敷教在宽的具体表现。
康有为言孔教之“敷教在宽”,又多引历史事实,指出历史上一些服膺儒教的士夫同时亦兼信他教而两相无碍:
“盖孔子只言公理,敷教在宽,不立独信之规条,不为外道之排斥。故自汉武帝定孔子为一尊,立六经于学官,立博士弟子诵之,与以甲乙科之出身,其诸不在六艺之科者绝勿进,盖定孔子为国教矣。而明帝临雍讲学,尊儒最盛,亦即遣白马驮经,迎僧竺法腾于身毒,而立白马寺。谢安、郗鉴,皆服膺儒术,而皆受五斗米道。徐光启、李之藻,于儒教中学行并高,而先传耶教。盖千余年中,孔教之君相士夫,多兼学佛理、崇老氏者。……诚哉!以敷教在宽,免二千年争教之巨祸,此孔子之大德,而为今文明国家之良法也。”[40]
更有甚者,在康有为1912年10月为孔教会所写的章程中,有一条说到奉孔教者同时亦可以奉他教:“孔子言敬敷五教在宽,孔子言人道,饮食男女,本不可离。既无人能离孔教者,则他教之精深新理,如佛教之养魂,耶、回之尊天,本为同条共贯。奉孔教者,凡蒙、藏之奉佛教,新疆、云南之奉回教者,不妨兼从。”[41]
指出历史上服膺儒教的士夫同时兼信他教而两相无碍是一回事,在建立孔教会的章程中规定奉孔教者同时亦可以奉他教则是另外一回事。既然此条特别关联于蒙、藏、新疆、云南等佛、回之教流行之地,那么,除了感叹此章程的确体现了敷教在宽的特点,我们对康有为的孔教主张与其“合满、汉、蒙、回、藏一统之而为一新中国”的国家关切之间的关联亦见之甚明。
《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中的国教条也就国教的制度设置做了非常简略的规定:“一、崇体制。总统与行政官、地方长吏,春秋及诞日大祭,朔望祠谒,学校奉祀,皆行三跪九叩礼。二、立学设学位。大、中、小各学皆诵经,大学设经科,授以学位,俾经学常入人心,其学校特助以经费。三、立教会。国家特保护而助以经费,或设教院专司宏导。”[42]
这里关于国教制度设置的规定的确是太过简略,其中有一点需要特别指出。我们知道,《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并不是按照康有为的虚君共和主张写成的,因为其时康有为知道虚君共和不可能被接受。问题就出在这里。在君主立宪制的前提下考虑国教的制度设置,即使君主像康有为在阐述虚君共和制时所说的只是一个“土木偶神”,在国教与政治系统如何勾连的问题上也比较简单,往往是以君主为国教名义上的首领,比如英国国王就是英国国教名义上的首领,日本天皇就是神道教名义上的首领,就是说,正是通过君主,国教与政治系统在制度安排上获得了勾连。如果不是以君主立宪制或虚君共和制为前提,那么,国教与政治系统在制度上如何勾连的问题就需要重新加以考虑。
很显然,《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有关国教制度设置规定的一个比较明显的缺陷正在于没有明确论及这个问题。
这个规定的一个特别之处,是强调了学校设立经科这一条。1904年,张之洞、张百熙等主持的《癸卯学制》颁布,大约也是从那时起,康有为屡屡强调学校读经的重要性。1912年1月,中华民国教育部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其中规定小学废止读经科。1912年4月,蔡元培发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明确反对学校读经,该意见随后成为教育部制定教育政策的理论根据。因此,康有为在《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中强调学校设立经科是有明确的针对性的。
但之后的情况并没有什么改观,到1913年8月《壬子癸丑学制》颁布,大、中、小学的经科皆被废止。在1916年9月写给当时教育总长范静生的信中,康有为专门针对“各国小学皆不读其教之经,则我何妨取法之”的论调进行了反驳。
他的核心看法是,在读经问题上,“我国必不可法欧美之小学,盖有二焉”:“夫欧美之学校之可不读经,以其人人皆被教会之教而无人不已读经也;学校之不读教经者,以其不切于治,而非同孔子之经之治教兼备也。”[43]
其申论中国无教会故应当在学校设读经科曰:“吾国既无教会之特别学堂,又无神父、牧师之家喻户晓、七日宣讲,又无人民之七日礼拜拳跪读经,若吾国果禁读经也,则驱全国之儿童、国民子弟终身不知有经。则二三十年后,经必绝于天下。此其为灭孔教之法,诚至捷矣,其如全国人心风俗将何归乎?”[44]
其申论佛、耶之经不切于治而孔教之经与之有异故不可不读则曰:“且夫孔子之经与佛、耶之经有异。佛经皆出世清净之谈,耶经只尊天养魂之说,其于人道举动云为,人伦日用,家国天下,多不涉及,故学校之不读经,无损也。若孔子之经,则于人身之举动云为,人伦日用,家国天下,无不纤悉周匝,故读其经者,于人伦日用,举动云为,家国天下,皆有德有礼,可持可循。故孔子之教,凡为人之道。故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若不读经,则于人之一身举动云为,人伦日用,家国天下,皆不知所持循。孰是孰非,孰从孰违,伥伥乎何所知,茫茫乎何所归。无教之人,魂失凭依,举国之人而失魂也,何以立国为?”[45]
由此可见,康有为强调学校设立经科,一方面是鉴于孔教缺乏面向民间的敷教制度——我们知道,这是康有为在《教学通义》中提出来的一个一直非常重视的制度关切,另一方面,则是激于民国不断废止经科的政治现实。陆宝千曾说:“然长素于民国初元所以大声疾呼以孔教为国教者,尚有内激之因缘,则政府之明令废孔是也。”[46]
实际上,康有为辛亥以后有关孔教的很多方面的言说和行动都是激于当时毁文伤教的政治现实。[47]在写作于1913年5月的《覆教育部书》中,康有为针对教育部明令孔庙学田充公这一事件,质问说:
“闻自共和以来,百神废祀,乃至上帝不报本,孔子停丁祭,天坛鞠为茂草,文庙付之榛荆。钟虡隳顿,弦歌息绝,神徂圣伏,礼坏乐崩,曹社鬼谋,秦庭天醉。呜呼!中国数千年以来,未闻有兹大变也!顷乃闻部令行饬各直省州县,令将孔庙学田充公,以充各小学校经费。有斯异政,举国惶骇。既已废孔,小学童子,未知所教,俟其长成,未知犹得为中国人否也,抑将为洪水猛兽也。呜呼哀哉!何居我闻此政也,抑或误效法国之革命,举教产以充公乎?则彼新旧教争,所毁者教皇之旧教耳,其敬奉者固在路德之新教也,其尊基督如故也。犹吾国昔逐荀子、郑康成于文庙外,而尊孟子、程、朱云耳,于孔子无损也。今乃公然收文庙之祭田,则是直欲废黜孔子矣。在诸公久停丁祭,不敬已久,宁在此举。然贵部主持教化,教者文行忠信,不知以何为教?育者果行育德,不知以何为育也?”[48]
此内激之因缘亦牵涉到与民俗有关的其他宗教。写作于1913年2月的《议院政府无干预民俗说》就是康有为针对民国破坏民俗的现实而发,其中特别谈到宗教问题,呼吁政府保护各种宗教在中国社会的自由发展。他以广东的情况为例,说明民国破坏民俗的状况的严重性,比如在谈到“藉口破神权之故,而破人民之财产生计”时他说:
“如七月锁城隍庙门,扭庙之神头;毁黄大仙祠,以铁练锁黄大仙而枪击之,又投诸河。禁神诞,禁打醮,禁烧衣,捉喃巫者,令穿道衣下狱半月。因此之故,业香纷香烛贩檀香者失业。芳村生花失业,陈村碧江元宝金银纸失业,致数万人无所衣食。佛山五色衣、纸神镜、神花、神位、金银纸、醮料失业,全佛山男女数十万以神事为业,今则数十万人无所衣食。盐步大沥制爆竹者十数万人失业,男妇无所衣食。尤可惊者,甚至烧阴骘文版,而龙藏街全街店铺失业,善堂无以为劝讲之计,小民无自闻劝善之言。”[49]
然后,他指出宗教乃风俗之源,根据宪法政府不应当干预:
“至于神道设教,尤为大义。管子所谓‘不明鬼神则陋民不悟’,孔子所谓‘明鬼神以为黔首,则百官以畏,万民以服”。至于各教,有一神多神之异,此乃立法之少殊。至于鬼神为德,在上在旁,以临悚人民,惩恶劝善,俾之斋明诚祀,其义一也。日本变法盛强至近矣,而神庙数万,植有松村六百户,而神社五百余者,政府何尝过问之。今即天主之教,何尝不燃矩过百,陈灯光明,而后为祭哉?此为宗教之事,风俗之源,尤非政府所能干预。若以握一日之政权,遂敢妄行,明背宪法,至令数十万人衣食于是者一旦尽失,试问宪法所以谋人民之安宁幸福者安在哉?”[50]
康有为建言保护佛教、道教及其他各种宗教,与他立孔教为国教加信仰自由的政教主张是完全一致的。令人慨叹不已的是,民国以前,至少从1895年公车上书开始,康有为屡屡呼吁朝廷将不在祀典的淫祠废掉,改为孔庙或学校,而民国以后,随着科学观念的影响僭越性扩展到人生观的问题上,孔庙——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宗教的行教场所——却被当作类似于淫祠一样的东西废掉了。
另外,在孔教会主导的定孔教为国教的运动中,其他宗教有反对者,亦有支持者,其中反对声音最大的来自基督教界。[51]而在民国初年针对孔教的行动中,基督教界非常有效、充分地利用了孔教是不是宗教这个引起争议的话题:从1912年3月11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颁布后,基督教界屡屡以其中“人民有信教之自由”的条款呼吁废孔,其根据则是以孔教为宗教;而在两次国教运动中,基督教界又以孔教非宗教为其反对定孔教为国教的主要理由之一。[52]
就是说,基督教界的策略是,在废孔的时候把孔教作为宗教看待而以信教自由非难之,在反对定孔教为国教时则又说孔教非宗教故不能定为国教。以至于后来达到如此地步,1917年5月4日,不仅是定孔教为国教的议案被宪法审议会否决,而且,竟然在将1913年宪法草案第19条第2项“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撤销的基础上又将第11条“中华民国人民有信仰宗教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受限制”的条文改为“中华民国人民有尊崇孔子及信仰宗教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受限制”。这一改动意味着宪法不得不专门就尊崇孔子的自由做一规定,可见当时孔教处境的艰难。
然而,很快在随后的1920年代,基督教界就遭遇了来自中国社会、特别是由活跃的知识阶层主导的、对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产生很大影响的非基运动。非基运动除了诉诸基督教与西方列强的帝国主义之间的明显关联之外,宗教与科学的对立也是持论者所诉诸的一个主要理由。
虽然从表面上看,后来的非基运动与早先国会否决定孔教为国教的宪法事件没有什么关联,但试想一下,如果定孔教为国教的议案被通过,就是说,康有为立孔教为国教加信仰自由的政教主张得以实现,那么,服膺孔教的人士则不会在非基运动兴起之时保持沉默,因为他们与那些持科学主义态度的激进人士不同,深知宗教对于现代生活——无论是个人的、还是国家的——的重要意义,不会认为宗教将随着科学的昌明和历史的进化而消亡。
因此,在一定意义上,遭遇非基运动也是中国基督教界废孔行动的自食其果,客观上也阻碍了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这一点尤其值得当下的基督教界深思。
结语:认真对待康有为的孔教思想
我们按照时间顺序梳理了康有为的孔教思想,将之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在康有为1890年会晤廖平之前,其时他还没有彻底确立他的今文经学立场,其中核心的文本是写作于1885-1886年的《教学通义》;
第二个阶段是从他确立自己的今文经学立场一直到戊戌变法,其中关于今文经学立场的核心文本是初刻于1891年的《新学伪经考》和问世于1898年的《孔子改制考》,而关于孔教建制主张的核心文本则是1895年的《上清帝第二书》(及《上清帝第三书》)和1898年的《请商定教案法律厘正科举文体听天下乡邑增设文庙谨写<孔子改制考>进呈御览以尊圣师而保大教折》;
第三个阶段是从他戊戌流亡后到辛亥革命前,其中代表性的文本是实际写作于1904年或稍后而收录在1911年出版的《戊戌奏稿》中的《请尊孔教为国教,立教部教会,以孔子纪年而废淫祀折》;
第四个阶段则是在辛亥革命后,其中代表性的文本是写作于1912年的《中华救国论》和1913年《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
理解康有为孔教思想的两对关键词是理学与经学、庶民与国家。以下我们顺此线索略加阐述。
首先,必须充分重视康有为提出孔教思想的理学基础。
我们已经指出,康有为的理学素养非常深厚,其特点概而言之是以朱学为主,兼采陆、王,在工夫论上则是以静坐为主。康有为孔教思想的提出,正是基于其独特的灵修体验。虽然后来康有为的经学思想有较大变化,其孔教建制主张在不同时期也有一些变化,但他终其一生对理学都有相当的肯定。
可以想见,来自理学的灵修体验对于他作为一个孔教的服膺者一直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此,如果我们要在当下的处境中考虑儒教的制度重建的话,那么,我们首先必须充分认识理学之于儒教的意义。
一种教化,如果缺乏直指人心的力量,而仅仅流于律法或礼仪,则很难真正发挥作用,特别是在现代社会。就此而言,理学对于儒教经典中的心性思想的深入阐发对于未来儒教的发展至关重要。
当然,就目前的实际状况来说,首先需要反思的是在现代人文科学的方法论主导下将理学彻底哲学化所带来的严重后果。直观而言,理学最重要的工夫论问题在哲学化的处理中遽尔变成了认识论问题。[53]
其次,康有为孔教思想的提出,关联于经学的重新开展,这也是我们应当充分重视的。
我们已经指出,即使是在写作《教学通义》的时期,康有为孔教思想的背后也有深厚的经学基础;而他后来阐述其今文经学立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更是明确地显示出经学之于教化的重要意义,尽管其中有很多论断是颇有争议的。
经学的存在,本身就关联于一个教化传统,或者说,经学是一个教化传统成立的根本要素。这一点提示我们,如果真正要复兴儒教,就必须考虑经学如何重新开展的问题。就此而言,经学在一个教化传统中所能发挥的主导性功能是现代人文科学根本无法替代的。
康有为孔教思想背后的理学基础和经学基础也促使我们思考如何基于儒教这样一个教化概念来理解理学与经学的关系。这当然首先涉及理学与经学在儒教中的不同定位。经学自然是儒教这个教化传统成立的根本,理学必须以经学为基础,这一点自然不需多说。那么,如何理解理学在儒教中的定位呢?
我们说,既然理学就其内容和功用而言主要着意于儒教教义的系统化和灵修工夫,那么,理学就其表现形态而言就属于系统儒学,相对于经学之为经典儒学。[54]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一点是,必须充分注意宋明理学背后的经学基础。学术界一个过分简单化的倾向是,往往从表面上将汉代经学与宋明理学对立起来,从而忽略了宋明理学背后——特别是宋学——的经学基础。
换言之,宋明理学虽然呈现出与汉代经学非常不同的面目,但理学的成立仍是以经学为基础的,只是理学背后的经学与汉代经学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尽管其连续性也不可忽视。而且,如果我们考虑到宋明理学兴起的背景是唐、宋以来中国社会的重要转型的话,那么,关联于现代这个以庶民为主体的时代,宋明理学那种重视个人心性的教化改革方案相比于汉代那种重视礼乐制度的教化建设方案对于儒教的现代复兴更具借鉴意义,尽管我们决不能忽略礼乐制度的重建无论对于个人还是国家仍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55]
再次,对于康有为孔教思想中的庶民关切,也是我们必须充分重视的。
我们已经指出,康有为最初在《教学通义》中提出敷教主张,其核心关切就是庶民问题。他以《尚书》、《周礼》等经典为依据,指出上古之治有庶民之教、士夫之教和官吏之教的区分,孔子以后则是士夫之教独兴而庶民之教和官吏之教皆亡。所以他的敷教主张一言以蔽之即恢复上古之治中的庶民之教。
《教学通义》中出于对庶民问题的关切而提出的以立教章、设教官、建教堂为主要内容的敷教主张,意味着康有为重新构想孔教建制的一个核心思路,后来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具体制度安排上的调整和充实。
就此而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国教折中人人祀天、人人祀孔的主张。联系过去的礼乐制度,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人人祀天、祀孔、祀祖先的三本一堂制度以及与此相关的以孔子为纪元等主张实际上是康有为直面庶民时代的到来而提出的教化制度方面最具实质意义、自然也是最为重要的改革措施。虽然后来孔教会的失败是我们必须认真反思、认真对待的一个问题,但康有为在教化制度方面提出的这些改革措施对于未来儒教的重建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最后,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康有为孔教思想中的国家关切。
我们已经指出,康有为的孔教思想,始终是从国家治理的角度展开的。在《教学通义》中,康有为主要以《周礼》中论述周代官制的思想为依据而提出设立敷教之官的制度主张。从官制的角度提出孔教建制主张,是康有为终生未变的思路。
在《上清帝第二书》、《请商定教案法律厘正科举文体听天下乡邑增设文庙谨写<孔子改制考>进呈御览以尊圣师而保大教折》以及《请尊孔教为国教,立教部教会,以孔子纪年而废淫祀折》中,康有为的孔教建制主张一言以蔽之是在地方设立各级教会而在国家一级改礼部为教部以统领之。在《中华救国论》和《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中,康有为的孔教建制主张一言以蔽之则是在地方设立各级教会而在国家一级设立教务院或教院以统领之。
除了这种官办教化的特别思路值得注意之外,我们还指出,康有为也非常重视孔教作为建设优良政党的政党教化以及更宽泛的政治教化的意义,毕竟,在中国古代,儒教首先是面向对国家治理至关重要、作为国家政治之主干的士大夫阶层的士夫之教。
不过,康有为立孔教为国教的思想中最重要的一点,还是其孔教国魂义。康有为明确指出,孔教与中国不可分离,从历史上看,孔教是中国成立的内在根源,无孔教则无中国。孔教国魂义往往被简单化地、仅从文化的角度去理解,即仅看到孔教作为影响中国几千年历史的文化传统的重要意义,特别是孔教在国民心理和国民性格的形成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如果把政治的角度也考虑进来,那么,对孔教国魂义的理解会加深一层。既然在历史上儒教是中国成立的内在根源,是几千年中国得以维系的一个主导性的、具有强烈政治意味的教化传统,那么,我们必须谨慎思考中国这个维系了几千年的历史国家(historical state)的根本性质。以民族—国家的概念来理解中国的性质显然不恰当,对此学者已经提出了非常有力的质疑。[56]
不过,以西方意义上的帝国来理解中国仍然有很多不合适之处。实际上,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理解中国这个维系了几千年的历史国家最恰当的概念是文教—国家。更进一步,既然我们已经意识到,以革命的方式和面目建立起来的现代中国其实是古代中国的自我转化,那么,我们必须思考儒教在现代中国国家建构中的意义。
就此而言,立孔教为国教运动的失败可能仅仅意味着中国在迈向共和时代的途中所走的一段弯路,而共产主义作为有效地建立了一个现代中国的政治信仰就其功能而言恰是过去儒教的替代物。
于是,一连串的问题迟早会摆在每一个有理性的中国人面前:如果共产主义的信仰危机在根本上无法克服,那么,中国将何去何从呢?
中国是否能够感受到自身的内在需要而决意恢复其文教—国家的本来面目呢?
如果中国不能恢复其文教—国家的本来面目,是否将面临混乱和分裂的危险呢?
如果中国决意恢复其文教—国家的本来面目,那么,在政治制度的安排上又如何才能做到措置得宜呢?
而要恰当地回答这些问题,康有为的孔教思想无疑是最有借鉴意义的。
注释
[1] 见《康有为全集》第九集,第259页。
[2] 我们知道,在经典的用法中,禅让与革命恰恰是两种极为不同的政权更迭方式,对应于上古历史的不同阶段:尧、舜、禹为禅让,夏、商、周为革命;在《礼记·礼运》中二者的差异被刻画为大同与小康。
[3] 见《康有为全集》第九集,第259页。
[4] 见《康有为全集》第九集,第268页。
[5] 见《康有为全集》第九集,第237页。
[6] 见《康有为全集》第九集,第238页。在《共和政体论》中,康有为曾提到旧朝旧君亦是新君主之人选:“夫今欲立此木偶之虚君,谁其宜者,谁其服者?……则举国之中,只有二人:以仍旧贯言之,至顺而无事,一和而即安,则听旧朝旧君之仍拥虚位也;以超绝四万万人之地位,而民族同服者言之,则只有先圣之后,孔氏之世袭衍圣公也。”见《康有为全集》第九集,第248页。
[7] 见《康有为全集》第九集,第237页。
[8] 见《康有为全集》第九集,第238页。
[9] 见《康有为全集》第九集,第249页。
[10] 无论过去还是将来,孔教皆关乎中国之存亡,此义康有为在稍后的《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中言之至明:“夫古文明国,若埃及、巴比伦、亚述、希腊、印度,或分而不能合,或寡而不能众,小而不能大,或皆国亡而种亦灭。其有万里之广土,四万万之众民,以传至今日者,惟有吾中国耳。所以至此,皆赖孔教之大义结合之,用以深入于人心。故孔教与中国结合二千年,人心风俗浑合为一,如晶体然,故中国不泮然而瓦解也。若无孔教之大义,俗化之固结,各为他俗所变,他教所分,则中国亡之久矣。夫比、荷以教俗不同而分,突厥以与布加利牙、塞维、罗马尼亚、希腊诸地不同教而分立,亦可鉴矣。故不立孔教为国教者,是自分亡其国也。盖各国皆有其历史风俗之特别,以为立国之本,故有孔教乃有中国,散孔教是无中国矣。”见《康有为全集》第十集,第82页。
[11] 见《康有为全集》第九集,第232页。
[12] 见《康有为全集》第九集,第232-233页。
[13] 见《康有为全集》第九集,第233页。
[14] 见《康有为全集》第九集,第235页。
[15] 见《康有为全集》第九集,第244页。
[16] 见《康有为全集》第九集,第245页。
[17] 见《康有为全集》第九集,第247页。
[18] 见《康有为全集》第九集,第247页。
[19] 见《康有为全集》第九集,第290页。
[20] 见《康有为全集》第九集,第290页。康有为认为共和制最大的危险在于暴民政治,如我们所知,在现代西方政治思想史上,此一洞见诸托克维尔和密尔的著作。
[21] 康有为1904年有《物质救国论》之作,阐述欧美富强之道在物质文明与民权平等,其中作于1905年3月的序曰:“吾既遍游亚洲十一国、欧洲十一国,而至于美。自戊戌至今,出游于外者八年,寝卧寖灌于欧美政俗之中,较量于欧亚之得失,推求于中西之异同,本原于新世之所由,反覆于大变之所至。其本原浩大,因缘繁多,诚不可以一说尽之。欧洲百年来最著之效,则有国民学、物质学二者。”见《康有为全集》第八集,第63页。
[22] 见《康有为全集》第九集,第327页。
[23] 见《康有为全集》第九集,第327页。
[24] 见《康有为全集》第九集,第327页。
[25] 见《康有为全集》第九集,第324页。
[26] 见《康有为全集》第九集,第324页。
[27] 见《康有为全集》第九集,第325页。
[28] 见《康有为全集》第九集,第325页。
[29] 见《康有为全集》第九集,第337页。
[30] 见《康有为全集》第十集,第16-17页。
[31] 《中华救国论》,见《康有为全集》第九集,第310-311页。
[32] 见《康有为全集》第十集,第69-70页。
[33] 见《康有为全集》第十集,第70页。
[34] 见《康有为全集》第十集,第82页。
[35] 见《康有为全集》第九集,第115页。
[36] 见《康有为全集》第九集,第343页。
[37] 陈独秀:《旧思想与国体问题》(1917年5月1日),见《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4页。
[38] 《中国以何方救危论》(1913年3月),见《康有为全集》第十集,第35页。从前面的引文看,陈独秀认为就孔教的教义而言三纲主义是破坏共和的主要思想根源。康有为也承认来自孔教的宗族观念与共和危机具有一定的关联。我们知道,康有为有鉴于中国分裂的危险而一直反对联邦制,于是有《废省论》之作。在对辛亥以来“藩镇割据”之封建局面的分析中,康有为提到了宗族观念:“若我国人,皆有宗族,俗多土著,属多亲戚,律非个人独立,即使贤者为政,而为亲属强逼,或为长者压制,瞽叟杀人,岂能执之?封建之亲贵,土司之官亲,其祸可戒。况今长吏多起寒微,其宗族、亲属人已万千,多饥寒交迫无定者,忽藉都督之势,有同国王之亲,怙势横行,何所不至?是有一都督,不啻有百千都督;有一知事,不啻有百千知事也。且既为土著,联合甚易,在位既久,根连滋满,凭借深厚。方今开国之始,僭争留后,其不酿成唐之藩镇不止。积日既久,负固益深,吴元济以淮西四镇之地,而竭唐之全力,四十余年乃能去之。况于一省之大,而又可与诸省联合者哉?”《论共和立宪》(1913年),见《康有为全集》第十集,第174页。关联于康有为思想的其他方面,虽然他承认共和危机与宗族观念有一定的关联,但就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而言他与陈独秀破除三纲的主张完全相反。如果我们简单地重述其核心主张的话,大概有两方面是必须提到的:首先,他会肯定来自孔教的家庭、家族观念对于共和有着至关重要的积极意义,其次,他会指出,藩镇割据的问题关键在于家族观念之上缺乏一个大一统的国家观念,而导致这个局面的主要因素就是君主制的废除,就是说,恰恰是三纲中的君臣之义的缺失,要为当时的共和危机负责。
[39] 见《康有为全集》第十集,第81页。
[40] 见《康有为全集》第十集,第82页。
[41] 见《康有为全集》第九集,第349页。
[42] 见《康有为全集》第十集,第83页。
[43] 见《康有为全集》第十集,第323页。
[44] 见《康有为全集》第十集,第322页。
[45] 见《康有为全集》第十集,第322-323页。
[46] 陆宝千:《民国初年康有为之孔教运动》,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八辑,1983年6月,第90页。
[47] 即使是1917年康有为参与张勋复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内激之因缘所导致的后果,特别是考虑到康有为在辛亥之变后对清帝退位的拥护态度。对此,曾亦说:“南海毕竟以民主共和为高,晚年虽以虚君共和适合国情,亦未必遽以复辟为惟一途辙,实民初废孔举措有以激成之也。”见曾亦:《共和与君主》,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82页。
[48] 见《康有为全集》第十集,第115页。
[49] 见《康有为全集》第十集,第24页。其列举的其他问题还有“藉口行新历之故,多人民之权利自由”、“藉口于讲卫生之故,而夺人民之财产生计者”、“藉口于改良风俗之故,而夺人民之财产生计,还人民之生命”、“藉口于欧美文明,而夺人民之财产与人民之自由”以及“藉口于平民主义而侵入人民之自由及家宅”等方面。
[50] 见《康有为全集》第十集,第25-26页。
[51] 曾亦说:“民初孔教运动的开展及失败,与基督教的活动有莫大关系。盖自清末预备立宪以来,基督教即试图在将制定的宪法中确立信教自由的条款。民国以后,随着孔教活动的开展,以基督教为主,包括佛、道、回在内的宗教界,积极努力,反对定孔教为国教,呼吁信教自由。基于反孔教组织的巨大声势,袁世凯表示,‘自未便特定国教,致戾群情’,‘至于宗教崇尚,仍听人民自由’。至于南方的孙中山,亦有信教自由的承诺。袁氏帝制失败后,陈焕章等再度试图在宪法中‘明定孔教为国教’,各地基督教乃组织政教分离请愿团、基督教公民宪法请愿团、信教自由会等,极力指斥孔教与帝制的关联,甚至称孔教乃中国近代衰弱之祸根,遂致孔教之国教化再度失败。”见《共和与君主》,第264页。另外,关于国教运动中孔教与其他宗教的关系,参见韩华:《民初孔教会与国教运动研究》,第十章。值得注意的是,两次国教运动中都有佛、道等宗教团体向参众两院请愿、上书,支持定孔教为国教,尽管在第二次国教运动中来自佛、道等教的反对声音加强,而其理由则曰:“孔教苟废,则各教必不能独存,应请列入宪法,定孔教为国教,庶与信教自由并行不悖。”见中国道教公会《上参众两院请定国教书》,载《尚贤堂纪事》,第10册第7期,1916年,转引自韩华:《民初孔教会与国教运动研究》,第249页。相比之下,两次国教运动中宗教界反对定孔教为国教的声音主要来自包括新教和天主教的基督教界。
[52] 这两个方面分别参加韩华:《民初孔教会与国教运动研究》,第23页以下和第240页。
[53] 观察这一变化的一个典型例子是贺麟在《宋儒的思想方法》一文中所表现出来的倾向,即以理智、直觉等认识论概念来刻画宋儒的工夫论思想,而这一倾向主导了现代以来几乎所有的宋明儒学研究。并不是说不能够用认识论概念来处理工夫论思想,而是说,如果工夫论思想在这种哲学化的处理过程中不再能够发挥其本来最重要的灵修功能,那么,这种处理就是非常成问题的。
[54] 我在《儒学研究的范式转移》一文中对此有较全面的阐述,该文见乐黛云主编:《跨文化对话》,2012年秋季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
[55] 当然,在此必须指出的是,就未来儒教的复兴而言,经典儒学和系统儒学的重建不可能是对过去经学和理学的简单重复。
[56] 白鲁恂说中国是“一个文明伪装成一个民族—国家”,汪晖则以“帝国的现代转化”理解现代中国的形成,参见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二卷。
【下一篇】【李长春】中国哲学研究的文明担当意识
作者文集更多
- 唐文明 著《隐逸之间:陶渊明精神世界··· 02-17
- 李天伶著《誓起民权移旧俗——梁启超早期··· 09-03
- 【唐文明】论孔子律法——以《孝经》五刑··· 04-07
- 【唐文明】定位与反思——再论张祥龙的现··· 12-29
- 唐文明 著《极高明与道中庸:补正沃格··· 09-15
- 【唐文明】三才之道与中国文明的平衡艺术 01-06
- 歌曲孔子版《孤勇者》(唐文明填词并注··· 09-09
- 唐文明 著《与命与仁:原始儒家伦理精··· 07-21
- 【唐文明】敬悼张祥龙老师 06-09
- 【唐文明】沃格林与张灏先生的中国思想··· 05-27
微信公众号
儒家网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

微信公众号
儒家网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