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朝晖】郭齐家:教育立命 修明心性
郭齐家:教育立命 修明心性
作者:储朝晖
来源:《光明日报》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十月初五戊申
耶稣2018年11月12日
1987年,郭齐家先生的第一部学术著作《中国教育思想史》问世。因为当时痴迷教育研究,我认真拜读全书,并做了详细的圈点和笔记。这是郭先生第一次在我脑海里留下的深刻印象。
1996年10月,桂子山丹桂飘香,华中师范大学召开陶行知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我第一次与郭先生相见,仍不敢奢望有朝一日能成为他的及门弟子。不曾想2001年,我幸运考入北京师范大学郭先生门下读博。“二十年前入陶门,二十年后入郭门。”1981年,我,一个物理系学生,迷上了陶行知;2001年,郭先生手把手把我“牵”进郭门。我突然发现,陶行知先生和郭齐家先生都是10月18日出生,于是惊异于上苍竟然安排得如此巧妙。

探索
1956年,郭先生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但直到1959年春,他才和同学们一起重回课堂,享受着教育系毛礼锐、陈景磐、邵鹤亭、瞿菊农四大教授同讲一门“中国教育史课”的大餐。
当时的郭先生总觉得,“教育史还是比其他课程深奥一些。尤其是中国教育史,又没有教材,老师讲到古代的东西,引用什么话,孔子什么、墨子什么就听得不是很明白。上课的时候没有教材,也没给我们发讲义,就在黑板上写了一些讲授的内容提纲。当时我们的古文水平也不高,老师要是没有板书,我们就更不知所云。实际上我们听了这些课程,真正记住的东西不是很多。要是上课前有个讲义或教材就会好一些。”
1960年7月,郭先生毕业后留在了北师大,在教育系教育学教研室任实习助教。而1961年4月召开的高校文科教材会议决定,由北师大教育系编写中国教育史教材,教育系把郭齐家从教育学教研室调入教育史教研室。他有机会给陈景磐、毛礼锐、邵鹤亭、瞿菊农四位先生当助手,借书、找资料,参与那时这一学科领域国内最强专业的团队工作。
毛礼锐先生后来说:“那时我就觉得他(郭齐家)是一位勤奋好学的青年,我有意培养他,给他压任务,让他早上讲台,果然有效果。”
为了编好这套教材,1961年6月,北师大陈垣校长出面邀请历史学家范文澜、翦伯赞、邱汉生、金灿然、林砺儒召开座谈会。郭先生回忆:“那次座谈会对于教育史教材编写来说,就是一个思想解放运动……给我们的教授们带来了很大的动力。”然而,这次思想解放并未一下子就修成正果,在经历了多次备课、讲课的循环后,教材生不逢时,总是出不来,直到1978年才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1977年,郭先生结束在武汉家中的养病再次回到北师大,被安排在资料室工作,1982年,他再次登上讲台。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学生积极性高,听课认真,这激发了郭先生对过去20多年中国教育史教学与研究的系统思考,为了给学生提供更丰富的教育史知识,他开始自己编讲义,将孔子、孟子等教育家关于教育对象、教育目的、教育方法的论述分别列述,条理清晰、资料翔实地呈现在课堂之上。
经过几轮教学修改充实,这些讲义成为郭先生的第一本专著——《中国教育思想史》,1987年由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郭先生在这部书中尽力解决此前对中国教育史简单化、单一化,批判多、肯定少的问题。
毛礼锐先生对这部“多年教学与研究的结晶”评价很高:“总的看,我觉得这本书写得是好的……既写了古代教育思想,也写了近现代的教育思想,是解放后第一本从古到今专论中国教育思想发展史的书……它既重视教育思想史料的挖掘和整理,也重视对这些教育思想史料的分析和驾驭。它既对每一个时期教育思想总的倾向和特点加以概括和说明,又抓住每一位教育思想家的个性有重点地论述,而不是千篇一律、千人一面、毫无特色。它既吸取了前辈人和当代教育史学界的研究成果,也有不少他自己独特的分析和创见。书中还采用了比较法,如对孔墨、对孟荀、对儒墨道法、对程朱与陆王的教育思想有比较的分析,还有中与外比,前与后比,这也是我多年提倡的。总之,本书对中国教育思想史进行了较深入的论述,取材较博,分析较密,提要钩玄,得其要旨,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对‘中国教育史’学科建设也具有一定的价值。”
《中国教育思想史》开启了对中国教育史研究从教育思想、教育制度以及各专题进行多角度、多侧面、多层次、多方法、多领域、多途径研究的先例,分别获1988年全国第一届优秀教育图书评选一等奖,1989年全国首届优秀教育理论著作评选优秀奖。2010年,外文出版社出版了《中国教育思想史》的英文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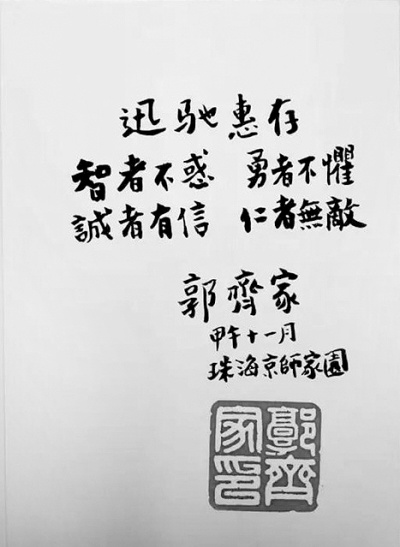
体悟
郭先生对中国教育史的研究,从儒家入门,对儒家学说相对偏重,将孔子研究作为中心和起点。《中国教育思想史》明确指出:“我国最早的教育思想,是载于《尚书·周书》中箕子、周公的教育思想……但是箕子和周公的教育思想,仍然夹杂在他们的政治思想之中,尚没有系统化。真正系统化、形成独立体系的教育思想,就还是从孔子开始的。”
尽管如此,郭先生还是一方面尽可能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视角,看待中国重视教育的优良传统和古代灿烂的文化,另一方面他也看到,“中国教育思想的发展总是具体的、历史的、丰富的、多元的、多民族的、多地域的、多层次的立体网络”,其中“儒家教育思想占有突出地位”。
郭先生理解的“儒家教育思想不是静态的、狭窄的、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动态的、历史的、涵盖面很广的范畴,具有包容性、延续性和浸透性的特点”,从孔子、孟子、荀子到《礼记》,它遇到过各种文化的撞击与融合;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被汉朝廷采纳后,又经过魏晋玄学的冲击,再经韩愈的复道,宋初三先生的疑传和疑经,形成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两股不同儒学传承的教育思想,是儒学与道家、玄学、佛教文化长期融合的产物。
对于儒家教育思想本身,郭先生认为“是以道德教育为轴心,不甚追求自然之所以的非宗教体系”。与欧洲教育思想和印度传统教育思想相比,儒家教育思想的显著特点是教人如何“做人”,如何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追求“同天人”“和内外”“天人合一”的最高的、理智的幸福。
儒家教育思想是一种群体本位的追求“乐感”的乐观教育,“极高明而道中庸”,追求自律而反对他律。因此,儒家教育思想“限制了实证科学的发展”,使教育与科学技术脱节,“它既给我们民族增添了光辉,也为我们民族的进一步发展设置了障碍;它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也是一个不小的负担和包袱”,应当扬长避短,以有易无,把历史的经验教训当作探索教育发展问题的“历史顾问”。
1978年后,不惑之年的郭先生自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开窍”了。“我觉得中国文化,不仅是一种知识,这知识背后还有一种精神,一种理念。”后来,他的变化是“逐渐从绝对的知识系统里超越出来,特别是对研究生的讲课,课堂讲授的知识要包含一种做人的东西,终极的目标是人文的关怀、终极的关怀。”
郭先生认为,中国古代教育是多元并进的。中国古代文化是靠教育传递下来的,中国古代各家文化都十分重视教育,文化的多样性决定着教育的多样性,其中最主要的是孔孟、老庄、墨翟,后来引进佛学,它们在各个历史时期交错发展;官学与私学的同时发展和竞争又使得具有层级特征的教育与文化竞相峥嵘,官学的相对保守、稳定、单一与私学的千姿百态、盛衰多变,使得中国古代文化有延续性而又不断走向新的灿烂。
郭先生讲解儒家经典及其注解时,会分门别类地阐释道家、佛家在同一问题上的看法,旁征博引,显现通达、圆融的思想境界。他常常介绍自己在忧患之中按照儒释道的智慧指引调节身心,修身养性,最终走出了人生阴霾的经历,引导学生能够真正将学问落实到生命里,夯实传统文化中最为根本的“性命之学”。立足于对中国传统教育“综合观”的体悟,郭先生认为,中国传统儒释道三家经典体现的是普遍的和谐,圆融无碍的生命智慧——
他看到了儒家德性、礼乐的智慧:“通过修身实践的工夫,尽心知性而知天。通过‘存心’,做一个好人,清理显意识”;
他看到了道家空灵、逍遥的智慧:“超越物欲,超越自我。强调得其自在,歌颂自然生命以及生命自我的超拔飞越,肯定物我之间的同体融合。通过‘修心’,做一个修炼人,净化潜意识”;
他看到了佛家解脱、无执的智慧:“启迪人们空掉外在的追逐,消解心灵上的偏执,破开自我的囚笼,直悟生命的本真。通过‘明心’,做一个明白人,趋向无意识”。
郭先生以儒家研究为主,却又不囿于此,以开放意识接纳各家学说,完整理解中华传统文化。他一方面加深拓宽对传统儒学的理解,另一方面积极回应当下社会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用生命教化的智慧,这份珍贵的“中国教育的思想遗产”,为中华传统文化引入现代生活创造条件。
弘扬
2000年后,郭先生以极大的热情、强烈的使命感投入到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事业之中。他曾经自述:“开始致力于在社会上普及传统文化,在图书馆讲课,也在社会上讲”,“对我个人来说,这个时候的文化其实已经进入到信仰层面了……学习中国文化,不光是要学习知识,重要的是要安定心灵,让我们的心灵沉静下来,不那么浮躁,我很看重这一点。”
其实早在1985年,郭先生就参加了一些孔子研究所的工作。1989年,中华孔子学会正式成立,他先后任副秘书长、副会长。在广泛交往中,郭先生从哲学、历史、思想、文化、中西对比、古今对比等视角拓宽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识,“优秀传统文化始终是中华民族的一种精神生命,是支持我们前进的力量”。
郭先生曾对新文化运动后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各种思潮和实践进行过深入研究,他认为,“必须重新认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传统与现代化既有一种对立、对抗的关系,也有一种包容、延续的关系……传统可以作为现代人的一种‘资料’‘资源’,如果运用得好,还可以变成现代发展的一个‘动力资源’。现代化不能经由全盘打倒传统而获得,只能经过对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而逐步得到。”
郭先生分析当下诸多社会问题,在于人们在追求现代化的途中误入功利、浮躁的歧途,因此需要用民族自身的传统文化来安定心灵,他一方面通过写文章,阐明传统文化的价值、意义,如何用它解决现实生活的问题;另一方面直接通过讲课、讲座、编写读本、支持青少年读经等社会活动,有意识地宣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郭先生不遗余力地宣讲,完全源于其内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片温情与敬意,更是他作为学人的时代使命与担当。行走在知识与信仰之间,他认为讲课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践行,与人交谈是养成“拈花微笑”的佛心,无处不体现着“兴慈运悲,不舍众生”的情怀。“我们学习《论语》《老子》等文化经典,不仅仅是为了增长见闻,或者附庸风雅,而是为了安顿自己的身心,涵养自己的性情,接上民族的传统,使自己在天地之间可以站得稳、行得正,在纷纭的世事中找到一处心灵的乐土,在‘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中追求真善美的互诠、圆融无碍的人生境界。”
2004年,郭先生在北师大正式退休,应邀南下北师大珠海分校教授《四书》等通识课程,这一讲就是12年,直到2016年夏天才回到北京。他讲《四书》的立足点是鼓励同学们回到“人”本身,回到“心性”的修养上,而不是仅仅关注知识层面,关心分数,关心考试,要关注技术背后的心性,不能一味用工具理性替代价值理性,片面用科学技术遮蔽人文精神。
郭先生指导学生成立国学社,学习和弘扬国学,每学期都会利用周末参加国学社举办的论坛,有时还会将自己收集到的一些国学书籍带过来送给大家。
珠海当地很多公益团体都邀请郭先生去参加公益活动义务讲学。只要条件允许,他都会不辞劳苦欣然应允,甚至有时不太方便,仍会尽量满足别人的需要,或带领国学社的同学走出校园,不顾一路颠簸近两小时参加社会公益实践,在知行合一中修习传统文化。
郭先生多次强调,中国传统教育其“内在观,即强调启发人的内在道德自觉性,心性的内在道德功能观。中国传统教育的显著特点是启发人的内心自觉,教育人如何‘做人’,如何在现实生活中实现其‘治国平天下’理想的入世精神,强调的是对自身的肯定……自我求取在人伦秩序与宇宙秩序中的和谐。”真正的教育是心灵与心灵的碰撞,是灵魂与灵魂的感召,是生命与生命的依托,要培养学生具有大爱的胸怀、高尚的德行,以及善念的种子。
于述胜教授评价郭先生,作为中国传统教育的研究者,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受益者,郭先生看到了中华民族文化经典背后不朽的价值,无论是对于个人心灵之安顿,还是对于民族生命之发展,抑或是中西文化之汇通,都有着深刻的价值与意义。
传承
郭先生十分重视学生教育,自1986年到2004年,共培养研究生30名。他要求自己对学生“以真诚对真诚,以生命对生命”,“五十岁之后,我还感受到另外一点,那就是我的学生,学生的集体、个人对我的影响,我在指导学生的同时,也从学生那里得到了很多帮助,这也是我需要感激的一个方面。”
除了学业指导外,郭先生还十分关怀学生的人生和生活,有针对性地介绍他们参加一些学术活动。进入先生门下,报到后不久都会被他叫到家里,在简短了解学业与家庭情况后,郭先生都会提出了一些要求,填写培养计划表,给每人开一份研读学习书目。
每次有学生来家里,郭先生和师母都会热情地准备茶水,逢年过节或周末,他会把学生们叫到家里来聊聊天,餐叙一番,感受一下家庭的气氛和温暖,更会对弟子们进行家庭关系、孝敬父母、遵守校规等方面的提醒和考核。
2004年,郭先生去北师大珠海分校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学,每周四门大课,每门课100多名学生,除此之外他还兼任其他学院的专业课。每次上课,他都会提前半个小时到教室,拿着放大镜照着自己的书稿笔记,在七八平方米大的黑板上写下满满的四面板书。
学生们心疼之余也有疑惑,为什么不把笔记打在课件上呢?郭先生说:“如果我不写黑板字,同学们就不会做笔记了,课件他们也不一定看的。如果板书的话,我辛苦,他们也辛苦,同学们会做笔记,会记住一些。还有,我也当练练字。我们不能总是靠打字啊,久了连字都不会写了,我们的文化载体不能丢失啊!中国汉字本身承载了巨大的文化基因与密码,一字一乾坤,一笔一画皆生命啊!”
上课前,郭先生都会庄严地立正鞠躬,然后高声说:“同学们好!”主动向学生行礼。后来,学生们也开始主动向先生行礼。一句“同学们好”,一句“先生好”,交织辉映成最亮丽的一道风景,成为活泼脉动的文化生命的课堂。
那情感、那力度能把大家都震撼住,偌大的教室出奇地安静,只留下讲者的声音久久回荡。郭先生对学生说:“同学们啊,我年纪大了,讲不了几次,将来靠同学们了。我们学传统文化,不只是在课堂上,更要走进基层中去。你们要真正地去践行国学,到社区给老百姓讲我们的传统经典文化。”
2011年,郭先生为国学社社庆题写贺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和经典为友,与圣贤同行’!为每一个生命的喜悦幸福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努力,愿与国学社同学共勉!”体现出了他对学生的殷切期待。
郭先生曾引用冯友兰先生“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的话寄语学生,勉励大家修学储能,传承好祖国的文化。“我现在讲的《孟子》,是五十多年前陆宗达先生讲给我们的,现在我传授给大家,这就叫作薪火相传。等你们将来成才了,继续传给你们的下一代。当我仰望星空时,我仿佛感受到我的老师在天上,像星星一样望着我。而将来有一天我与他们相会,我也会在天上看着同学们,给你们力量……”
这些话语情真意切,有心的学生就将郭先生讲的很多课程用摄像机拍摄下来,甚至同样的课程拍了几届不同的版本,作为此后温故知新的宝贵资料。
课堂上和论学时,郭先生非常严谨,往往会一脸严肃,不苟言笑。但在课下,他却能较为开放地与学生交流,用实际行动诠释一个儒者与师者为人处世的修养以及对家国天下的担当。
郭先生身体力行,在现实生活中为人师表,真正将学问落实到生活实际之中,他对人总是谦逊和客气,虽然很多人把他当名师敬仰,但他却丝毫没有高高在上的模样,总是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生怕给别人添麻烦。
有一次,一位同学向郭先生投诉助教改作业过于严苛,以至于影响了他的学业成绩和学习积极性。这件事让郭先生为了难,他比较同情和理解那位同学,于是就找到助教,想提醒他适当宽松些,但又碍于平时自己要求的严谨学风,怕打击助教的责任心,结果是欲言又止。
那时的郭先生,与平常讲学时酣畅淋漓形成了鲜明对比,脸上竟呈现出有点纠结为难的神态。后来,学生们都觉得这事跟“启功不打假”颇有异曲同工之妙,也更加体会到先生在宽严之间的仁爱之心,不禁肃然起敬。
郭老师谦虚地认为自己属于“困而学之者”与“学而知之者”之间的人,“我这一生其实也没做什么大事儿,我是靠我的学生成就的。”他对学生们寄予厚望,认为“中国教育事业与教育思想未来发展的方向是:立足本国,面向世界,超越传统,综合创新”,应该“以开放的胸襟,面对挑战,广采博收别人的长处,实现自身的变异和革新,以获得外来文化的营养丰富自己,发展自己”。
郭先生真正做北师大校训所要求的“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作为后学,我们应该学习他的风范与使命感,以及炽热的家国情怀,学习他的为人与为学,学习他的勇敢与坦诚,学习他崇高与平实融为一体。或许,有人做得有点像,但还差得太远。
学人小传
郭齐家,1938年生,湖北武汉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法政学院教授。曾任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会顾问。长期从事中国传统教育和传统文化的教学与研究,主讲“中国教育史”课程。1989年主持的“中国教育史课程教学质量建设”项目获北京师大优秀教学成果奖。1997年被评为北京师大“师德先进个人”,2017年当选“当代教育名家”。先后培养硕士生17名(其中英国留学生1名)、高访学者和进修生10名(其中韩国、日本高访学者各1名)、博士生13名(其中韩国留学生2名)。专著有《中国教育史》《中国教育思想史》《中国古代学校》《中国古代考试制度》《中国古代教育家》《中国古代学校和书院》《儒家文化与中国古代教育——文明薪火赖传承》等,合著有《简明中国教育史》《中国远古暨三代教育史》《陆九渊教育思想研究》等,参编有《中国教育思想通史》《中国教育魂——从毛泽东教育思想到邓小平教育理论》等,主编有《中外教育名著评介》《中国小学各科教学史丛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全书》《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实务全书》等,共同主编有《中国教育通史·宋辽金元卷》《中国教育史研究·宋元分卷》《中国教育传统与教育现代化基本问题研究》等,其中有多部著作获国家级奖项。
(作者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地方教育史志研究会学校史志分会理事长,中国地方教育史志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副秘书长,《教育史研究》编委会副主任,主编《20世纪中国教育家画传》。)
责任编辑:姚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