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丹】王阳明临终遗言:“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王阳明临终遗言:“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作者:胡丹
来源:《中国青年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正月十八日庚寅
耶稣2019年2月22日

王阳明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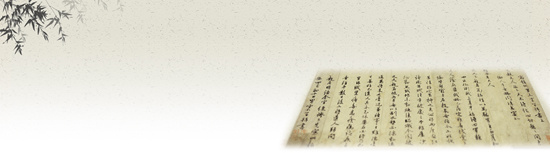
王阳明《寓赣州上海日翁》书
导读
“此心光明,亦复何言!”王阳明先生何以这样说?作者通过阳明先生一生的经历来为我们解说阳明先生的临终遗言。
这句话既是一种人生态度,也是一个人生故事。阳明先生是明代思想家、军事家、文学家,陆王心学的集大成者,中国少有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者,然而,在中国没有方向的舆论场中,他的身世和清誉却也是大尺度地沉浮,曾经高达浪尖潮头,也被人置于水底泥沙。
明史学者胡丹的这篇文章,或许能够帮助我们读懂阳明先生、读懂中国。
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57岁的王阳明在两广总督军务时,旧患咳痢之疾突然加剧。他有很不好的预感,于是在上疏“请告”(请求离职)后,不待“廷报”,就自作主张,坐船自梧州经广东韶、雄北行。打算一边等待朝廷批准,一边往家赶。当他离粤时,门人布政使王大用害怕路上有变,专门为老师备了副棺材,随在舟后。
十一月二十五日,舟逾梅岭至江西南安。府推官周积闻师至,前来拜见。阳明起坐,咳喘不已,自谓“病势危亟,所未死者,元气耳”。由于病势骤剧,阳明在南安一停五日,无法前行。至二十九日辰时,召周积入舟,已不能语。久之,开目视之说:“吾去矣。”
积泣下,问:“先生有何遗言?”
阳明微哂道:“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顷之,瞑目而逝。(《阳明先生年谱》)
上面这段记载十分感人。阳明自知不起,召门人来见,当是有所交待,不料话到嘴边,却不禁自笑(“微哂”),一个字都不想说了,唯带着一颗光明开悟的心离去。
讲学家似不当不言。然阳明临终,因何欲言又止?“微哂”之意何在?他生命最后时刻的这一幕,十分关键,但历来讲解者多不得要领。本文且就着“言”与“不言”的引子,从阳明后半生深溺“言不信之地”的境遇,对他的临终遗言作出分析。
一
临终前,阳明可能已预知到身后将发生什么。微微一哂,其实是无声的苦笑。
在去年(嘉靖六年)五月重获起用前,阳明在家赋闲已达七年之久。
自“今上”即位以来,不断有朝臣推荐他,有荐他入阁的,有荐他总督三边、出掌兵部的,可皇帝一概不准。这次命他往征粤西,也是事出无奈。盖因思恩、田州迭遭土官之乱,朝廷调集四省官军围剿,终是师老无功。这才从大学士张璁、桂萼之荐,准他出山,去西南几千里外料理这件棘手的烦难事。
阳明深知皇帝对他有成见,但可能不知道成见的症结何在。他与那位二十出头的年轻皇帝,一次都没见过,如何让紫禁城里的最高统治者心生厌憎的呢?
过去几年,时局纷扰,为了由外藩入继天位的嘉靖皇帝生父母的封号问题,吵得天翻地覆。在这场名为“大礼议”的政争浪潮中,原首辅大学士杨廷和下台,保守派阁部大员或贬或逐,而皇帝的支持者、被称为“议礼新贵”的张璁、桂萼辈强势入阁,“赞礼派”纷纷跃居高位。
参与大礼议的活跃人物,多有阳明的门人和好友,他们对大礼的态度,并不一致。如好友席书、霍韬与门人方献夫、黄绾、黄宗明等,“以议礼得幸”。为此翰林院编修王思公开宣称,“羞与同门方献夫为伍”;邹守益、王时柯等门人还参加了嘉靖三年著名的左顺门哭谏事件,为此遭受廷杖,王思受刑不过,被活活打死!
当朝臣因为议礼而分裂时,在越中大开讲席、声望日隆的“王夫子”,却采取了刻意回避的态度——大臣霍韬、席书、黄宗贤、宗明等“先后皆以大礼问,竟不答”。
当时赞礼派遭到激烈的反对,处境艰难,急需理论支持。阳明不言,他们从宋儒欧阳修那里找到了依据。当“大礼”尘埃落定后,欧阳氏乃被抬入孔庙陪祭,得到当世的巨大报偿。不妨设想,假若阳明趁时而鸣,公开发表赞礼意见,力挺急于当孝子的皇帝,他将得到什么?反过来再想,他讲学名气那么大,却在大家争得不亦乐乎时,一言不发,又会给皇帝留下怎样的印象?
阳明受命起复后,在给霍韬的信中,针对他“不言”的质疑回应说:“往岁承你以《大礼议》一文见示,那时我方在守丧,心中虽然赞同却不便奉复。既而席书也有信来,使者非要拿到回信才肯离去。我不得已,草草作答,大意认同其说,只是认为,其时典礼已成,当事者(即保守派)未必能改,言之徒益纷争,不如姑且相与讲明于下,等信从者多了,再缓图之。”
霍、席皆为赞礼健将,也是阳明好友。从阳明复书可见,他对前者是持同情态度的。他不发声的原因,除了典礼已成,再言徒益纷争,还因“议论既兴,我身居言不信之地,不敢公言于朝”。
阳明置身事外,比局中人看得更清楚:两派所争,明为伦理,实为权利。他的表态将无济于“明理”,只会帮助一派人击败另一派人,而无论如何,他的一部分弟子和好友都将受到伤害。他希望大礼之争,能“委曲调停,渐求挽复”,而不至决裂,朝政大坏。
在权势之争中,理常输于势,对此阳明有切身之痛,作为受害者,他形容自己“身居言不信之地”。
二
阳明不是生来就老成能忍之人,即便在壮年,经历了三年“龙场之谪”的磨难,依然不失豪爽之气,有话辄说,有屈即辩,这是他的本性。
在好友陆深为他父亲王华所写的《海日先生行状》里,记了这样一件事:阳明得罪大太监刘瑾遭杖谪后,王华也因不肯向刘瑾屈服谄媚,被勒令致仕。这时,有人拿王华同年好友之事做文章(古人称同科中举者为同年),对他加以诬毁。人们劝王华上疏自白,他却不然:“此事因我同年而起,我若辩白,是讦我友矣。谣言焉能污我哉?”竟不自辩。阳明复官回京后,听说了这件事,很替老父不平,便要具本奏辩。王华忙驰书制止他,说:“你以为那是我平生大耻吗?我本无可耻,你却无故攻发我好友的阴私,反为我求来一大耻。”他还批评儿子说:“别人都说你的智慧过于我,我还真不信呢!”
此事详情已不可知,但阳明既急于替父澄清,则定是关系到王华声誉的大事。可是因为牵涉到同年好友,王华不愿令旁人蒙羞,遂采取了清者自清的坦然态度。
那时阳明年近不惑,且在贵州讲学,已揭出“知行合一”之旨,开始获得较大的反响。可在这件事上,还是不如其父开霁大度。心知不平,便要鸣,道理不明,便要辩;鸣与辩,即是行。从其盛年激扬,到临终纵负万千枉屈,亦一言不辩,唯以光明开示后人,连接这两头的,正是他十几年的入世与修行。在这个过程中,阳明深感“居言不信之地”的痛苦。
三
正德十四年(公元1519年)夏,王阳明首树义帜,平定江西宁王之乱,一举成天下大名。
宁王朱宸濠早有不臣之心,两年前阳明奉敕督兵南赣,按照兵部尚书王琼的用意,就是布设在宁王背后的一柄利剑。果然,当宁王于南昌骤叛后,阳明从上游发兵,只用了四十多天,就生擒叛王,平定了明代中期的一场大乱。
可是平乱之后,功赏不行,“谗言朋兴”,立大功者反而“几陷不测”。朝廷派来的太监张忠、大将许泰,对阳明百计构陷,甚至诬陷他与宁王“交通”(勾结之意)在先,后乃趁一时之变,权衡两端,侥幸成事。
为了挖出阳明“通濠”的黑材料,他们把阳明门人冀元亨抓起来,严刑拷打。一时“谗邪构煽,祸变叵测”,成为阳明一生最为惊险的一段时期。
直到正德十六年四月嘉靖帝继位,权奸下狱论死,冀元亨才获释出狱,但他脱难仅仅五日,就因伤重去世。
一年多来,阳明承受着“通濠”的污名,这比他父亲所遭受的误解不啻百倍,他却连自辩的机会都没有。然而“委屈”适成他学问精进的最大动力,正是在这一年,阳明在南昌“始揭致良知之教”。对此他深有感触地说:“自经(朱)宸濠、(张)忠、(许)泰之变,益信良知真足以忘患难,出生死……往岁尚疑未尽,今自多事以来,只此良知无不具足。”
在正德晚年那个黑暗时代,奸佞当道,是非莫明,阳明陷溺于言而不信之地,只好痛自隐忍,不敢自明。如今新君继统,新政肇始,张、许等冒功滥赏之徒被处理,阳明“平宸濠之乱”的首功也得到追叙,京里还传来消息,说新君有意召他上京,将有重用。
阳明虽有良知可恃,此时益难以“忘患难”了,他还是忍不住要“言”,于是写揭帖遍递六部及都察院,为蒙难的门人“伸理”鸣冤,说到底也是为自己的泼天之冤辩白——他虽然得到“新建伯”的封爵,但对“通濠”之诬,朝廷还没有正式为他平反。
可是由于首辅杨廷和与尚书王琼关系恶劣,而阳明是王琼重用之人,为此遭到杨的嫌忌;“大臣亦多忌其功”。为阻止阳明来京,当道者借口“国哀未毕,不宜举宴行赏”,仅改授他为南京兵部尚书。而随阳明“起义”的同事诸臣,却在杨廷和主持的“考课大典”中,被以各种理由加以黜革,昔日大忠大节及其功次一概删削不问。
阳明“痛心刻骨,日夜冤愤不能自已”,他连上几疏,希望“辞封爵,普恩赏,以彰国典”;他甚至还非常“不明智”地替已经削职为民、发配甘肃的罪臣王琼争。这是阳明一生最后一次“大鸣大放”。
他这么做,深深得罪了以杨廷和为首的“当道”之人,使他在新朝依然不改“言不信”的困境。他的争辩,无人理睬。阳明大失所望,心灰意冷,遂借父丧(王华于嘉靖元年二月病故),挂冠归越。他走了,伯爵之封也成了一纸空文,应授的铁券和禄米都没给他。
四
三年后,阳明守制(守父母之丧)期满,例应起复为官;而杨廷和此前已因在大礼议中与皇帝意见相左而遭罢相去位。可是对廷臣的“交章论荐”,内廷仍然“不报”(指对奏疏不予理会)。已升任礼部尚书的席书气愤地说:“今诸大臣多中材,无足与计天下事者。定乱济时,非守仁不可”,他请皇帝召阳明入阁辅政,“无为忌者所抑”——席书所称“忌者”,直指首辅费宏,他对阳明的推荐,实际上暗含了伐异的私心。不久,老臣费宏在赞礼派的严攻下踉跄去位。
其后几年,阳明安坐清凉的阳明洞里讲学,不以不能复出为失意。他对形势看得太明白了,深悉赞礼派在大礼议中大获全胜,不是时局安定的开始,它将引发更大的权势之争,时势未有宁息。
“群僚百司各怀谗嫉党比之心,此则腹心之祸,大为可忧者。”阳明在嘉靖六年给门人黄绾的信里写道,“近见二三士夫之论,始知前此诸公之心尚未平贴,姑待衅耳。一二当事之老,亦未见有同寅协恭之诚,间闻有口从面谀者,退省其私,多若仇雠。”在信的末尾,他慨叹说:“病废之人,爱莫为助,窃为诸公危之。”
尽管此时他已奉敕出山,却依然一副置身事外的口吻,仿佛打定主意,待功成即身退;在信里,他还对江西功赏不明表达了耿耿于怀的态度,大约担心此次南征,恐不免重蹈覆辙——没想到竟被他不幸言中了!
阳明于当年年底到桂,指挥部署,迅速抚定思、田,并藉收服之众,乘势进兵,将多年的贼巢八寨、断藤峡一鼓荡平,功成只在数月间。
阳明的表现,怎么说也是有声有色,虽说因为病重,不待朝报就离职而去,可这点“任性”和他的勋劳比起来,似应谅解;何况他刚出粤境就去世了,已证明他在请告疏中对自己病情的描述非虚,朝廷怎么也该讲点人情不是?
可是,当阳明病故的消息传到北京,嘉靖帝非但没有惋惜,反而“令吏部会廷臣议故新建伯王守仁功罪”——说是功罪一起议,可从皇帝的态度来看,他要议的,主要是“罪”,不是功。
据《明史》说,当断藤峡捷书到京后,嘉靖帝就曾写手诏给首辅杨一清等,指责王阳明奏功夸大,并论及其人品和学术,对他作出了近于全面否定的评价。史云“一清等不知所对”。事实上,杨一清和他的前任费宏,都曾以阳明“好古冠服,喜谈新学”为由,反对召他入阁辅政。老派大臣在学术上对阳明的偏见,与皇帝并无二致;而赞礼新贵中,也有要员对他心怀嫉恨。
此事还有内幕,黄绾在《阳明先生行状》里有详细披露。他说,要“害”阳明的,主要是大学士桂萼。当阳明讣至北京时,桂萼故意将他亡故的消息按住,却拿他“擅离职役”做文章,指责其处置广西思、田、八寨恩威倒置,同时还“旧账”重提,诋斥阳明昔日擒宸濠军功冒滥,“乞命多官会议”。(“会议”又称廷议,是明代集体议政的一种形式,参与者包括勋戚、内阁、部院司寺大臣及科道官员。)
起初一力推荐阳明的,是大学士张璁,桂萼是被迫附议。两广捷音到京后,张璁“极口称叹”,说“我今日方知王公之不可及”,马上向皇帝推荐,要取阳明来“作辅”——也就是入阁之意。新贵桂萼和老臣杨一清都不高兴,于是嗾使锦衣卫指挥聂能迁诬奏阳明托黄绾送给张璁金银百万,才得以复出。
此事内情十分复杂,还牵扯到张璁与杨一清的首辅之争,故黄绾的回忆有其局限性。另一说称,聂能迁因在大礼之后不得升职,怨望不平,遂嘱人草疏,“论新建伯王守仁贿通礼部尚书席书,得见举用,词连詹事黄绾及大学士张璁”,张璁怀疑杨一清庇护聂能迁,遂彼此攻讦。
论阳明“功罪”的廷议,由桂萼主持,在吏部举行。所议之“罪”,包括“党逆”宁王(这个罪名比“交通”更甚),在江西放纵军士,屠戮无辜,私藏南昌府库财宝,以及新近在广西恩威倒置、举措失当等。最后只有讲学成为唯一被“坐实”的罪状。嘉靖帝随即下旨,停阳明之爵(新建伯由军功封授,例应世袭),同时颁布禁学之令,将王学斥为“伪学”,禁止学习和传授。
阳明纵是“不言”,纵然立功,都无法避免罹于党祸!他在身后遭到了比生前更大的冤屈。当他指心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时,难道不是已经预见及此了吗?
在一个争权夺利、是非混淆的时代,任何辩解,都是多余的。
五
当然,除了政治上的陷阱,人们对阳明的误解,也实在太多了。
好比他晚年提出“良知说”,成为其心学的根柢,而实现良知的前提在“存敬”,用阳明的话说,就是“心不动”。可这位崇尚不动心的夫子,偏偏被许多人视作权谋家。
阳明幼年,有一个著名的“枭鸟治继母”的故事。这个故事显然是他的“拥趸”想象出来的,阳明本人绝不会认同此事“可为训”。一次,好友储巏(号柴墟)派人送来一份《刘生墓志》,请他过目。阳明读后,认为此文“缜密”,但提出“独叙乃父侧室事颇伤忠厚,未刻石,删去之为佳”。理由是“子于父过,谏而过激,不可以为几;称子之美,而发其父之阴私,不可以为训”。编造“治继母”故事的多事者,肯定没读过这篇《答储柴墟》,遂造出一个权谋天成,却离阳明本心太远的“异闻”。
与多数理学家不同,阳明不仅有道德文章,他还有很大的事功。阳明是当世有名的兵家,人们常说“夫子应变之神真不可测”。长于用兵者,必知权变,这自然成为人们理解王学的一个角度。
古人说,“用兵之妙,存乎一心”,然行兵必以诈,这与纯儒的标准似乎严重对立,对阳明“伪学”的指责也多半由此发轫。可能是这个原因,阳明对自己的“兵事”极少提及。据门人钱德洪说,他“事先生八年,在侍同门每有问兵事者,皆默而不答,以故南、赣、宁藩始末俱不与闻”。
钱曾请教:“用兵有术否?”阳明否认有术,他说:“用兵何术?但学问纯笃,养得此心不动,乃术尔。”阳明之意,竟是不动心就能带兵?老师这样解释,学生自然信服,于是有人得意起来,以为“可与行师”了。阳明问他为什么,此生答:“我能不动心。”阳明道:“不动心可易言耶!”此生自信地说:“我有不让心动的法子。”阳明笑道:“此心当对敌时且要制动,又谁与发谋出虑呢?”
言至此而竟!阳明到底还是没讲出“用兵无术”的道理,也没有就用兵“发谋出虑”与“此心不动”的关系作出理论阐释。言之不尽义,是阳明“语录”中常见的现象。
阳明用兵的情形,多见于报捷等疏文,但遗漏甚多,如“一切反间之计俱不言及”。反间即用诈,是兵家常事。钱德洪的理解是,“以设谋用诡,非君子得已之事,不欲明言示人”。为此他亲赴江西,搜集《征宸濠反间遗事》,存录了许多阳明用间使诈的案例。为使人了解老师“武功”的详情,钱德洪搜集了大量奏疏文移,查对月日,编次整理,“而后五征始末具见”。
由于阳明治学,要在讲席发挥,或私信讨论,很少著书立说,加上他本人又有较多避讳,这都导致对其本人及学术理解的偏差。当时就有人指责阳明“学术不端,聚众祸乱”,后世更有人认为,阳明学是一种“谋叛哲学”,即根因于此。
阳明作为“宸濠之乱”的平定者,却始终难以摆脱“通濠党逆”的指责,这不是“忌妒”二字就足以解答的。
六
随着越中讲学的影响越来越大,王学声名鹊起,同时非议与批评也多起来。
嘉靖元年(1522)十月,礼科给事中章侨上疏说:“三代以下,论正学莫如朱熹,近有聪明才智足以号召天下者,倡异学之说,而士之好高骛名者,靡然宗之……乞行天下痛为禁革。”
“聪明才智足以号召天下者”,即指王阳明,这是第一次出现指王学为“异学”,要求予以禁革的声音。
“近年士习多诡异,文辞务艰险,所伤治化不浅。”嘉靖帝在批复中肯定了章侨的观点,并且要求,“自今教人取士,一依程朱之言,不许妄为叛道不经之书,私自传刻,以误正学”。这实是王学被定为“伪学”的先声。
次年春,北京会试,策题以心学为问,含有“阴以辟先生”之意。门人徐珊读题后叹道:“我怎能昧着良知以幸时好呢?”不答而出。但另几位同门欧阳德、王臣、魏良弼等,在作答时发挥老师所教意旨,毫无忌讳,居然被录取了。这在当时的舆论环境下,“识者”也只能理解为“进退有命”。其实,当圣旨作出王学“有误正学”的批评后,发挥心学意旨的考卷仍能“漏网”中举,说明朝廷禁令已无法阻止王学传播了。而阳明遭忌愈深,与王学的迅猛传播是密不可分的。
钱德洪参加了这次会试,下第而归,他向老师抱怨,“深恨时事之乖”。阳明却喜形于色地说:“圣学从兹大明矣!”德洪不解,问:“时事如此,何见大明?”阳明说:“吾学岂得遍语天下读书人?今《会试录》虽穷乡深谷无不到矣,吾学既非,天下必有起而求真是者。”
当朝廷指斥王学为“叛道不经”,一些在朝为官的门人欲上疏奏辩,阳明制止他们说:“无辩止谤,尝闻昔人之教矣。”这“昔人之教”,想必也有他先父的教导。从辩到无辩,阳明对谤议的态度,已发生了极大的转变。他“无辩止谤”的理由是:“四方英杰,以讲学异同,议论纷纷,吾侪可胜辩乎?”
与辩相比,他更看重“默而成之,不言而信”。所以他才不在乎“伪学”的指责,反而更看重部分门人破冰登第,因为他们中榜后,试卷将收入《会试录》,成为天下士人的必读书,凡读者皆受一番洗礼,这便是“默而成之”。他根据自身经验体会到,设若学者处“言不信之地”,纵然千言万语,于“今日之多口”,“可胜辩乎”?
晚年的阳明,对于“受谤”,愈趋于向内用功:与其与众人辩,辩不胜辩,不如“反求诸己”,“动心忍性,砥砺切磋”,使学术愈为醇厚,最终达致“不言而信”之境。
一日,门人邹守益、薛侃、黄宗明、马明衡、王艮等侍,谈到近日谤议日炽,阳明说:“请各位谈谈其缘故。”有说先生势位隆盛,是以忌嫉谤;有说先生学术日明,为宋儒争异同,则以学术谤;有说天下从游者众,良莠不齐,是以身谤。最后阳明道:“你们说的这三种情况都有,只是我心中所想,你们还未谈到。”众人忙请教,阳明说:“我在南京以前,尚有乡愿意思。在今只信良知真是真非处,更无掩藏回护,才做得狂者。使天下尽说我行不掩言,吾亦只依良知行。”
阳明说他在正德十六年改官南京前,还有点媚时从俗的心理(即“乡愿”),生怕别人不理解,不得世人之好,如今他却只信真良知,依从良知行事,对天下之谤,反不再介意了。这里,阳明竟是以“狂者”自喻的。
“良知”,就是一颗光明的心;“只依良知行”,就是守住内心之光明。阳明如此说,既有一种兼济天下的难为之意,同时态度里又有了一分从容和安宁,他相信他的良知与光明,终能使人理解信从,“亦复何言”呢?
然而,“狂者”堪足自守,不为天下沸议所动,但狂者为师,如何能成为天下榜样呢?阳明还是说之不透。
七
被后人誉为“真三不朽”的阳明,一生道路坎坷,他没有神奇的魔法,也没有登高一呼、万众云集的魔力。相反,在探索新学的道路上,遭遇了层层阻力,蒙受了太多的猜忌与冤屈,正像霍韬所说:“夫忠如守仁,有功如守仁,一屈于江西,再屈于两广!”这在明代士大夫中,真不多见。
逆水行舟,风波不定,但阳明找到了压舱之物,那就是王学最后的口号:“致良知。”
前引阳明在江西南安府所留遗言,见其门下弟子所编《年谱》。黄绾所写《阳明先生行状》,也记有他的临终之言,与前者不同。行状云:
(嘉靖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至南康县,将属纩(临终),家僮问何所嘱。公曰:“他无所念,平生学问方才见得数分,未能与吾党共成之,为可恨耳!”遂逝。
对门人,阳明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对家僮,他说“未能与吾党共成(学问)”为可恨。这两个遗言并不矛盾。
阳明心学的根基,是良知,然而如何达致良知,需要一套完整而明确的论述与规范。然而,读后人辑录的《王阳明全集》,内中关于如何进业的具体记载,却非常之少,许多时候,只是对理想状态的一种描述——比如前面提到的“心不动”。阳明是明代理学大师,更是心学发展的标志性人物,但平心而论,他主要是提出新问题,然后给出答案,但在问与答之间,尚缺乏缜密的论证过程(这也是中国古代思想家的通病)。
好比他晚年提出“真足以忘患难,出生死”的良知说,基于他对“世事之难为,人情之难测”的切身感受,是从他备尝艰辛痛苦的感悟中来,具有强烈的个性,但如何将“良知”变作一种普适的理论工具,却没有现成的办法。在大礼议之争中,门人的分裂,以及后世学者不得法,沦为所谓“王学末流”,都是证明。阳明自叹“平生学问方才见得数分”,应是肺腑之感,他遗憾没能把他的学术大厦建立起来。因此,“不言”与“可恨”是相互补充的,两者缺一不可,共同形成阳明最后的“学术影像”。
多年以前,阳明之父因为他急于辩驳,对他作出“不智”的评价;十余年来,阳明明知“身居言不信之地”,却不得不亟亟而辩;到了生命的最后几年,他的心突然静了,不动了,对一切讥毁,始取坦荡不辩的态度。这是他个人修为之得法。然而终其一生,阳明都没能稳立于“言而有信”之地,在身后竟还遭到伪学的玷污……
阳明的伟大理想,一定是用他的心烛,点燃世界的火炬,而不是在那小小的角落里,保留一星火种(也就是他说的“此心光明”)。可是,在他弥留之际,留以示人的,仍然只是他自守的一片“光明”——这,正是他的所念与所恨处!
责任编辑:近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