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家星】“介于朱、王二本之间”——魏庄渠《大学指归》对明代理学的批判、融通与重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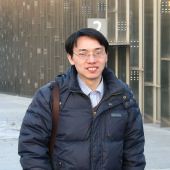 |
许家星作者简介:许家星,男,西元1978年生,江西奉新人,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博士。曾任南昌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
“介于朱、王二本之间”
——魏庄渠《大学指归》对明代理学的批判、融通与重构
作者:许家星
来源:《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二月廿七日己巳
耶稣2019年4月2日
作者简介:许家星(1978-),男,江西奉新人,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四书学与宋明理学。
内容提要:明代理学家魏庄渠《大学指归》对《大学》的阐发,突出了至善无对、知止见性、格物知本思想,彰显了复性定性、静养天根、先立乎大、自作主宰工夫。试图以此解决朱、王二家支离、空寂之弊,融通朱、王二家之说,开拓明代理学“第三条路线”,彰显了明代理学演变的复杂性,体现了《大学》诠释的多元性,启发今人不可拘泥于“非朱即王”的观点,以免对明代理学做出简单化理解。
关键词:魏庄渠/《大学指归》/明代理学/中间路线/Wei Zhuangqu/The Great Learning Tenet/Neo-Confucianism of the Ming Dynasty/the middle way
标题注释:国家社科重大项目:“中国‘四书’学史”(13&ZD060);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基地招标课题:“明代江右四书学研究”(JD1407)。
朱子学与阳明学构成明代理学的两条主线,然亦各有其弊。为此,有学者试图在批判性吸收二家思想的基础上融会贯通,形成了“介于朱、王之间”的明代理学第三条主线,可谓“中间路线”。已有学者指出,明末东林学派、蕺山学派对朱子学阳明学的调和渐为思想界主流,①这一融通朱、王的思潮实则早在王学流行之初即已出现。崇仁学派的魏校(1483年-1543年,字子材,号庄渠)是与阳明同时代的学者,亦是批判、融通朱、王,力图重建明代理学的“中间路线”代表。《明儒学案》置庄渠于“崇仁学案”,判其学是对“一秉宋人成说”的康斋学“稍微转手而终不敢离矩矱”②,又指出江右王门主将聂双江“归寂”说发端于庄渠,显出庄渠之学与朱、王二家皆有密切关系。四库馆臣亦言庄渠最重要著作《大学指归》“介于朱、王二本之间而更巧于附会”。③本文拟以《大学指归》为中心,结合《庄渠遗书》等著作,揭示庄渠《大学》的思想及其意义,以引起学界对明代理学发展脉络的进一步思考。
一“支离、空寂均之有偏”④
庄渠有鉴于“大道既隐,学术分裂”之局面,试图通过著《大学指归》纠正朱子学“支离”与阳明学“空谈”之弊,给“浸失其初”的学者指明圣学途径。他批评朱子学先天带有过于讲明而少于践履之偏,造成后学支离的学弊。“世之学者咸知诵法朱子,虽然,其讲明也过多,其践履也过少,后儒之所以支离也。”⑤又指出阳明学看似易简,无支离之病,实则言过其行,违背圣人讷言敏行之教,陷入晋人“清谈”大病。“承谕今之讲圣学者,其说似若易简,与世俗之支离者不同,夷考其行,顾反不逮。”⑥“迩来讲学者众,吾道其复兴乎!但往往好为空言,与晋清谈何异?”⑦
鉴于朱、王二家“支离、空寂均之有偏”,庄渠直趋儒典,试图通过创造性诠释《大学》来纠正二家之非,由“正《大学》”以重建道学正途。王廷《大学指归》序指出,《大学章句》与《大学指归》的差别在于前者不过是解释文义,后者则直指为学趋向。“《章句》析其义,《指归》一其趋”,此“一其趋”强调《大学》所代表的古人之学就是心学,“古人之学,心学也。外心而言学者,非也”。⑧庄渠认为此说言简意赅地突出了《大学指归》发明“心学”的主旨,乃有德之言。
庄渠高度称赞《大学》为圣学枢纽奥妙所在,“近体《大学》,颇窥圣学之枢机,至易至简。说者自生繁难,阳明盖有激者也”。⑨它以极其简易的方式阐明了古往今来圣人之“绝学”,故对该书之诠释、体认不可有丝毫谬误空疏。阳明《大学》乃激于朱子繁琐章句之学而发。他再三指出,《大学》强调从工夫源头入手,对圣学工夫之发端与收煞,皆有明确指示,首尾一贯。因此,庄渠写了三本《大学》论著:以古文撰写的古本《大学》;采用古本,全面阐明《大学》思想的《大学指归》;就《大学》14处文字异同作出考辨作为附录的《大学考异》。《指归》乃庄渠一生心血所在,反复数次修稿而成,去世前一年寄给王廷写序。“正大学”亦是庄渠“正六经”计划中唯一完成的著作。
二“其用功在复性,其收功在定性”
庄渠刻意突出了《大学》的“复性”意义,提出“《大学》功夫,复性而已”的说法。认为《大学》乃“言乎大人之学也”,所谓“大人”即成人,非孔子所言“可谓成人也已”之“成人”,包括士、贤、圣。庄渠喜用“始乎为士,中乎为贤,而终乎为圣人”这一表述,认为《大学》所示成就圣贤之道本来“坦如大路”,但受功令科举之学的误导,使得以践履修身为主的圣贤之学逐渐异化为钻研书本之学,导致“以读书为学”“道在纸上矣”。
庄渠对三纲的阐发突出了《大学》工夫在于复性的宗旨,指出“在明明德”四字已统括了儒学根本。明德不离肉身,就血肉之躯而显露发布,因此易于遮蔽。言“德既昏,何以能明也。曰:根心难灭,但随光随熄,非透彻不可以复明”。盖人之根心(本心)从不会被灭除,只是常呈若隐若现,飘忽不定的不明朗状态。只有获得完全究竟之透悟,方可使得心体复其本初,重新恢复光明。明德新民不过就是复性而已。他据阳明“吾性自足无假外求”说,提出明德新民“合一”论:“明德、新民一邪二邪?曰:合一。由己以及人,若分我人,则是吾性有外也。”⑩此“合一”论的实质是“性同论,性足论”,人性与己性一般,皆是自足、同质、相通的,故能做到人己相通而无隔无别,若有隔有别,则新民即不可能。故明德与新民不过是“变文同义”,“明明德者,明我明德也。新民者,明我明德于人也。而变文言新民者,吾性自足不待外求。人性亦自足,不待吾增益,但能变化之耳”。(11)盖人我之性皆内在自足,无须向外寻求探索,增益补充,故为学工夫就只能是复性。此强调人性具有内在完善的充足性与根源性,突出道德主体自我完善的必然性,强调人性正面性与积极性。
“至善者,明德本然之体也,不与恶对。”庄渠“至善”论突出了至善超越善恶的本体意义。他借用佛学“本来面目”说,糅合《中庸》未发已发论,阐发明德与至善的体用、已发未发关系,言:“明德者,至善所发,本来面目也,未发无面目可言。至善者,明德本然之体也,不与恶对。”(12)明德是至善之已发,是有,是至善呈现出来的本来形态,即人的善性;至善是明德之未发,是无,它根本就无面目可言,无形无影,是明德的本然之体。明德尚属于善恶视域下显发出的伦理范畴,至善则是超越善恶,不与恶对的本体性存在范畴,是无声无臭的形上存在,是明德之善的根源。南宋以胡宏为代表的湖湘学持“性善不与恶对”说,认为性作为本然之善,并非对待分别意义上的善,而是超越善恶等价值判断的本体存在意义上的善,是“无对”“至尊”之善。“季随主其家学,言性不可以善言,本然之善本自无对,才说善时便与那恶对矣……本然之性是上面一个,其尊无比。”(13)但庄渠至善“不与恶对”说更多源自《乐记》“人生而静,天之性”说及明道、阳明思想。《乐记》“静”说对庄渠影响甚大,在庄渠看来,此静是超越动静之静,并非表示现实状态之静,它与超越善恶之善相应。明道是庄渠最推崇的学者,其“无对”“定性”等思想对庄渠影响甚深。明道《识仁篇》提出“道”至尊无比,不与物对。“此道与物无对,大不足以名之”,“义”亦不与死相对,“义无对”。即此推而论之,作为世界价值本源的“善”,亦不与恶相对,恶是后天才起的,“人生气禀,理有善恶,然不是性中元有此两物相对而生也”。(14)阳明的“无善无恶心之体”说,亦“与伦理的善恶无关,根本上是强调心所本来具有的无滞性”。(15)显然,庄渠至善本然无对说与朱子相背,而近乎阳明。在朱子那里,至善基本上只有一层含义,即作为明德、新民之目标的“事理当然之极”。在“极”的意义上,庄渠同于朱子,亦把“至善”视为为学“总会”“究竟处”。
庄渠以性为枢纽,突出了至善的定性意义,提出“《大学》工夫,只是定性”(16)。又以复性和定性来表明三纲关系,“明新是复性,止至善是定性”。(17)复性、定性为工夫全体所在,分别指功夫之开端和成就,定性既是复性之功效,亦是其前提。“学问之道无他,其用功在复性,其收功在定性,然不知定性,则亦不能复性矣。”(18)此说充分体现了他以性论《大学》的观点。他又以奋发有为之人道和自然无为之天道来界定“明新”与“止至善”的工夫与境界关系,“明明德新民者,人道也……止于至善,复其天也,自然而无为矣”。(19)
庄渠又提出“止于至善者,定性也。知止,教人见性”。在《大学》诠释史上,“知止”受到宋“兼山学派”黎立武、王学及“止修”学派李材等学者重视,庄渠亦特别重视之。言:“《大学》指授知止,此是千圣渊源。……若于此悟入,则工夫有个起处,便有个究竟处,若由大路然。”(20)“知止”为一切圣人渊源所在,既是圣学入手起头处,又是究竟根源所在,由此入圣,最为平坦。庄渠还将知止“见性”与止至善“定性”关联论之。指出经文以“知止”衔接“止至善”,缘于二者一脉贯通,分别指向见性工夫之开端与定性境界之达成。止至善是最高层次之定性,知止则是见性悟道的第一步工夫。须对性先有所悟见方能定性。如无见性工夫,则无法实现定性。见是定的必要前提,见性不在言说而在自家体认有得。“夫学以定性为极,然不见性,亦无由定矣。且道如何见性?”(21)
庄渠认为很难从正面阐释“知止”境界,但可从反面论述“非止”心境。“吾心被物牵动,念念迁转无停,时戾吾性,不得自如,吾性寂然本体,奚若不知止,决无定时。”(22)“非止”表现为心无所定而被外物所牵引,内心意念如车轮流水般迁移流转不停,近乎佛家“流注想”,导致无法体验寂然不动的本体状态。若无知止之功,则吾性永无定性之时。根本原因在于心无法与性合一。心具有活动变化性,性则具有稳定不变性,此处蕴含的前提是心性有一从分开到合一的过程,或者说心性为一体的过程。使心与性为一离不开变化气质,庄渠特别强调了变化气质对于复性的重要,言“吾性元是圣人,只被气质自害”。气质造成善的本体不能发用自如,戕害本性。批评王学轻言良知本体,把本应作为工夫对治对象的气质变成工夫的主体,由变化气质转为随气质变化。“夫学所以变化气质,非随气质为学也。”(23)
三“主静天根之学”
“静”是庄渠的核心工夫,庄渠言“静者,圣学之极功”。庄渠于定、静的比较中凸显了“静”为圣学极致所在,“执持而后静日定,不执持而自定日静。静者,圣学之极功也。一念未起时,不待执持,自不茫昧”。(24)定是经知止见性透悟后,再经由执持工夫所达到的心静境地,而静则是不需要执持工夫,自然而然处于心定境地。静、定区别在于是否还需要执持工夫。定可谓静的前提,静则内在包含了定。尽管定处于很高的境地,但仍会受到外物影响,故难以保持静。静则达到了自然无为的境地,被视为圣学工夫顶点。庄渠强调“静”是念虑未发、无须把持而心体自然虚灵不昧。此与上文所说“学以定性为极”似相矛盾。他认为,作为天地万物根源本体的“静”同样是作为定性“止至善”的本原,故庄渠之“静”乃是指“先天本体之学”。他指出,“吾辈欲学圣人,不求诸人生而静,只就孩提有知识后说起”。(25)盖谈道者多、体道者少,欲学为圣人,当从“人生而静”先天之学本源处下手,不应只就人之孩提产生知识后入手。
庄渠秉“心常静”说,不满于阳明“心常动”说,主张“圣学全在主静,前念已往,后念未生,见念空寂,既不执持,亦不茫昧,静中光景也”。(26)倡导前念已往后念未生之时,当下念头空寂,不执着不茫昧的虚灵光明之景,所谓“静中光景”也。王龙溪指出庄渠之静,仍是从朱子“静存动察”中而出,是时间状态意义上的动静。而阳明之“动”非动静相对意义上的动,开悟后本无须分动分静。此论显然未合庄渠“静”论的先天意义。庄渠把主静与求仁的圣人之学相结合,提出圣人之学以求仁为本,求仁之功则莫先于主静、莫大于主静。“圣门之学唯在乎求仁,求仁之功莫大乎主静。”(27)“求仁之功必先于主静。”(28)庄渠从天道化生的宇宙论证明静为仁根。“维时春气微温,生意盎然萌动,充鬰且久,太和满盈于宇宙间,蔼然吾人之仁也。然其原,乃自冬气闭藏严密中来,夏首连山、商首归藏,此圣学第一义也。”(29)“春气氤氲,尤易体验盎然吾人之仁也,其根却欲静中来。”(30)作为生意萌发之春,表征的是生生不已之仁,此仁之生意流动,实来自严冬至静之紧闭深藏中。故《连山》以艮卦始、《归藏》以坤卦始,皆强调“静”作为生生之仁的根源意义,此乃圣学第一等要义。
庄渠的“主静”是心身修养的共同宗旨,他认为养德与养身具有一体性,“养德养身,元无二理”,其要皆在于“凝精完神,此乃养德养身第一义也”,(31)反复告诫凝精全神的主静收摄工夫是消除身体疾病的有效良方,自然宇宙、经典著作于此皆有昭示。“凝精完神,深造自得,其于却疾也何有?”(32)庄渠以友人夏悖夫曾犯心疾,通过主静虚心工夫而自我痊愈为例证明其效用。“昔敦夫尝得心疾,久而自悟用功,疾亦良已。”(33)在女婿郑若得了喉痹病后,庄渠告知不需药物、针灸,此病属于心火,主静、清心、无为、损欲是最好的药方。“然此本病是火。其发于咽喉,乃标病也……不必药饵不必针砭,只是清心无为,便是上妙方也。”(34)
庄渠“主静”学的另一表述是“天根之学”。庄渠之学传自胡敬斋,本为朱学一脉,门人括其主旨为“天根之学”。黄宗羲亦把庄渠之学归为“天根之学”,实质是“主静之学”。“其宗旨为天根之学,从人生而静,培养根基,若是孩提知识后起,则未免夹杂矣。所谓天根,即是主宰,贯动静而一之也。”(35)庄渠天根之学强调天根的本原性,本乎易之艮卦。“天根之学本《易》艮背之旨。”(36)天根之学针对现实中害道之甚的“虚志骄气”,其学“妙在涵蓄,切忌泄漏”。其要领是收敛聚蓄,关键在心之收放。“收敛停蓄,深造默成,方是天根之学,其机只在此心收放聚散之间耳。”天根之学要求退藏于密,反对言语之说,以实现返朴归真。“何由返朴还淳,校是以着意天根之学。”(37)庄渠称赞《归藏》之说实为圣学第一义。归藏即是天根所在,孔孟之学亦只是顺其天机。盖造化总是由混沌到开辟,由收敛到发生,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过程。“是故归藏于坤,乃圣学第一义。噫,斯其为天根乎!”(38)由此不难理解庄渠赞赏老子的归根复命说了。
与“天根”相应的是由此而发的“天机”。庄渠反复言及为学为教关键在于是否能触发天机,由此奋发警觉,精进不已。“故夫子教人,妙在感触其天机,使不容已,提撕警觉。”(39)善学者可因鸟之知止而触发为学之天机奥妙,“缗矣诗是欲人触发天机,因鸟之知止而悟为学之当务。此触发天机处也”。(40)庄渠以“立本”与“研几”来区别天根、天机。言“吾所谓立本,是贯串动静工夫。研几云者,只就应事起念时,更着精彩也”。(41)立本与研几是不同的为学层次,分指静中工夫与动中发用,二者既不可混杂,亦不能割裂,构成工夫之全体。然立本实则贯穿动静,研几则是在意念发动时格外用心处。此近乎朱子戒惧与慎独工夫的区分。
庄渠对安、静的辨析亦类此:“处静境而能静者谓之静,兼闹境而无不静者则谓之安。此静、安之别也。”“静”指处乎安静之境而心静不动,“安”则兼及动静,即便闹市之中,亦无处不静。至于“虑”,则兼及事情作为。“此又兼有事言”,表现在有事状态下心体澄净朗照,从容周遍,无所不明,“遇事从容悉照则谓之虑”。(42)庄渠认为思虑对心之静否影响极大,然主静亦非要断绝思虑,而是要求思虑无邪,思所当思。故知止、定、静、安工夫皆落实收功于“虑”。“心之未静,以思虑多也。何故收功在虑?曰:思毋邪,则思虑。”他还提出“真止”来区别“知止”与“定静安虑”,知止是教人初步见性,经过定、静、安,虑方才真正能止。“至则是静亦定、动亦定,是之谓真止。”此真止亦即明道《定性书》“动亦定,静亦定”之“定”。
庄渠注重为学层次的区分,认为《大学》开篇言“知止”乃“学者之事”,非初学所能遽知。初学当从知本入手,为学当先知本末,故“物有本末”乃特就初学者而言,是退一步收缩说。庄渠将知止、定、静安虑得与为学之始、中、成三层相应。“知本,知止,学归其根,此之谓始乎为士。至于定,必曾勇猛用功一番,大段已了,此之谓中乎为贤,过此省力矣。毫发差池,不能作圣。静安虑而后能终乎为圣人。”(43)为学知其本,知其止,是归根复本之学,始乎为士之学,确定了为学的正确方向。至于定,则是已勇猛用功,道德成就颇有成效,进入中乎为贤的境界。由此之后,则进入静安虑得境界,用功极其省力,亦极为微妙,终乎圣人之境。庄渠明确将止、定、静与士、贤、圣相应,表明《大学》一书充分涵盖了人生道德成就的各个阶段,是循序渐进的阶段性与上达圣人终极完善的统一,为进德修业最佳指导。可见,庄渠具有整体把握《大学》工夫层次的思路,尤为看重不受朱、王重视的止、定、静,突出了“静”作为圣学之极的意义。
四“格,揆物定理也”(44)
庄渠就《大学》八目关系提出“起头”与“尽头”,“三转语”说。八目以身为中心,天下、国、家皆始于身,身又本于心,故一切皆由心而发,心“乃学之统宗会元也”,“已说到学之尽头处”。但《大学》尚进一步言及诚意、致知、格物,意在“就尽头处提掇起头处”。意、知、物三者是作为“尽头”的心之“起头”。可见,《大学》八目当以正心为中心分为两层,此与传统主流的修身为中心有所不同。他进而提出,作为“起头”的意、知、物之间具有层层紧密的转进关系,构成“三转语”,对学者用功极好。批评先儒对此有所忽视。“下面三转甚紧,正是提掇个起头处教人。先儒不免说得散了。”(45)一转是为何先诚意后正心。尽管万事归心,散心有善恶两种指向,若发心有假,则不当在正心上用功,而当反求诸意,透过诚意工夫来去伪存真,使心归一路,意之所发真实无妄。二转是为何先致知后诚意。人所发意念善恶掺杂的原因在于未能从知上真知善恶。正因未能真知,故所发意念亦未能真切,需要作推扩光大本心之明,破除蔽暗的致知工夫,此“知”非知识性之知,乃是人人皆具上天所赋之良知,良知由自身而遮蔽,亦当由自身而得到开显,此即致良知也。“匪天不降吾良知,人自不能致也。吾自蔽之,吾自开之。”(46)可见阳明“良知”学对庄渠亦有影响。三转是为何致知在格物。庄渠认为致知格物本只是一事。致知只有就着格物说,用功方才着实而不悬空。“如何又说致知在格物?盖心体本明,暗处是有物蔽我良知也,故心与物交。若心做得主,以我度物,则暗者可通。若舍已逐物,物反做主,明者可塞。故功夫起头,只在先立乎其大者。”(47)盖心体本来光明,其暗处乃是后天事物遮蔽良知所造成的后果。当心物相交时,心为物主,以我为主来度量事物,则心体光明,其暗处亦可透亮。若心为物役,以物为主宰,则明处亦变暗塞不通。故格物关键是以心还是以物为主。格物工夫源头在于“先立乎其大者”,格物其实就是树立心作为衡量、把握世界的尺度。“立乎其大则小者不能夺”乃象山名言,而为庄渠最喜采用,庄渠对象山颇有好评,此亦见出其学术兼综融合的特色。
“格,揆物定理也。”庄渠对格物的理解与前人存在重大差异。他批评程朱以穷理解格物乃自古未有生造之说。“格物也谓之穷理,古未之闻也。”(48)“穷理”一词源于《周易》“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所指乃圣人事,非初学所宜。格物属“精义入神”的始学之事,“穷神知化”乃圣人之事。委婉批评程朱格物穷理犯了颠倒为道次序的错误。“吾不知格物也者,属之精义入神乎?属之穷神知化乎?语道而非其序也,安取道!”(49)他把“格”解为“揆物定理也”。“所谓格,揆物定理也。……物在外,物理固在心也。理非一定,其见于物者,各有定也。且道揆者是谁,此须自寻把秉。所揆是物,能揆是心。心与物交,逐物则知诱于外,绝物则昧昧不能知。摄提此心,以我揆物而不以物役我,物理各正,心体渐莹,知之也真。”(50)揆是测度义,格为用心、立心测度事物确定事理。事物在人心之外,其理则不在事物而存乎人心。此似把事物与事物之理割裂开来。且心之物理亦无确定显现,当其显诸日用事物之中时,事物方才有定。此有定、无定意在强调心具理、心赋理的双重性。揆物之主体是揆物之心,对象是所揆之物。当心与物,能与所相交时,存在三种关系:一是心为物转,追寻外物而不知返;二是心断绝外物,排斥外物而不与外物相交。此二者后果是此心昏昧不明,无由彰显固有之良知。三是摄持此心,以我应物度物而不为物役,如此则物理得其正而心体渐莹彻光明,内心之知亦真实无妄,其知之也真,其行之也力。庄渠格物说“物理各正”的前提是“摄提此心”,目的是挺立本心,把握本心,工夫在内心而非外物。如无法挺立作为标准的本心,则“揆物定理”不可能。
他把“格”解为“揆正”,突出“正”的意味,近乎阳明“正其不正以归于正”说。此“揆”的标准是作为“矩”的心,人心自有作为主宰、准则的天,心中一点灵明透亮处即是权度絜矩所在。打开这点灵明之光,则内心光明畅达,关上这点灵光,则内心黑暗闭塞。心之光明之开合皆由乎各行动主体而不依赖于任何外在事物。“人心有天,只一点灵明处是已。开之生白,闭之暗塞,不由乎我,更由谁则。”(51)此“人心一点灵明”之说,显然受阳明影响,阳明说:“人又甚么教作心?对曰:只是一个灵明。”(52)庄渠进一步指出,灵明就是“把秉”,庄渠此词似据“民之秉彝”改来,突出作为人心灵明的法则性,言“一物一天则,总由吾心出,故曰秉彝”。秉彝是作为万事万物存在意义上之“根源”的本心。当内心无所把持,未能遵循一定法则时,作为揆正物理之心则会追逐物欲而四处奔驰。“心无所持,逐物欲而四驰,伊谁揆正物理?”故若要做到揆正物理,则需做到“把秉在我”,有两种途径实现之:一是决断心思,使其不与物接,但只要肉身存在,心作为活物,必然要流动。故要警惕“坐驰”之想;二是在与物相接时,做到主一无适,用志不分,避免“出位之思”。庄渠又将“格”理解为“揆正之也”,此“之”当指“物理”,测度并端正事物之理,其前提仍是“正心”。他对格物的要求是“博而专”。一方面“物物而格之”,对象极为广博。同时要求专一,“吾心格一物时,若不知有他物”。此外,庄渠并不主张先知后行说,而是认可知行合一、知行并进说。言“此知行并进之古。若曰先知而后行,等到几时行得?却是后世以博洽为知矣”。(53)“(无)所不用其极也而知行自合一矣。”(54)
格物之传“虽亡而实未亡”。庄渠力主《大学》古本说,反对朱子补传说,批评补传反使学者产生望洋兴叹,迷茫之感,认为从表面言之,格物之传可谓已亡,但实则“虽亡而实未亡”。首先就“此谓知本”来看,乃是教导学者为学当“知本”,此是成圣之学的第一步功夫,“优入圣域,发足在兹”。其次,格物之传义存《乐记》一章,此乃天意留此以补格致传。《乐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乃《大学》“至善”义,“人生而静,止于至善之原也”。(55)又说“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他特就“性之欲”与“物欲”作出区别,认为“性之欲非他,动以天也,人欲不可谓性之欲”。“性之欲”是来自人的自然天性,具有普遍性、合理性,“人欲”乃是掺杂了个人私利之欲望,应当消除,二者不可混淆并立。庄渠区别“性之欲与物欲”是针对阳明学“不察性之欲与物欲,则是以念念流转者为主,无端生出许多议论来。听其言,不曰且圣矣;夷考其行,犹是凡夫。且虚抬此心,不在本位,日用间真病痛却都放宽”。(56)阳明学者将性之欲与物欲混同,工夫被误导向以流转不停之念头为主,无法把握寂然不动之心体,最终导致言论高超,修行平庸的浮夸不实之弊病。此已点出后来黄宗羲批评阳明后学的“以情识为良知”之病。他批评阳明后学过分自负,犯有“良知傲慢”的弊病,又兼具党同伐异之心,不能虚心接受批评。庄渠认为《乐记》下言“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中的“好恶”是“意”的表现,与《大学》“如好好色如恶恶臭”之好恶一致。“物至知知”为凡圣皆有之反映,不过圣人内有节制而常人则无,故造成流而不知返的后果。所谓“节”,乃是“本然之权度”。庄渠将“格”解为“揆度”,无节可谓无格物之功也。故“无节于内”是格物反省之功有所欠缺的表现,“古语无节于内者,其察物弗之省矣”。(57)“知诱于外不能反躬”的原因在于不“知本”。为学大病莫重于为外物所诱,对治此病之良方莫善于格物致知。“故病莫重于知诱物化,药莫要于格物致知。”据《乐记》与《大学》格物的关联,他论定格物之义并未消亡。且格物之功当从反躬、节制之动上入手,盖人多从动处产生过失,物欲是引动人心、诱惑人心的罪魁祸首,若无欲则心自止而静。“格物何以先求诸动?曰:正为人多失之于动也。……多欲则多动,无欲止止,弗动矣。”(58)此通于濂溪“无欲故静”说。
“格物知本也。”庄渠认为老天并未丧此斯文,故有意保存“此谓知本”作为结语,“故特达存结语”。庄渠把格物解为为学之本,“格物,知本也”。认为如不能做到格物,即“不能反本还元,不可言至”。格物是知本、还本之学,是知止之学,是为学之始。庄渠始终注意把“此谓知本”与格物结合论述,指出传文两次提及“知本”,与经文“知止”相应,“传两提知本,与圣经知止相因”。作为知本的格物与知止存在初学与贤人之学的层次关系。“知止节是悟入工夫,乃贤者事,初学未亦及也。故又言此知本,是格物工夫,是学者工夫。”(59)庄渠以孟学解释《大学》知本说,指出此格物知本即孟子“先立乎其大”说,“不思而蔽于物”是因为心被耳目之见所支离蒙蔽,应开发光明此心之知,使心发挥思考功能。若不先立其心,则思索主体无由挺立。“心不先立,思者其谁?”知本即是先立乎其大者,此似陆氏口吻,但问题是,此先立乎其大者的内涵既不是发明本心,亦不是格物穷理,而是明心、求放心。“格物谓之知本者,即此是求放心。学患不归根,学归其根,物物各有着落。”(60)故格物知本就是求放心的归根复本之学,由此而事事物物皆有其着落。归根来自《老子》“复归其根”“归根复命”说,故他对老子颇有正面评价,有取于其返璞归真的归根之学,反对判定其为异端。“《老子解》渴欲一见之,千圣相传,俱是教人反朴还淳。……后世目为异端,非唯不知老子,恐于圣门宗旨,亦未必知矣。”(61)他曾据老子归根思想体验而有得,言“‘重为轻根,静为躁君;轻则失根,躁则失君’。溽暑中验之,尤得力也。”(62)但庄渠归根复本的内涵则是朱子的“存理灭欲”。在实现归根的路径上,庄渠采用明道“体贴天理”说,言“随事体帖天理出来,随事刮磨人欲使勿障”。强调应随时在事上体贴天理,消除人欲,作存天理、去人欲工夫,以达到心之通达无碍。其“随事体贴天理”在表述上亦近乎甘泉“随处体认天理”说。他批评司马光提倡的“绝物求心”说有见于末学弊端而陷入“枯守其根”之病。“此恶夫末学之蔽而未免于枯守其根也”,特别指出谨慎言语对于归根、求放心具有根本意义,“吾儒欲存此心,亦须扪口勿言,不轻漏泄。意自归根,则养得心完密,无罅隙可走”。(63)言为心之发,如多言妄语,则为心思泄露的表现。如沉默寡言,则意念自然复归根本,心意绵密而无缝隙。他在格物方法上突出了自我主宰、提起本心的决定意义,批评泛观物理论。言“天生吾人合下付这道理,散见于日用事物而总具于吾心,必先常常提省此心,就逐事上一一穷究其理而力行之。根本既立,则中间节目虽多,皆可次第而举。若不于心地上用功,而徒欲泛然以观万物之理,正恐茫无下手处。此心不存,一身已无个主宰,更探讨得甚道理”?(64)天下万理虽散见于日用事物而皆全体具于一心,故此为学之要不是到事物上逐一穷理,而是先把握总具万物之理的心。此是格物之根本。只有在时常警醒此心,保持心能自作主宰的前提下,方可以去事物上逐一穷理。只要作为根本的心体能够自作主宰,则具体节目自然一一应对。反之,如不在心地用功,而欲泛观物理,只会茫然无下手处。若心不存,身无主,任何道理都不可能探究,即便讨来亦无处安顿。他反复论及“心立主宰”的重要,无论有无动静之间,皆需要有本为之主宰,有主宰才能统摄诸事,以一应万,同时批评一味静坐收心,隔绝外物的佛学自闭式修养法。“人之一心,贯串千事百事,若不立个主宰,则终日营营。凡事都无统摄,不知从何处用功。又有兀坐以收放心,事至不管,是自隔绝。”(65)是否能“立主宰”、收本心,直接决定求道的成败。“深觉把摄只在方寸,但愧不能自作主宰,未免衮衮随逐大化。”(66)
如何来实现自我主宰呢?庄渠坚持朱子学的敬畏工夫,言“敬只是吾心自做主宰处”。为学必须常存敬畏之心,保持心之警醒,心体之浑全,此方合乎圣人心学所传宗旨,“须常存敬畏,此心醒然,事来方能照察得到,心体浑全。……此乃千圣心学相传,若合符契”。(67)庄渠的“敬自做主宰”与象山“收拾精神自作主宰”不同,其义是让敬成为自身主宰,以敬来收心,不让心走失散乱,突出的是自我克治。敬的要领是主一,使精神意念归于纯一,不产生杂乱思虑,特别批评持敬而添一外在之心以治心的毛病。主敬还要求工夫既不可过于散漫,同时亦不可过于把捉,不得舒畅,会产生滞留之病。“敬只是吾心自做主宰处。今之持敬者,不免添一个心来治此心,却是别寻主宰。”(68)“功夫只在主一,但觉思虑不齐,便截之使齐,立得个主宰。”(69)通过破除邪、闲之思,使本体豁然,达到或无念、或皆善念地步。庄渠把《大学》止于至善章的“敬”概括为严密、刚健、谦卑,唯“谦卑”不同于朱子,盖他把“恂栗”解为谦卑谨慎,言“恂读作峻,当如字,敬非卑实不能”。(70)朱子则循郑玄“战惧”说,突出敬畏义。庄渠还讨论了“敬止”说,认为由敬于止才能安于止,进而实现心性合一。“敬止者……心性所以妙合也。”(71)
格物与闻见:“圣学俗学之辨也。”庄渠深入辨析了格物与闻见存在圣、俗性质之别。言“然亦未知若何读之,博吾见闻邪?反求诸心邪?此通塞之机,圣学俗学之辨也”。(72)读书的目的如是求放心,是格物致知,则是圣学,若是广个人见闻知识,装模作样遮人眼目,则为玩物丧志之俗学。由此他甚至常有反对读书作文之说。读圣贤书本求体贴受用,反求诸己,收摄放心。世人却因读书而放其心,一心扑在书册上,这是极为令人叹息的俗学之蔽。他在讲义中反复告诫不可多读书,尤其要戒除诗文之好,求放心才是为学根本。他对读书抱有某种警惕感,听说皇帝爱读书,即表担心。这一强调读书弊病的“反读书”立场,更近于陆王之学。当然,他并非真的“反读书”,而是反对口耳之学的读书,推崇古人真知实行的读书。“谓古人读书主于体而行之,与后世唯事讲明者异。”(73)他从“弘天之学”与“闻见之学”的角度辨析二者的差别。批评“俗学以多闻多见为知,窒天聪明也,非开天聪明也”,不仅无助于开发人的天赋聪明,反而桎梏之。博学于文与闻见之知的不同在于:“多闻见者,杂采之学也,支离于耳目。博学于文者,当其博时,就约以礼而实体诸身。学欲博者,天纵吾,不知天限量。自知开扩万古胸襟,悉取众善,协之归一。此弘天之学也。”(74)闻见之知是毫无选择的“杂采之学”,无益身心,造成精力支离分散,导致人心散失。博学于文则是博中有约,强调“实体诸身”,其学为天之所纵而无限量,然根本却在向内开拓恢弘自家心境,取诸家之善而协调熔铸为一,极大弘扬天赋聪明而无有极限,实为“弘天之学”。
“《大学》关纽于诚意”(75)。庄渠喜用“关纽”说来突出诚意的工夫枢纽地位。他将诚意与格致并提,作为成圣两关之一,修身以下节目皆归为诚意而非修身。“《大学》以格物致知为入门,以诚意为一大关纽,透得此关,则更无关。”(76)诚意直接关系到圣贤人格的成就,成圣成贤的目标难以实现,皆因诚意关难以透过。“中乎为贤,终乎为圣人,俱在兹。……只因诚意一关难透。”他提出“意,心所愿为也”。心主乎意,意是心之主,心随意愿走,即心愿。“心愿”较之朱、王“意为心之所发”的“心发”带有更强的指向意味,强调了意对心的主导性。庄渠重视自欺说。指出自欺病症状非常严重,人陷入鬼蜮禽兽之中皆因有此。他据“诚意”章“曾子曰”推出《大学》曾子口传,弟子笔述说。“曾子只是口传弟子,未尝著为书说,至于此,又尝叮咛弟子,因附记师旨。”与朱子“夫子之意而曾子述之”说不同。
总体来看,庄渠对诚意论述不多,基本认同朱子说。“诚意一章乃圣贤吃紧为人处,文公《章句》《或问》,说得十分痛切。”(77)关于“正心”,他有不同于朱子的说法,指出“所谓修身在正心”的“在”不对,是弟子记录之误。经文只有格物致知言“在”,盖二者关系密切,本为一事。“今省文言在,乃弟子记师意而有少误也。”(78)他认可朱子所反对的谢氏“求是处”和“以恕为本”说,朱子则认为此说过于空洞,且不合格物本义。庄渠认为“心有所忿健、恐惧、好乐、忧患”四者有病,朱子则认为此四者作为人心之发用,乃人所不能无者。庄渠认为亲爱、贱恶、敬畏、哀矜、傲惰五者是恶德,朱子则认为并非“凶德”,乃是人本有之则。
五“心学”与“天心”
庄渠既突出了《大学》的性论,又认为心学是《大学》主旨,《大学》是发明古人心学之书。如认为“于缉熙敬止”之“于”作为叹词,意味着下文将阐发圣人心学之玄妙。“于,叹词。将言圣人心学,其妙有不容言者。”庄渠所言“心学”实指关于“心”的修养工夫,他最喜以“渊”字形容“心学”即见出此。如言“王纯甫心学渊深”“元诚心学光洁”“元诚心学渊微”“斯人心学渊悫”等。全面的心学工夫要求既内心有主以求入手,又要破除仅是把持内心而陷入道有中边的观念,以免狭隘,当兼顾内外心物两面。“知道无中边而不知内为主,则茫无下手处;知内为主而不知道无中边则隘。故曰‘此心学之全功也’。”(79)
在庄渠看来,心具有充塞宇宙的超越性、普遍性、至高无上的尊严性。作为至尊的心是独一无二的,“惟心无对,上帝至尊,岂有对邪”?又言“心,本体也”。心是天地万物宇宙之本体,是自足自立,不依赖于外在事物的本然之体。心亦具有虚灵、神明、莹彻、昭融的特点,妙贯、主宰、根底的功用。他采康斋说云:“夫心,虚灵之府,神明之舍,妙古今而贯穹庐,主宰一身而根底万事。本自莹彻昭融,何垢之有?”庄渠修改王廷序点明心除虚灵而无形外,又引《易》说突出寂照、感通、不变的特点,既内含于方寸而至小,又与太虚同体而至大。“愚意更欲赘云‘寂而能照而不为物先也,感而遂通而不与俱往也’。”(80)庄渠之改补充“不为物先”“不与俱往”,更具体形象点明心体与事物同在的当下性。庄渠论心喜引象山“宇宙内事即己分内事”说,此与“太虚同体”说皆表明心体广大无垠,无所不包。他喜用鉴之空照来阐明圣心之寂感,“圣人之心,寂如鉴空,有感如鉴照,物各还定形。应迹而无迹,空恒自若也”。圣人之心体本寂如镜,照物而不留物,应事而不留迹,其本体之空始终如一,不受事物沾染。他用佛语“求大解脱”来指向求心功夫,“今欲求大解脱,则何如?曰:只要心在。物本不能累心,心自累物,当下绝断”。(81)关键在于当下断绝,过去不追忆留恋,未来不妄想臆测,做到“勿意、必、固、我”,方能把握当下,行所无事,保持内心的通透虚明状态。庄渠既大量采用佛学、道家之语,如“大解脱”“微尘”“灵台”,又极力反对佛家,曾经焚烧佛衣,激烈排佛。与此同时,他对道家颇有好感,思想具有明显的道家痕迹。
庄渠喜用“天心”一词,似为天地之心的简称,“天心”仅有天而无地,表明全宇宙只有一个心,可以讲“天心无对”。庄渠认为扶持阳抑制阴是天地运行之普遍规律,故地不与天对,夏至不与冬至对,圣人特别重视此点,言复见天地之心。如有对应,则当为“复见天心,娠见地心也”。“天心无我”,天心另一特点是空空无我,大公无私,内外谐和。“心,天心也,空空无我”,“天心仁爱”,天心的根本特点是生生,是仁爱。“天心仁爱,大儆动于我心。”他特别以掌管刑杀的刑官咎繇“好生”说为例,证明“仁爱”实乃天心本质所在。“咎繇为古今刑官第一……大抵其学以天为主而好生一言者,真天心也。”他又认为只有圣人之心全然是天心,“圣心醇乎天心”。“圣人之心,何心也?醇乎天心也。浑乎天地万物一体,罔有不仁也。”(82)圣心与天地万物浑然一体,全体皆仁。
庄渠特别突出了“天心”的政治性,使之成为一个具有道德与政治双重意味的概念。如作为典范的君王能够分享天心,“皇极之君克享天心”。庄渠提出“凡心”与“天心”相对,以阐释心之概念的差异性。“天心”与“凡心”在道德上相对应,前者表示修养最高层次,后者则是修养不完善状态。“吾心犹有夫人者在,则未能合天心也。”由凡心进入天心的途径是,经诚意工夫达到无意、纯粹、至善地步。“自诚意而进于无意,纯粹至善,乃为天心。”天心与凡心也在政治上相对应,表现在处理人民利益上,能与民共利,则是天心;反之,专其利者,则是凡心。“与民共其利,天心也。独专其利,凡心也。”“天心”与“凡心”是心之两面,人皆有之,二者相对,少一分凡心,则多一点天心。天心受到凡心的遮蔽而不纯粹。此与朱子人心、道心略相应。“吾人学不大进,只为被凡心绊却,故天心不纯。”(83)庄渠又提出“民心”与“天心”相应。天命在于民心,与民心相合方才合乎天心,“合得民心方才合得天心”。民心又取决于“君心慎与不慎”及君心是否有“弘天之学”,天心、君心、民心构成一循环关系。
六批判、融合与重建
庄渠之学既有取于朱、王,又严厉批评朱子学沦为支离功利之俗学,阳明学流于空言无实之讲学。庄渠对此两种学风极为忧虑:“世道之衰极矣,人才至于今每下,则以科举坏之也。而迩来讲学者众,天其将兴斯文乎!而又往往好为大言,太朴愈散,徒长骄肆,不知天意终当何如?”(84)庄渠认为功利俗学较阳明学更为可恶。阳明学尽管空谈,但仍是关乎道德而非功名之空谈,且对功利俗学深具矫正之效,故庄渠对此学实抱有期盼,故亦特别加以批评。因彼时阳明讲学之风极为兴盛,具有耸动人心之效果,弊病亦不易发现,而俗学支离、流于功名的弊端显而易见,且一直以来都不乏批评。庄渠批评王学以“讲学”自居,实则流入有“讲”无“学”的境地。“讲而不学者众也,是以讲为学者也。”(85)庄渠与欧阳崇德、聂豹、王畿、邹守益、唐顺之、季本等王学学者关系密切,屡屡批评王学“收敛停蓄”的静养工夫不够,“和合议论”太多,犯有言过于行的毛病,当遵循“讷言敏行”之教。如他反复论及王畿曾反省自身缺乏收敛停养含蓄工夫,当于谨言上作内讼自求工夫。“昔承教时,每见自讼只于和合议论宛转世情上用功,不曾收敛停蓄。至哉言也。”(86)“岁莫王汝中过我,自咎只于宛转世情、和合议论上用功。不曾收敛停蓄。”(87)庄渠批评王学“言学太易易”的毛病,将之与晋代“清谈”并称,实开以“清谈”论王学之先。庄渠同样属于以禅学批王学的先行者,明确指出阳明激于对功利俗学之不满而引儒入佛,实难辞其咎,“阳明盖有激者也,故翻禅学公案,推佛而附于儒”。(88)庄渠又指出王学根本之弊在于未能辨析意念气质与良知心志之别,有认气为心(志)之弊,导致此心脱离道德本位而流于意气空虚。“勿认意气为志……虚台此心,不在本位。”(89)他也批评了阳明学一味相信良知,反对经典权威的态度,产生了“自高”“自误”之弊。“然非笃信圣人,或能自误,以故一遵圣贤之言,就自己身上体贴去做,见到的然处,方敢自信,虽然,犹恐易差也。兹承来谕厌时学之自高,可谓确论。”(90)
庄渠试图调和朱学与王学两派对立局面。他在给徐爱的信中表达了对两家门户私见的忧虑,希望能抛开私见,商议解决王学空言近佛,朱学庸俗支离的弊病,以求归一。“承惠书,深惩吾党各立门户之私,意极倦倦。……安得吾辈同志数人相与聚首一处……辨异端近似之非,振俗学支离之弊。务求至当归一,精一无二,剖破藩篱,以为大家。岂不快哉。”(91)庄渠对朱、陆得失的正反评价亦显示其为学的包容性。他一方面对陆学“实做”的学风颇有维护,“近见序文深斥陆学,愚意陆学且未可非,彼其功夫虽粗,却是实做也”,(92)反复称其“振古豪杰”,《答吴长洲》言,“象山固是振古豪杰,卓然先立乎其大者……足以大振俗学之卑陋”。他称赞象山“明白正大”“论学甚正”“天资甚高”,“超然妙契圣传”。反思往昔指责陆学为禅学是自身见识鄙陋,此反思对沉溺于朱子的学者有所触动,“昔议其近于禅学,此校之陋也”。同时他批评象山“气质太粗”、受虚气、客气拖累,以气为心,故未能达道。“犹有虚气骄志……去渊骞尚远”,“学未近道,客气累之也”。他指出朱子“广大刚健笃实明睿”,缺点则是过于支离,“用志或分,凿开混沌”。庄渠以静养天根之学为主旨,试图使朱王二家至当归一,认为如能做到涵蓄停养工夫,“则昔日讲学异同皆不必论矣”。此主静固守工夫,包括固守其心,收心工夫,固守其舌、扫除言语见解等法门。他主张“完养不轻发”即孔孟之道所在,亦是明道能传孔孟之道的根本,要求学者作潜龙勿用存养工夫。“慨自孔孟既没,唯明道深得其传。正以完养不轻发耳。”(93)
黄宗羲评价庄渠继承崇仁一派,而又有所变化“转手”,但仍未脱其“矩矱”。“转手”可理解为庄渠受到王学影响,有由朱子“两轮哲学”转向近乎王学的“合一”论倾向。如敬斋等坚持朱子动静、知行的二分说,主张静养动察,重视诚意慎独,庄渠则贯动静为一,主知行并进合一,尤重静养知本,突出“人生而静”的天根之学。又如较之敬斋“有理而后有气”的理先气后,庄渠则突出了“气”的主宰地位,强调理在气中,批评理气心岐而为三,主张三者皆归于气,言“天地间祗有一气,其升降往来即理也。其得之以为心,亦气也”(94),黄宗羲认为如此,则庄渠之“理”成为“死物”“闲物”,可见其有气本论倾向。“转手”亦表现为庄渠对心学之包容、接纳及影响。如庄渠由最初排斥攻击象山为禅学,转向表示钦佩,体现出对于师门辟陆的“转手”。“先生疑象山为禅,其后始知为坦然大道。则于师门之教,又一转矣。”(95)庄渠“至善不以善言、不与恶对”说与王学“无善无恶”之说颇为同调,“知止见性”论与黄绾“艮止”、李材“止修”之学相通,“静养天根”学被认为启发了聂豹归寂思想。“格物知本”论与王艮“格物知本”、高攀龙“知本则物格”说相似,养德养身一体论亦与王龙溪“养德而养生亦在其中”说相通。然而,尽管庄渠确有不少偏离朱子学处,黄宗羲认为其仍在朱子学“矩矱”内,他对阳明学“良知”“格物”“心即理”等核心宗旨皆未接受。
综上所述,处于朱子学与阳明学两股思潮对峙下的魏庄渠,不满于二家支离与空寂之学病,立足于静养、复性之学,试图通过对《大学》的创造性再诠,来达到重整理学的目的,其思想呈现出“介于朱、王二本之间”的特色,堪称明代理学朱、王之外第三条路线的探索者。它深刻启发我们不能囿于“非朱即王”的观点拘泥地看待明代理学,故对庄渠思想加以全面深入的研究,实为推动明代理学研究及《大学》诠释的应有之义。
注释:
①张学智:《明代哲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99页。
②[清]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一,中华书局,2008年,第14页。
③[明]魏校:《大学指归》,《四库全书存目》经部156册,齐鲁书社,1997年,第571页。
④[明]魏校:《复高汝白》,《庄渠遗书》卷三,《四库全书》第126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742页。
⑤[明]魏校:《朱氏遗书序》,《庄渠遗书》卷六,第812页。
⑥[明]魏校:《与李才庸》,《庄渠遗书》卷三,第755页。
⑦[明]魏校:《答欧阳崇一》,《庄渠遗书》卷三,第757页。
⑧[明]魏校:《大学指归序》,《大学指归》,《四库全书存目》第156册,齐鲁书社,1997年,第543页。
⑨[明]魏校:《复沈一之》,《庄渠遗书》卷四,第771页。
⑩[明]魏校:《大学指归》,第544页。
(11)[明]魏校:《大学指归》,第544页。
(12)[明]魏校:《大学指归》,第545页。
(13)[宋]黎靖德:《朱子语类》卷101,《朱子全书》第十七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393页。
(14)[宋]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2004年,第10页。
(15)陈来:《有无之境》,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04页。
(16)[明]魏校:《复毛希秉》二,《庄渠遗书》卷十五,第952页。
(17)[明]魏校:《庄渠先生门下质疑录》(以下简称《质疑录》),《续修四库全书》第93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63页。
(18)[明]魏校:《答欧阳崇一》,《庄渠遗书》卷四,第766页。
(19)[明]魏校:《大学指归》,第545页。
(20)[明]魏校:《答甘钦采》,《庄渠遗书》,第774页。李材亦有类似说法,言“总千圣渊源之的,只是教人知本,只是教人知止”。
(21)[明]魏校:《与林相》,《庄渠遗书》卷四,第774页。
(22)[明]魏校:《大学指归》,第545页。
(23)[明]魏校:《与徐少参》,《庄渠遗书》卷十二,第910页。
(24)[明]魏校:《大学指归》,第545页。
(25)[明]魏校:《答甘钦采》,《庄渠遗书》,第774页。
(26)王畿《南游会记》论及庄渠与阳明有关于静、动工夫的交涉:尹洞山举阳明语庄渠“心常动”之说。先生曰:“然庄渠为岭南学宪时,过赣。先师问:‘才子如何是本心?’庄渠云:‘心是常静的。’先师曰:‘我道心是常动的。’庄渠遂拂衣而行。……庄渠曰:‘圣学全在主静……”又曰:“学有天根,有天机,天根所以立本,天机所以研虑。”[清]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十二,第248-249页。
(27)[明]魏校:《与穆伯潜》,《庄渠遗书》卷三,第751页。
(28)[明]魏校:《与唐虞佐》,《庄渠遗书》卷三,第744页。
(29)[明]魏校:《答吕仲木》,《庄渠遗书》卷三,第752页。
(30)[明]魏校:《答彭通判》,《庄渠遗书》卷十四,第945页。
(31)[明]魏校:《与吕仲木》,《庄渠遗书》卷十四,第939页。
(32)[明]魏校:《与王纯甫》,《庄渠遗书》卷十一,第885页。
(33)[明]魏校:《答王仲实》,《庄渠遗书》卷十四,第939页。
(34)[明]魏校:《与郑壻若》,《庄渠遗书》卷十五,第959页。
(35)[清]黄宗羲:《明儒学案》,第47页。
(36)[明]魏校:《答陈元诚》,《庄渠遗书》卷四,第779页。
(37)[明]魏校:《与邵思抑》,《庄渠遗书》卷十三,第925页。
(38)[明]魏校:《与杨实夫》,《庄渠遗书》卷十三,第926页。
(39)[明]魏校:《与高汝白》,《庄渠遗书》卷三,第740页。
(40)[明]魏校:《质疑录》卷一,第364页。
(41)[明]魏校:《答曾太平》,《庄渠遗书》卷十二,第907页。
(42)[明]魏校:《质疑录》,第363页。
(43)[明]魏校:《大学指归》,第546页。
(44)[明]魏校:《大学指归》,第547页。
(45)[明]魏校:《与顾惟贤》,《庄渠遗书》卷三,第747页。
(46)[明]魏校:《大学指归》,第547页。
(47)[明]魏校:《与顾惟贤》,《庄渠遗书》卷三,第747页。
(48)[明]魏校:《大学指归》,第551页。
(49)[明]魏校:《大学指归》,第551页。
(50)[明]魏校:《大学指归》,第547页。
(51)[明]魏校:《大学指归》,第550页。
(52)[明]王阳明:《传习录下》,《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24页。
(53)[明]魏校:《答胡郡守孝思》,《庄渠遗书》卷三,第739页。
(54)[明]魏校:《大学指归》,第553页。
(55)[明]魏校:《大学指归》,第550页。
(56)[明]魏校:《答甘钦采》,《庄渠遗书》卷四,第774页。
(57)[明]魏校:《大学指归》,第550页。
(58)[明]魏校:《大学指归》,第550页。
(59)[明]魏校:《质疑录》,第363页。
(60)[明]魏校:《大学指归》,第552页。
(61)[明]魏校:《与王纯甫》,《庄渠遗书》卷四,第776页。
(62)[明]魏校:《与林相》,《庄渠遗书》卷四,第788页。
(63)[明]魏校:《与梁仲用》,《庄渠遗书》卷四,第895页。
(64)[明]魏校:《复余子积论性书》,《庄渠遗书》卷十三,第932页。
(65)[明]魏校:《答王直夫》,《庄渠遗书》卷四,第757页。
(66)[明]魏校:《与馆中诸生》,《庄渠遗书》卷十五,第949页。
(67)[明]魏校:《与馆中诸生》六,《庄渠遗书》卷十五,第952页。
(68)[明]魏校:《体仁说》,《庄渠遗书》卷五,第793页。
(69)[明]魏校:《体仁说》,《庄渠遗书》卷五,第795页。
(70)[明]魏校:《大学指归》,第553页。
(71)[明]魏校:《大学指归》,第555页。
(72)[明]魏校:《答顾禹锡》,《庄渠遗书》卷四,第769页。
(73)[明]魏校:《与余子积别纸》,《庄渠遗书》卷十一,第888页。
(74)[明]魏校:《大学指归》,第551页。
(75)[明]魏校:《质疑录》卷一,第364页。
(76)[明]魏校:《大学指归》,第553页。
(77)[明]魏校:《复周充之》,《庄渠遗书》卷三,第731页。
(78)[明]魏校:《大学指归》,第556页。
(79)[明]魏校:《答陈元诚》,《庄渠遗书》卷四,第779页。
(80)[明]魏校:《复王郡守子正》,《庄渠遗书》卷十二,第915页。
(81)[明]魏校:《大学指归》,第556页。
(82)[明]魏校:《周礼沿革传序》,《庄渠遗书》卷六,第809页。
(83)[明]魏校:《与沈一之》,《庄渠遗书》卷四,第781页。
(84)[明]魏校:《与王纯甫》,《庄渠遗书》卷四,第757页。
(85)[明]魏校:《与邹谦之》,《庄渠遗书》卷四,第779页。
(86)[明]魏校:《与王汝中》,《庄渠遗书》卷四,第766页。
(87)[明]魏校:《答欧阳崇一》,《庄渠遗书》卷四,第766页。
(88)[明]魏校:《复沈一之》,《庄渠遗书》卷四,第771页。
(89)[明]魏校:《复王道思》,《庄渠遗书》卷四,第769页。
(90)[明]魏校:《答沈一之》,《庄渠遗书》卷四,第761页。
(91)[明]魏校:《复徐日仁》,《庄渠遗书》卷十一,第899页。
(92)[明]魏校:《与崔子钟》,《庄渠遗书》卷四,第783页。
(93)[明]魏校:《答周道通》,《庄渠遗书》卷三,第749页。
(94)[清]黄宗羲:《明儒学案》,第47页。
(95)[清]黄宗羲:《明儒学案》,第48页。
责任编辑:近复
作者文集更多
- 【许家星】饶双峰文献的钩沉、整理与新见 10-13
- 【许家星】吴仲迂《语类次》思想及其诠释 12-13
- 【许家星】张栻的道统思想 04-27
- 【许家星】道之辩——以船山对双峰《学》··· 02-16
- 【许家星】并非“塞责抄誊”:《四书大全··· 12-08
- 【许家星】即气论以论仁学——李存山先生··· 10-07
- 【许家星】精一之传——王阳明道统思想探幽 05-28
- 许家星 著《经学与实理:朱子四书学研··· 06-26
- 【许家星】朱子的道统世界 10-23
- 【许家星】“羽翼朱子而有功于圣门”——论··· 07-09
微信公众号
儒家网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

微信公众号
儒家网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