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永健】人“统治”人何以正当? ——亚里士多德“Natural Slavery”问题释解与演绎
人“统治”人何以正当? ——亚里士多德“Natural Slavery”问题释解与演绎
作者:贾永健
来源:《原道》第35辑,陈明、朱汉民主编,湖南大学出版社2019年1月出版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四月二十日辛酉
耶稣2019年5月24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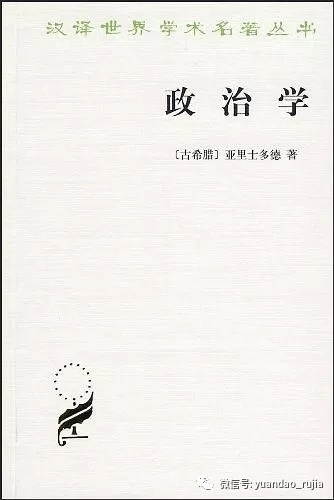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出版)
内容提要:人们往往会形成这样一个印象:亚里士多德在为奴隶制辩护。亚里士多德对“奴隶制”的“美论”并非是为奴隶制辩护,而是从自然目的论出发对“Natural Slavery”学说的阐述和建构。
他认为,人之天性中存在的理性差别根本上决定人(理性完全者)“统治”人(理性不足者)的自然正当性和永恒性。它与中国儒家基于人之德性差异的统治正当论存在许多共通契合。
在现代语境下,“Natural Slavery”实际是一种政治社会领域的理性分工论:人的理性差异决定人与人必然存在“脑力与体力、管理与被管理”分工和分化。
面对所谓“禀赋决定论”甚至“种族主义”的质疑和批判,亚氏学说必须充分吸纳“自由开放、机会平等”现代文明观念方能更具解释力和生命力。展望未来,或许人工智能的发展会为消灭“社会分工”这种人之“异化”根源创造积极可能。
关键词:亚里士多德;Natural Slavery;社会分工;理性主义
一、问题的提出
(一)亚里士多德是在为奴隶制辩护吗?
读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人们往往会形成这样一个印象:亚里士多德在为奴隶制辩护。
他试图用推理和事实等各种方式的充分论证,赋予“奴隶制”以当时最美好的词汇:“自然的”“有益的”“互利的”“正义的”,并以“有人天生就应做主人、有人天生就该是奴隶,对奴隶来说,被奴役不但有益而且公正”。
这使“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现代读者对于亚里士多德支持奴隶制常常感到尴尬”。尴尬的原因在于,现代读者观念中,人人生而平等自由,符合这种观念的制度才是正义的;而现实的奴隶制造成人对人的压迫与奴役;奴隶被当做物件被任意处置、摧残甚至被剥夺生命。
奴隶制应该是严重摧残人性、践踏人之尊严的“万恶制度”,何谈正义?何谈有益?何谈互利?而这个伟大思想家,竟然支持这种丑恶制度!对此,持现代观念的读者当然感到不解和尴尬。
对亚里士多德的这种支持奴隶制态度,近代启蒙思想家卢梭对此强烈反对,批判亚里士多德是“倒果为因”,甚至将其作为《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与基础》的主要批驳对象。自此以来的现代学者也通常将其归因于他那个奴隶制时代的偏见。
例如亚里士多德的研究大家Ross在其著作《亚里士多德》中解释说:“像这样已经成为希腊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一部分的安排,如奴隶制,亚里士多德会认为其属乎事物本性,这一点固然令人遗憾,但也毫不奇怪。”
另一位学者Mulgan也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理论》一书中提醒读者:“我们不可忘记……他写作其中的社会把奴隶制视为当然,奴隶制受到普遍承认”。
希思则直接要求摈弃这种让人窘迫的学说,因为它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偏见并且论证也不充分,根本上是错误的。
而在我国,长期以来,认为这是由于“亚里士多德本人的阶级立场局限”的观点,在许多政治思想史、法律思想史等教材和著作中更是随处可见。
比较典型的说法,如“对于这种分明是由于社会经济的必然演变而产生的、用国家暴力镇压来维持的奴隶制度,亚里士多德却硬要把它说成是‘自然的’或‘合乎理性的’制度。可见,作为奴隶主阶级的大知识分子,亚里士多德的阶级偏见是极深的。”
总之,古今中外许多学者都把亚里士多德称赞的“奴隶制”与现实奴隶制作为同一事物,而进行批判与阐释的。

(雅典城邦)
但亚里士多德所论“奴隶制”的美好与现实奴隶制的残暴之严重冲突,又该如何解释呢?甚至细心的读者还会发现,亚里士多德这位哲人,对奴隶制的论述存在“前后矛盾”问题。
如“自然赋予自由人和奴隶不同的身体”,奴隶“身体粗壮以适于劳作”,自由人的身体挺拔适合作战和政治活动(1254b25-30),而后文却又说“有些奴隶具有自由人的灵魂,有些奴隶具有自由人的身体”(1254b35)。
有学者干脆认定“亚里士多德关于奴隶制的那些赞美之言,一定是错误的”;也有学者指出其对奴隶制的赞美从根本上与其宏大的自然目的论信条存在抵牾。
若将亚里士多德视为一位思想巨人,那么就自然形成就有这样一个疑问和困惑:上述吾等后人极易发现的矛盾和谬误,难道这位哲人对此都毫无察觉抑或是故意视而不见?
前述学界对亚里士多德之奴隶制态度的各种解释,都因或多或少存在着误读和偏狭,而不能通顺解答这个困惑。
对此,我们既不能完全站在现代观念立场上对亚里士多德支持奴隶制的态度简单地感觉尴尬或给予批判,也不能完全从当时时代背景出发以一种力求全面客观的姿态来包容和同情地理解。
本文试图引入这样一个两维视角,即亚里士多德的“奴隶制”论述,其实包含有两个维度:一是形而上的“自然目的论”维度;二是形而下的“现实约定法”维度,相应也就有两种奴隶制:一是“自然”奴隶制;二是“现实”奴隶制。
坚持区分这两个维度的,来阅读《政治学》,或许可以对亚里士多德的“奴隶制”问题获得一个通顺理解。
(二)亚里士多德所赞“奴隶制”到底何指?
《政治学》一开始就将“奴隶制”作为讨论主题,但直到第六章才点明“奴隶制话语”存在两个叙述维度。
他说:“奴隶制和奴隶这两个词语有两重意义:一种因法律而生的,这种法律是一种战争约定:“战败者为战胜者的奴隶”;另一种是因自然而生的”(1255a5-10)。
因法律而生的奴隶制,这种法律主要是战争约定,因而是一种约定法,那么这种奴隶制也可以说是因“约定法”而生的奴隶制。
这表明《政治学》的“奴隶制”表述,有两个需要区分开来的维度:一是形而下的“现实约定法”维度;二是形而上“自然目的论”维度。相对应也就有两种奴隶制概念:一是现实奴隶制;二是自然奴隶制。
首先,是现实奴隶制。它是指根据战争中“战败者为战胜者奴隶”的法规,而产生的奴隶制。这种法规本质是约定性的,所以这是一种约定的奴隶制,不是自然的。
法规背后的正义观是,“正义就是强者的统治”;而反对这种奴隶制法规的正义观是“正义就是仁善(benevolence)”。
其次,是自然奴隶制。这是指根据自然本性中“德性高贵者应当做统治者(ruler)或主人(master)”(1255a20)的自然法而产生的奴隶制。
这种法则的根据乃是“自然”(Nature),因为自然趋向于(Nature tends to)根据德恶区分出自由人和奴隶(1254b25-30、1255a40),因而这是一种“natural slavery”观念。
其实这种观念并非是亚里士多德的创造,也普遍存在于当时人们的意识观念中。他们承认,一些人在任何地方都是奴隶,有些人在任何地方都不是奴隶,有些人在任何地方都是高贵的,而非希腊人只在自己本邦是高贵的。(1255a25-30)
于是,在两种维度下,“也就存在着两种高贵和自由:一种绝对的,一种相对的”(1255a35)。
“自然的奴隶制”下的高贵和自由乃是绝对的,而源于约定法的现实奴隶制所区分出的高贵和自由则是相对的。那么在《政治学》卷1中,亚里士多德所谓的“奴隶制”指是那种呢?
换言之,亚里士多德所努力论证予以“支持辩护”的“奴隶制”到底何指呢?答曰,是基于形而上的“自然目的论”而演绎出的“Natural Slavery”。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政治学》开始论及奴隶制时,就是从“自然目的论”维度出发的,因此从开始就确定了第1卷讨论的奴隶制主要是“自然的奴隶制”。
《政治学》在第一章伊始提出“人类政治共同体应当以最高善为目的”的终极论点后,在第二章就开始考察世界的自然结合关系:从雌雄(男女)关系到主奴关系,确立了他论述的自然主义基调和视角。

(奴隶市场)
他认为,为自身延续而形成的男女结合,并非有意而为,而是出于自然本性的驱使;自然的“统治者”与自然的“被统治者”的结合,也是因为共同保全的缘故。
具有理性预见能力的人,就是自然的“统治者”和自然的“主人”,而以身体劳作的人就是自然的“被统治者”和自然的“奴隶”。而且此后也没有任何文字直接指明或相关内容间接表明,他改变了论述对象。
第二,亚里士多德自己说,《政治学》一开始所谈的奴隶制就是“自然”奴隶制和“自然”奴隶。他在第六章中说,“当人们使用这个词(奴隶——引者注)时,他们真正所意味的正是我们开头所论的自然奴隶”(1255a30)。
第三,第1卷从第二章以后谈及奴隶制的各章都有直接表述,表明其所论“奴隶制”即是“自然的”奴隶制。
比如第三章的主题,是在自然意义上构成城邦最基本部分——家庭的基本要素:主奴、夫妻和父子。
因此,这里的主奴关系,也是自然意义上的。第四章主题则是考察自然奴隶的本性和职能,“那种在本性上不属于自己而属于他人的人,就是自然的奴隶。”(1254a14)
第四,亚里士多德运用诸如正义、有益、互利、友谊等美丽词汇所修饰的“奴隶制”,在第一卷第五章中被直接指明就是“自然的”奴隶制;而且从逻辑上这些美丽修饰也只可能适用于自然奴隶制,若用于现实奴隶制,则有违人们的历史常识。
第一卷中,亚里士多德在多处对“奴隶制”进行了美好修饰,所用词汇包括:“自然的”“有益的”“正义的”,具体表达比如“主奴存在共同利益”(1252a30-1252b1)、“主奴之间是互利友好的”(1255b10-15)、“奴隶制不但是正义而且也是有益的”(1255a1、1255b5)。
第五章最后还说,“于是很明显,有些人是自然的自由人,有些人是自然的奴隶,对自然奴隶来说,奴隶制不但是正义的而且是有益的”(1255a1-5)。
自然的自由人与自然的奴隶组成的主奴关系,形成的奴隶制当然是“自然的”奴隶制。因此,这里“正义且有益的奴隶制”是指“自然的奴隶制”,直接佐证了亚里士多德所赞美的“奴隶制”,是“Natural Slavery”。
而且,亚里士多德论证“Natural Slavery”之自然、有益、正义,也是完全在自然意义上的,是从他的“自然目的论”体系出发的理路。
他指出,人和人之间的理性和德性的自然差别,决定了自然主奴的区别与存在,从而证明了自然奴隶制的自然性;理性和德性差别也决定了自然主奴的“职能”(function/task)差别,自然奴隶制使得二者各自自然职能和目的得以充分发挥。
因此,自然奴隶制对主奴双方都是有利的,在此意义上主奴之间也就是“互利的”“友好的”;既是自然又是有利的,自然奴隶制因而也是符合正义的。
但历史现实中的奴隶制,基本是给予强力和战争产生的,不是出于自然的;是奴隶主对奴隶的残酷压迫,而非对奴隶是有利的,奴隶主和奴隶之间也不可能是互利友好的。
因而在人们的历史常识中,奴隶制是残暴的、血腥的、灭绝人性的,根本不可能是符合正义的。因此,亚里士多德笔下的美好“奴隶制”,只有指“自然的奴隶制”,而非现实的奴隶制,这样从历史和逻辑上才讲得通。
第五,把“Natural Slavery”认定为亚里士多德的主论对象,坚持与现实奴隶制区别开来,方可对奴隶制相关矛盾论述和冲突情况获得圆通理解。
比如,其一,在自由人和奴隶的身体特征区分方面,自然意图与现实情况的矛盾。
“自然有意区分奴隶和自由人的身体:让奴隶身体粗壮以便用身体劳作提供生活必需品,而自由人的身体则无助于体力劳动,却具备挺拔和其他适于政治生活的特征。
但相反的情况也常常发生,有些奴隶具有自由人的灵魂,有些则具有自由人的身体”(1254b25-30)。也即是说,对于主奴关系,现实中存在着与自然意图相反的情况和类型。
其二,在自由人和奴隶的德性区分方面,自然意图与现实情况的矛盾的不一致。
“自然意图根据德和恶来区分出自由人和奴隶、高贵者和卑微者,让良善者生良善者,但却做不到总是如此”(1255a40-1255b1),现实中“并非所有奴隶都是自然的奴隶,也并非所有自由人都是自然的自由人”(1255b1-5)。
其三,同样是奴隶制,“合乎自然的主奴关系中,主奴之间互利友好,而出于约定法和强力的奴隶制中,主奴关系情况则相反”(1255b1-15)。
对以上矛盾和冲突,只有放在自然和现实两重维度奴隶制语境下,只有将亚里士多德所主张的“奴隶制”勘定为“Natural Slavery”,方可获得通顺理解。即这种冲突的本质乃是奴隶制的自然与约定维度、理论与现实维度之间的冲突。
二、“Natural Slavery”作为理性“统治”关系而具正当性
亚里士多德把“自然目的论”体系中的“奴隶制,表述为“Natural Slavery”,这个名称下面的实质含义是什么?
换言之,以人类高级事务——“政治”(Politics)所命名的《政治学》讨论的“Natural Slavery”,到底意欲探究人类的何种政治关系呢?深入研析《政治学》文本,可知即是人类理性主导的“统治”关系。
(一)“Natural Slavery”即是“自然统治”关系
第一,《政治学》第一次提到“自然的主奴”关系,就与“自然统治”关系是同义并列使用的。
他说:“具有理性预见能力的人,就是自然的统治者(ruler)和自然的主人,而以身体劳作的人就是自然的被统治者(ruled)和自然的奴隶”(1252a30-1252b1)。
这句话表明,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自然的“主奴”关系就是以理性为主导的“统治”关系。这也说明,亚里士多德的“统治”关系论的主导标准,乃是理性,因此其思想内核,是理性主义的。
第二,亚里士多德的随后行文多处把“统治者”和“主人”同义并列使用,认为“Natural Slavery”中的主人,就当然也是“统治”关系中的“统治者”。
比如,第六章就有两处,其一,“德性(virtue)高贵者应当做统治者或主人”(1255a20);其二,“同样,很明显,人类确实存在着奴隶和主人的有益且正义的区分以及被统治者和统治者的区别,统治者事实上就是主人”(1255b5-10)。
第三,亚里士多德在第五章,通过考察灵魂与肉体、雄性和雌性关系得出“自然本性高贵者(natural superior)为统治者,自然本性处于低位的为被统治者”这样一个普遍结论后,说:“这个结论也普遍适用于整个人类”(1254b10-15)。
然后他接着说,“如同灵魂与肉体、人与兽之间存在的高低之别一样,人们之间也存在着高低之别,那些根据其职能充其量只能使用身体的人,就是自然的奴隶(natural slaves)”(1254b15-20)。
可见亚里士多德的“natural slave”,就是在自然目的等级体系中,处于低位的人,他们应当接受处于等级高位的主人的统治。
第七章也说,“主人”“统治”的对象是自然的“奴隶”,以区别于以自然自由人为统治对象的政治家统治(1255b20)。因此,亚里士多德的“Natural Slavery”,也就是“自然统治”关系。
第四,第五章开始的设问,提出三个“Natural Slavery”相关问题:一是自然(by nature)本性和功能如此的人,即自然奴隶是否存在?二是这样的人成为奴隶,对他们来说是否有益并且符合正义呢?
三是抑或所有奴隶制都是违背自然的呢?(1254a20)接着他回答说,“统治”与“被统治”不仅必然而且有益,有些人天生就注定做“统治者”,而其他人天生注定做被“统治者”(1254a20-25)。
这里针对“Natural Slavery”的相关问题,却借助讨论“统治关系”来回答,可见,在亚里士多德看来,“Natural Slavery”与“自然统治”关系是等同的。
事实上,奴隶制作为人类社会较早的一种统治形式,在亚里士多德的时代,也是主流统治形式。囿于时代局限,亚里士多德只能把奴隶制作为当时人类社会的基本统治关系形式,作为他讨论人类“统治”关系的唯一概念和用语。
(二)理性是自然“统治”关系的主导标准
虽然从外在行文表述看来,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是在讨论“Natural Slavery”,但从实质内容上看,他乃是在探讨人类理性主导的“统治”关系问题。
他是以“奴隶制”之名和形,行考察人类“统治”关系问题之实,提出了理性主义的“统治”关系论。在亚里士多德的自然统治关系论中,理性是其核心标准和根本基石。它对人类“统治”关系的形成和运行都具至关重要的意义。

(古希腊天文学)
首先,人类形成“统治”关系要靠理性。在第二章关于“城邦起源”的探究中,亚里士多德说,“就像我们说的,自然造物都是有目的的,而人是唯一具有语言的动物。
……语言能清楚地表达利害,并进而阐明正义与不义。和其他动物比较,人之独特性在于:他是唯一能对好与坏、正义与不义感知的动物。正是这些人类感知的结合才形成了家庭和城邦。”(1253a10-20)
在这里,希腊词汇logos,可译为“理性”“语言”“道理”等。那么,“语言”就是人类理性的一种表现形式。
这句话的逻辑链是这样的:理性表现为语言,因而语言能表达利害、正义与不义,进而人类具有对好与坏、正义与不正义的感知。这些感知的结合才形成了家庭和城邦,结成“统治”关系。因此,是理性让人形成了“统治”关系。
其次,人的理性差别决定其“统治”地位的差别。在第二章首次论及“统治”关系时,亚里士多德就说:“具有理性预见能力的人,就是自然的统治者和自然的主人,而以身体劳作的人就是自然的被统治者和自然的奴隶”(1252a30-1252b1)。
人之所以分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就是因为人们的理性存在差别。“统治者的职能要求他作为一个理性大匠师”(1260a15-20),具备完善的审慎理性能力;“奴隶是人,也分享有理性能力”(1259b30),“那些自身没有理性、却能分享理性理解能力的人,就是自然的奴隶”(1254b20-25),也就是自然的“被统治者”。
理性之所以绝对决定着人与人的“统治”地位,根本原因还是在于灵魂各部分的关系就是如此。“灵魂包含统治部分和被统治部分,两部分有德性差别。这个德性差别是指:统治部分属于理性的部分,被统治部分则属于非理性的部分”(1260a5-10)。
灵魂中,理性部分“统治”非理性部分是自然且有益的,因而人类中,也应当是理性完善的人“统治”理性不足的人。
再次,不同理性能力的“被统治者”,其被“统治”的自然方式也是根本不同。“自由人统治奴隶、男人统治女人、父亲统治孩子的方式是各不相同的,是因为这些人灵魂各部分存在状态是不同的。
深思熟虑的完善理性能力,在奴隶灵魂中完全缺失;在女人灵魂中存在却不占主导地位;在儿童灵魂中也存在但还处于不成熟状态。”(1260a10-15)
概言之,人对人的“统治”根本上乃是理性的“统治”。因此,亚里士多德的自然“统治”关系论本质上是理性主义的;所谓“自然性”,即是指“理性”。
自然的“统治”关系,就是以理性为主导权威和根本标准的“统治”关系。
三、作为正当“统治”关系的“Natural Slavery”近似现代管理分工关系
其实,若对“Natural Slavery”具体内涵的深入探析,可以发现与其基本同义的“自然统治(rule)”关系,作为中心词的所谓“统治”(rule),在语义上更接近今天的“管理”(rule)一词,而非现代意义上的以“强力”为基础的“统治”。
若全面深入分析亚里士多德的这个理性主义“统治”关系论,就可以发现,亚里士多德所赞成的“互利友好而正义的”的“Natural Slavery”,在当今语境下,更符合于现代政治社会领域中的管理分工关系。
(一)亚里士多德理性主义“统治”关系论的基本内涵
《政治学》第1卷集中论证和阐释了亚里士多德的“Natural Slavery”理论,也即他的理性主义统治关系论。概括起来,其包含如下内容:
第一,人统治人的“统治”关系是永恒存在的。人类为什么存在“统治”关系呢?第五章开始就回答说:“世上存在统治与被统治的统治关系,不仅必然,而且有益”(1254a20),然后从逻辑推理和事实观察两个角度予以了论证。
首先,一切生命物都存在“统治”元素与“被统治”元素,人类当然也不例外。这里他从普遍到特殊、从抽象到具体,运用了一个演绎推理的论证方法。

(柏拉图)
亚里士多德先提出一个普遍命题说,“一切组合成整体的部分之间,无论是连续的还是不连续的,都必然有统治和被统治地位差别的存在”(1254a30)。
这个命题的普遍性表现为,它不但适用于生命物中,在无生命物中也同样适用,比如乐曲。为什么生命物中普遍如此?因为这个特性是由自然整体赋予的,所以一切在自然状态中的自然物,都具有如此自然特性。(1254a30-35)。
因此,从自然意义上说,属于自然之一部分的人类,当然也必然存在“统治”关系。
其次,观察灵魂和肉体、理智与情欲、人类与动物、雄性和雌性的关系,归纳得出“高贵者统治低微者是自然且有益”的结论(1254b5)。
这一结论“也普遍适用于所有人类”(1254b15),因为人与人之间也存在诸如灵与肉、人与兽类似的高低之别。因此,自然本性高贵的人也应当“统治”自然本性低微的人,人对人的“统治”关系必然存在。
那么,人对人的“统治”关系是否是永恒的呢?亚氏持肯定意见。
他从“统治”关系存在的原因来论,首先,自然是永恒的,“生命物中都存在统治与被统治关系”的自然法则也是永恒运行的;
其次,人与人之间的自然本性也永恒存在高低之别,因为自然赋予了每个人不同的职能,而每个人的自然本性(德性和理性)与各自职能相适应;自然职能永恒差异,自然本性永恒存在高低之别。
总之,自然的永恒,决定了人对人的“统治”关系是永恒存在。
第二,人对人的“统治”根本上是理性的“统治”。所以,实质说来,人类社会的“统治”关系中,谁的理性能力强,谁就能也应该担当“统治者”和领导者。具备完善的理性审慎能力,是“统治者”的根本特质(1260a15-20)。
第三,有些人天生就是“统治者”,有些人天生就是“被统治者”。亚里士多德认为,谁该做“统治者”,谁该做“被统治者”,是基于每个人的自然本性和自然职能,是自然所赋予和自然秩序所决定的,是天生的,因而是不能改变的。
第四,在“统治”关系中,“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是共利的、友好的。《政治学》的直接相关表述有:“主人和奴隶具有共同的利益”(1252b1);“对自然奴隶来说,奴隶制(slavery)不但是正义的而且是有益的”(1255a1-5);
“自然奴隶做奴隶和被统治者,自然自由人自然地该做主人和统治者,这不但是的正义而且也是有益的”(1255b5)。所以,“这种主奴(即自然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确实是互利友好的关系”(1255b10-15)。
第五,“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是一种主次关系和主从关系。第五章说,“统治”元素与“被统治”元素在事物中普遍存在,生命物中如此,无生命物中也是如此,如乐曲中的主旋律和辅曲。(1254a30-35)
这里以“乐曲”例证,直观表明事物中普遍存在的“统治”元素和“被统治”元素的关系,就是主要和次要、主导和辅从的关系。
第六,“统治”关系是一种主体-工具关系。第四章在考察自然奴隶的自然本性和职能时,开始先讨论了“主体-工具”关系。
他以航海为例,把船长作为主体,他的工具为两种:一是有生命的工具——瞭望者;二是无生命的工具——船舵。瞭望员是人(human being),为什么也是工具呢?
在技艺相关领域中,于实现目标和任务的主体而言,辅助者都是相对意义上的“工具”。这个“工具”称谓,是相对性的关系称谓,正是在这个关系意义上,工具完全归属于主体“所有”。
这个关系性称谓和关系性归属,为下面把“奴隶”这类人定义为“工具”并完全归属主人“所有”做铺垫。以航海中的“主体-工具”关系,来阐释家庭管理中的“主体-工具”关系,即“主人和奴隶”的关系。
“主奴”关系中,“主人”为主体,相对的,“奴隶”是有生命的完全归属主人“所有”的实践工具。
第七,“统治”关系是一种命令-执行关系。那么“奴隶”作为工具的“实践(action)”作何理解呢?参考第七章关于做“主人”的知识和做“奴隶”的知识可以得以理解。
亚里士多德首先认为,如何做“奴隶”的知识和如何做“主人”的知识确实存在。“奴隶”根据各自自然职能(task)高低决定的工作事务不同,需要的知识也是不同的,但都是去直接行动实践(action)的知识。
做“主人”的知识,就是如何使用“奴隶”的技艺,即如何发布能让“奴隶”清晰明白怎样去做的命令。(1255b25-35)所以,“奴隶”或“被统治者”的实践事务,就是直接执行和实现“主人”或统治者的命令。故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统治关系也是一种命令-执行关系。
第八,“统治”关系也是一种脑力-体力劳动关系。《政治学》开始就说,“具有理性预见能力的人,就是自然的统治者和自然的主人,而以身体劳作的人就是自然的被统治者和自然的奴隶”(1252a30-1252b1)。
亚里士多德明确地以脑力和体力劳动差别,来作为划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标准。因此,自然也意图赋予二者差异的身体特征:自然“奴隶”(被统治者)身体粗壮适于从事劳作,自然的“自由人”(被统治者)身体挺拔适于从事政治生活。(1254b25-30)
第九,“统治”方式从形式上看,包括“政治家的统治”和“君主式统治”两种方式。第十二章详细阐述了这两种“统治”方式特征及其区别。
政治家的统治方式中,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在自然本性上平等自由,实行轮番而治;君主的统治中,统治者根据被统治者的尊敬、自身的年长(代表的丰富人世阅历)以及对被统治者的爱,进行一人的权威统治,统治者本性上优于被统治者。(1259b1-15)
(二)自然“统治”关系契合现代社会的管理分工关系
对亚里士多德自然“统治”关系论若不拘泥于文字而深入其内容,那么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亚里士多德所谓的自然(理性)“统治”关系其实是一种理性的社会分工关系。
他所论证的“统治”正当,即是在证成“管理”关系的自然正当性。因为这种自然“统治”关系的主要特征与现代管理分工关系非常契合。
第一,前述理性主义“统治”关系之主次关系、主从关系、主体-工具关系、命令-执行关系等四个层次,表明这种“统治”关系是一种分工关系。
这种主次、主从、主体-工具和命令-执行关系,非常类似现代社会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分工关系。
对社会存续发展起主导作用的管理者谋划和发出指令,被管理者则服从、落实和执行,各种社会角色各司其职,各担其责,共同促进社会良性持续发展。
这种分工,是由人类社会事务和实践必然存在“意志决策-行动执行”的结构所决定的。任何人类社会都必然存在着这种分工关系,因此,任何人类社会都必然存在亚里士多德所谓的“统治”关系。
第二,理性主义“统治”关系各主体间存在“共同利益”和“平等有爱”的特征,表明这是一种社会分工关系。
历史现实中以暴力和强力为基础的统治关系,明显不具备这些“互利有爱”的美好特征。这只可能存在于社会分工关系中。
社会分工关系中,人与人的差别或不平等,仅限于从事事务的职业差别,但其基本人格是平等的——都是人。
亚里士多德也认为,作为“统治”关系基本主体的“主人”与“奴隶”,也都是平等的,都属于人。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克伦理学》,商务印书馆2017年出版)
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指出,“主人”和“奴隶”存在良好友谊的基础,在于“他们都是人”。
“奴隶作为奴隶,和主人异格,和主人不能有友爱;但奴隶作为人,则与主人就存在着友爱。因为一个人同每个能够参与法律和契约过程的人的关系中都似乎有着某种公正。因此,每个人同每个人都可能有友爱,只要他是一个人。”(《尼各马可伦理学》1161b5-10)
人类社会各职业之间是互补协调和互惠互利的,最终目标是相同的,因此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这样,在平等人格上的分工关系之下,人们才存在着共同的基本利益——社会持续存在和良性发展,才可能互惠互利、互爱友好。
所以,自然“统治”地位不同,仅是社会分工的不同,并不意味着强力的差别甚至压迫。因此,亚里士多德才会说:“合乎自然的主奴关系中,主奴之间互利友好,而出于约定法和强力的奴隶制中,主奴关系情况则相反”(1255b1-15)。
第三,理性主义的“统治”关系中,每个人的“统治”地位差异,来源于人的自然本性的差异。自然赋予每个人的天性不同,那么每个人的自然职能也是不同。
根据各自的天性和职能,人们就相应居于不同的统治地位。也可以说是,居于不同的统治地位,承担不同的职能和分工。所以这种“统治”关系中的分工,就是一种自然性的社会分工。
人们这种自然本性和职能分工的多样化差异,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正是城邦永葆生机活力和发展动力的根源。
《政治学》第二卷第二章在讨论城邦的自然本性应该是高度一致的,还是其由多样化差异部分所构成的时(1261a15-20),亚里士多德认为,整齐划一必然使城邦毁灭(1261a15-20),而组成部分的多样化则使得各部分互惠互利。
而互惠原则正是城邦的生存基础(reciprocal EQUALITY preserves city-states,1261a30),多样化差异才能保存城邦、延续城邦,使城邦充满生机与活力(1261a20-1261b5)。所以,如Jowett指出的那样,亚里士多德思想中的社会分工法则,是一个自然法则。
第四,亚里士多德用来说明“统治”关系的例证,直接表明其所谓“统治”关系就是管理分工关系。
比如第五章说万事万物普遍存在着统治元素与被统治元素,比如乐曲中的主旋律和辅曲,而这就是这种统治关系。
这里的rule,若从现代观念出发理解为“以暴力和强力为基础”的统治,明显不合适,但理解为一种主导与辅配的管理分工则更具解释力。
同样,还有第四章中航海关系的例子,其中“统治”关系包括船长与瞭望者、船长与船舵的关系,这里的“统治”恐怕也不能理解为强力统治,而是航海事务中的分工和管理关系更为合理。
四、“Natural Slavery”之正当性的现代挑战与发展
理性主义是亚里士多德“Natural Slavery”学说主要特征,理性主义政治思潮也由此开启,并且深刻影响西方政治哲学的发展,特别是直到近现代以来的政治思想。
(一)理性至上与人人平等:现代政治思想对亚里士多德的扬弃
启蒙以来的现代政治思想与亚里士多德可谓一脉相承,推崇理性,倡导理性至上,在政治事务领域竭力排除情感、冲动、偏见等非理性因素,以理性宏观谋划和运筹帷幄人类政治事务,依照理性化的法律定纷止争、治理国家。
理性主义正是现代政治的主导标准和根本特征。具体而论:
首先,“理性化”正是现代启蒙思想家所努力推进的“启蒙”之实质。

(康德)
康德在《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一文中就说,“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
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Sapere aude!(译注:要敢于认识)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
康德这里提出的“启蒙运动就是勇于运用自己的理性”,被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称为“现代性的纲要”。
自启蒙运动以来,西方政治哲人就一直孜孜以求构建一个宏大的现代理性体系。他们不断宣扬人类的理性解放,并将以“试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方法视作为惟一可靠的获知来源;从而否定了宗教启示的权威,否定神学经典,否定传统和一切来自非理性的先验的知识形式。
人类的理性不仅可以发现蕴涵着现代“绝对真理”的普遍规则,而且可以通过逻辑将其发展成为一个完善的普遍的规则体系。
在伏尔泰看来,这场“未竟的现代性事业”无限美好,它被设计为自由、平等的乐园;在康德那里,“科学-道德-艺术”(认知工具理性-道德实践理性-艺术表达理性)共同筑起现代性的主体理性大厦。
正因为此,韦伯、福柯、哈贝马斯等现代性问题思想家给出诊断:现代社会就是一个理性统治的社会。在韦伯看来,我们所处的现代性时代,基本特征就是理性,现代社会就是一个日益理性化的社会。
他在《以学术为业》的演讲中说:我们这个时代,世界已被除魅,所独有的特征就是理性化和理智化。理性是现代社会的唯一权威。恩格斯一言蔽之:“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放弃存在的权利”。
现代政治思想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理性至上”理念,共同张扬理性,推崇理性,二者同属于政治思潮的理性主义之流。
这个理性主义观念在亚里士多德的法治思想中萌芽,终在现代法治国家里得以变为现实,理性主义统治也成为现代统治唯一“正确或正当”的方式。
但对亚里士多德,现代政治思想的最大修正,就是用“人人平等”观念对其进行根本扬弃。
亚里士多德认为,谁做统治者,谁做被统治者的分工,是基于每个人的自然本性,实质即是理性能力和相应的自然职能,是自然所赋予和自然秩序所决定的,是天生的因而是不能改变的。
而现代政治思想奠基者坚持现代性平等观,将“人人生而平等自由”作为现代政治的前提和基础。在霍布斯看来,自然状态下人人是自由平等的。洛克断言:人类天生都是自由、平等和独立的。卢梭同样认为“每个人都生而自由、平等”。
从“人人生而平等”的前提出发,现代人相信,统治关系和地位是人为的、可以改变的,并非是自然或者是天性(by nature)决定的。
人人皆有资格做统治者,而统治者是由平等的人依据民主程序自由选举出来。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每个人的基本政治权利,每个人皆有可能被选举为统治者。
这就是现代民主政治,它非常类似于亚氏所谓的“政治家的统治”(rule of statesman),是平等自由的人们轮番而治。(1259b5)
因此,有必要运用“平等”理念扬弃亚里士多德的“Natural Slavery”学说,将政治和社会各领域的职位和关系视为是“自由开放的”、对每个人“机会均等”。
这样才能更符合现代文明观念。这种依循现代文明观念的“扬弃”不仅不违背亚里士多德的理性主义理念,甚至是对理性主义政治理念的深入运用和发展。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只要具备充分完全的理性能力,具体来说就是高瞻远瞩的理性预见能力和深思熟虑的审慎行事能力(1252a30-1252b1、1260a15-20),就可以作“ruler”或“master”。
亚里士多德的局限性在于,他囿于自己“理性差异天生不可更改”的窠臼,而认为人之政治社会地位被先天决定,不可更改。这正是他被后世批判为“天性禀赋论的种族主义者”的主要根源。
而人类历史的发展实践表明,人的理性能力在先天差异基础上,是能够经过后天努力和学习得以提升的。
因此,有的人虽先天理性能力不足,但经后天的努力,习得了充分的理性远见和深思熟虑能力,那么依据亚里士多德的理性标准,当然可以作“统治者”或“管理者”(ruler)。
其实,这个“悖论”问题也为亚里士多德所注意,但却被他视为一种例外现象——“有些奴隶具有自由人的身体,有些奴隶具有自由人的灵魂”(1254b30)。
这即是说,自然意义上的“被统治者和被管理者”,却具备统治和管理的能力。在现代民主政治中,这种所谓例外已是普遍的正常现象。
在现代社会,被亚里士多德认为是自然意义上的“被统治者”和被管理者(ruled),如女性、体力劳动者和年轻人等所谓理性不充足者,经过后天环境和条件的培养,都能够获得卓越的统治能力,成为社会和政治领域的精英(ruler)。
因而,“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分工是可以人为地改变的,并非永恒不变。
总之,现代政治文明对亚里士多德“Natural Slavery”学说的扬弃,既坚持和发展了其理性主义内核,又确定了政治和社会地位对所有人“平等开放”、“机会均等”的原则,以理性能力这把唯一标尺公平地衡量所有人,是巨大的历史进步。
然而,在“如何理解平等”这个问题上,近代以来的政治理论与实践曾经历严重曲折,留下深刻教训。
庸俗的民主平等论者,机械地理解“平等”,崇信民粹,仅仅根据出身底层的身份,而罔论其理性管理能力,将一些人推上“管理者”,甚至是政党和国家的“治理者”(ruler)位置。
这些人可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其结果却酿成重大政治悲剧,对其本人、所管理团体、政党乃至整个国家都造成极大危害。经过了这些曲折,亚里士多德“理性能力决定政治地位”的千年教诲,对当代人类政治发展无疑极具警示意义。
(二)社会分工与人的异化: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与超越
现代政治理论发展到马克思主义,亚里士多德证成“统治”和“分工”之正当性的“Natural Slavery”学说又发生了根本性的颠覆。
首先,在政治统治理论领域,马克思主义不仅否认“统治地位由自然天性决定”,而且也否定“统治关系永恒存在”。
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国家和法律必将消亡,因此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将不存在统治关系,“共产主义革命则反对活动的旧有性质,消灭劳动,并消灭任何阶级的统治以及这些阶级本身”,取而代之的这样的联合体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所以统治关系并非是永恒的。
其次,与亚里士多德类似,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在论其所倡导的统治关系时,也将其视为是一种“分工”。
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就只是分工的不同,如刘少奇对劳动模范时传祥所言:“我当国家主席,你做掏粪工,我们工作性质一样,都是为人民服务,只是分工不同”。
然而,亚里士多德认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存在共同利益,是互利友好的关系;但马克思主义认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是一种对抗性斗争关系,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
马克思、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出于相互对抗的地位。”
“我们已经看到,至今的一切社会都是建立在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的对抗之上的。”
再次,相较于亚里士多德对分工的肯定态度,马克思主义则从根本上批判“劳动分工”,并将其视为导致“人之异化”的一个根源。

(马克思)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分工极端精细化,人被作为原子式个体束缚在具体分工的细微领域,“在精神上和肉体上被贬低为机器”,“人变成抽象的活动和胃”。
分工是“类活动的人的活动的这种异化的和外化的形式”。在社会分工体系中,形成了不同的社会生产部门,个人限定其中,由此人的劳动活动也形成了相应的分配体系。
这种劳动活动的分配体系,本质是不公平的分配,因为它是基于人的能力、技艺、智识等劳动要素的自然差异,并不是出于人的自由意志。
马克思这里“社会分工基于自然差异”的观点与亚里士多德高度类似,但二者态度却是截然相反。马克思看来,这种劳动活动的不公平分配必然导致劳动产品的不公平分配。
劳动产品分配的不公平愈演愈烈,就产生了私有制。在此意义上,分工和私有制的所指基本等同。而后,分工造成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深刻矛盾;产生城乡差别与对立。
马克思、恩格斯说:“城乡之间的对立是个人屈从于分工、屈从于他被迫从事的某种活动的鲜明反映,这种屈从把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城市动物,把另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乡村动物,并且每天都重新产生二者利益之间的对立。”
马克思批判分工的基本逻辑就是,人类社会自产生分工起,就产生了私有制,造成“物象化”现象,从而导致“人之异化”。
马克思控诉分工与“物象化”说,“社会活动的这种固定化,我们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着我们、不受我们控制、使我们的愿望不能实现并使我们的打算落空的物质力量,这是迄今为止历史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
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即成倍增长的生产力。因为共同活动本身不是自愿地而是自然形成的,所以这种社会力量在这些个人看来就不是他们自身的联合力量,而是某种异己的、在他们之外的强制力量。
关于这种力量的起源和发展趋向,他们一点也不了解;因而他们不能再驾驭这种力量,相反地,这种力量现在却经历着一系列独特的、不仅不依赖于人们的意志和行为反而支配着人们意志和行为的发展阶段。”
(三)人工智能的未来:“Natural Slavery”失去存在基础而消亡?
“Natural Slavery”或者人类社会的分工关系有没有可能消亡呢?虽然亚里士多德指出,“Natural Slavery”是自然的、永恒的,然而他同时也认为这个论断是存在前提条件的。
这个前提条件就是“自然奴隶”或“自然被统治者”的存在。如果“自然奴隶”不存在了,也即意味着“Natural Slavery”的消亡。
其实,人之理性差异并非完全是天生而绝对不可改变的。所谓理性不足的自然“奴隶”或自然“被统治者”的形成和存在,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历史客观条件限制的产物,不全是由自然本性所决定的。
他们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人格不独立不自主,“在本性上不属于自己而属于他人的人,就是自然的奴隶”(1254a14);二是理性存在不足仅能感知别人的理性(1254b20-21),缺乏理性审辨能力(deliberative faculty)(1260a11-12)。
所以,他们才需要别人的理性指导和管理。但其实他们并非毫无理性能力,至少具备理论推理能力和实践理性的潜能,只是缺乏现实的实践理性能力。
质言之,他们有理性种子,只是缺乏理性成长完善的土壤。这个土壤就是“广泛充分参与城邦政治生活”,城邦生活才是人发展和实现理性能力的最主要场域。
然而,城邦若得存续下去,必定需要有一部分人从事粗鄙(vulgar)劳动,来为城邦生活提供生存基础(1278a10-13);而参与城邦政治和提升德性必需充分的闲暇,也注定一部分人必须从事粗贱劳动来为另一部分人提供充足的闲暇。(1329a1-2)
所谓自然的“奴隶”,就是由这种自然客观条件和城邦客观需要所决定的“不得不”接受管理和指导从事粗鄙劳动的人。
总之,“Natural Slave”是为成就人之卓越德性而付出的必要牺牲,“Natural Slavery”则是为成就“人之最高最广的善”而不得已的“奴役”。
因此,如果消灭了那些束缚人之全面发展的局限,也就消灭了“Natural Slavery”。即使那些理性不足的人(Natural Slave),一旦具备发展自己理性潜能的土壤,亦会成为健全的理性自由人。
什么条件下,这样的情况才会发生呢?
亚里士多德明确指出:“倘使所有工具都能按照人的意志和命令而自动完成工作,倘使每一个梭子都能不假手于人力而自动地织布,每一琴拨都能自动地弹弦,倘使我们具备了这样的条件,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大匠师才不需要助手,masters也不再需要slaves。”(1253b38-40)
这是说,当生产工具完全实现自动化,人因此从繁重的生产劳动中完全解放出来时,这世间就再不需要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slaves,也不会存在这种slaves,那“Natural Slavery”亦即告消亡。
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管理和劳动分工关系,坚定主张予以“彻底消灭”。唯如此,人才能消灭“异化”和私有制,才能彻底获得解放和自由。因为完全自由的社会,是必然不存在固定的分工关系。
“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
不过与亚里士多德类似,马克思主义也认为,社会分工及其“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阶段,是社会进步的必要牺牲和代价,其消亡也需要生产技术高度发达到将人从工具操作者地位中解放出来作为基础条件。
人类社会正步入人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自动化技术方兴未艾,正在人类生产各个领域逐渐铺展,并日趋成熟。
军队作战越来越依赖无人机与其他无人作战平台,工业机器人在生产线普遍应用,自动驾驶技术、超级自动医学诊断软件开始推广,甚至机器人快递员已经投入使用,人工智能还能自动生成和创作文艺作品。
这些情景与亚里士多德“生产工具完全能按照人的意志和命令自动完成工作,而无需人力操作”的千年设想已经非常相似。
展望未来,社会资料的生产工作很有可能会被人工智能所完全取代,而人类则从粗鄙的体力劳动中彻底解放出来,所需要从事的生产活动,就是发号施令和监督管理。
这正是“Natural Slavery”下master和ruler的工作。这意味着“Natural Slaves”可能会被人工智能完全取代。“在未来,机器与人的关系很有可能会上演又一次主奴辩证法的循环。”
这样所有人都成了master和ruler,都拥有充分闲暇,自由参与政治治理活动,提升德性。所有人也就不再被局限于某个特殊领域,而是可以自由选择活动方式。
人工智能技术这一重大突破,很可能开创人类文明的一个全新时代。在那个时代,似乎束缚人之自由发展的“Natural Slavery”可能会走向消亡。
但细思也不尽然,即使人工智能取代了人去完成粗重劳动,但却并意味着人之理性差异的消失。只要人还存着理性差异,那么人对人的“统治”就仍具有正当性,仍具有存在的基础。
五、结语
对于古人观点的认识,需要回到古人语境下作“同情式理解”,而非以今人观念厉责古人。
深入《政治学》的文本语境,可知亚里士多德所念兹在兹的“奴隶制”是自然目的论层面上的“Natural Slavery”;以“奴隶制辩护者”之恶名强加亚里士多德并大加挞伐是重大误解。
作为“Natural Slavery”中心词的“统治”作现代理解,就是广泛存在于政治和社会领域的“管理”;所谓互利友好而正义的“Natural Slavery”可以理解为社会管理关系中“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分工关系。
这种人对人的“统治”何以正当?因为基于理性差异的“统治”,是理性的,而非强制和暴力的,所以它是正当的。中国的儒家也主张这种人之差异决定下的统治正当论,只是这种差异主要是“德性”差异。
如孟子所言:“天下有道,小德役(于)大德,小贤役(于)大贤;天下无道,小役大,弱役强。斯二者,天也。顺天者昌,逆天者亡。”
马克思主义异化论对“分工”的深刻批判启示我们,亚里士多德的“Natural Slavery”必当走向消亡。
当前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似乎为“Natural Slavery”走向消亡提供了积极条件,但仍远远不够。人对人的“统治”在可预计的将来,仍旧具有正当性。
贾永健,河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开封市龙亭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挂职)。本文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与全面深化改革关系研究”(14ZDC003),河南大学“省属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人才支持计划•第二批青年科研人才种子基金项目资助。
责任编辑:近复
【下一篇】【吴楠】桐城派优秀教育传统仍具当代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