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家星】“羽翼朱子而有功于圣门”——论《四书纂笺》述朱与订朱兼具的学术特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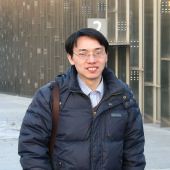 |
许家星作者简介:许家星,男,西元1978年生,江西奉新人,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博士。曾任南昌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
“羽翼朱子而有功于圣门”
——论《四书纂笺》述朱与订朱兼具的学术特色
作者:许家星(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暨哲学学院教授)
来源:《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03期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六月初七日丁未
耶稣2019年7月9日
摘要
詹道传《四书纂笺》采用笺证形式,对《四书集注》作出了正其音、明其义、考制度、辨名物、究本末、补未言、列异说、辨错谬诸方面的考察,被称为“羽翼朱子而有功于圣门”。该书还就《四书集注》注音、字义、引文、史实、袭用古注、未及修改、两说冲突、与朱子它书说冲突等多方面之误提出中肯批评,体现了批判修正朱子的一面,四库馆臣认为詹道传“于《集注》舛误之处讳而不言”的论断实属不当。此正反映出“羽翼与修正”兼备这一元代朱子四书诠释特色为人所忽略之处。作为元代四书考证类晚出著作,该书对前人成果裁择颇丰,堪称元代疏证《四书集注》的汇编之作,它展示了《四书集注》对汉唐学术的继承,显示了元代朱子学者“学有根底”的笃实学风。研究该书对掌握朱子《四书集注》、理解元代朱子学、认识朱子四书诠释的考证路向,皆有积极意义。
元代朱子学围绕朱子四书的诠释获得全面而深入的展开,这种诠释有侧重异同问答的“经疑”体、义理疏通的“发明”体、训诂考辨的“纂笺”体、概念阐发的“通旨”体等,堪称百花齐放,各有千秋。考辨《四书》的作法渊源于朱子本人。朱子早在《语孟集义序》中即提出“汉魏诸儒正音读,通训诂,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的看法[1](P3631),故《论语集义》《论语训蒙》特别注意音读训诂考辨之学,这一特色在《四书集注》中仍得到保留。不过较汉唐注疏更为简明而已。詹道传《四书纂笺》即秉承朱子思想,对《四书集注》作了一番全面的训诂考辨。《四书纂笺》对《四书集注》作出了正其音、明其义、考制度、辨名物、究本末、补未言、列异说、辨错谬诸方面的考察,被称为“羽翼朱子而有功于圣门”。值得注意的是,该书还就《集注》注音、字义、引文、史实、袭用古注、未及修改、两说冲突、与朱子它书说冲突等方面提出中肯批评,体现了批判修正朱子的一面,四库馆臣认为詹道传“于《集注》舛误之处讳而不言”的论断实属不当[2](P201)。此正反映出“羽翼与修正”兼备这一元代朱子四书诠释特色。作为元代考证类晚出著作,该书对前人成果裁择颇丰,堪称元代疏证《四书集注》的汇编之作,它在笺证《四书集注》的过程中,亦很自然地展示了《四书集注》深厚的汉学知识,体现了朱子四书对汉唐学术的继承,同时显示了元代朱子学者“学有根底”的笃实学风。
该书卷帙较繁,全录朱子《四书集注》,四库萃要本尚录有《大学或问》《中庸或问》,计28卷之多。著者詹道传生平未详,仅知其为元代江西临川乡间一读书人。詹道传对《四书纂笺》有明确定位,“藏于家塾以授其徒”,帮助初学朱子四书者扫除文本障碍。因《四书集成》《四书纂疏》诸书对朱子四书的义理问题已有详细研究,故该书不再费辞于此,以求各有分工也。“笺事及音读欲便初学耳。义理之训,则《集成》《纂疏》诸书详矣,是编奚庸赘辞。”[3](P175)该书“凡例”指出,本书仿朱子《论语集义》之例,对《四书集注》作一番追源溯流的正音读、通训诂、考制度、辨名物、究本末工作。鉴于朱子四书“务从简明,于制度器数之本末,经史子集之事实,钩玄提要,不复致详”的特色,该书采用笺证体,对朱子之说“各笺证据于下方”。浙江胡一中称该书“羽翼朱子而有功于圣门”[3](P174)。
该书在参考前人著作基础上形成,句读“用王文宪所定及温州点本参订为之”,字音“参用诸儒所定经文”。笺证于元人杜瑛《语孟旁通》、薛引年《四书引证》、金履祥《语孟集注考证》、许谦《读四书详说》、赵悳《四书笺义》诸书成果采用颇多,分类纂入,故称为纂笺。它书所论有得者,亦采入之。选材甚广而裁取颇严。“所笺如杜缑山《旁通》、薛秋潭《引证》、金仁山《考证》、许益之《详说》、赵铁峰《笺义》等书,颇加裁择,随类纂入。或他论有所补益者,间亦一二附焉。”[3](P175)故该书在很大程度上是元代疏证《四书集注》的汇编之作,代表了元代疏证《四书集注》的水准,这也提升了研究该书的必要性。以下分别从正其音、明其义、考制度、辨名物、究本末、补未言、列异说、辨错谬等方面展开论述。
一、正音
《四书集注》需要正音的字无外乎多音多义字、难读生僻字、通假通用字,它们皆影响对文本的理解。注音采用的方式是直音、反切、同音、标明声调(此类尤多)。以《大学章句序》注音为例,多音多义字如:适(音的)子;夫(音扶)百家;否(部鄙反)塞;充塞(先则反);间(如字)亦;圣经贤传(去声);鲜(上声)矣;少(去声)仪;使之治(平声);性分(去声),与(去声)有闻;为(去声)之。难读字如:颓(徒回反)败;余裔(余制反);泯(音闵)焉;辑(音集)之;沈痼(音固)。通假字如:蚤与早通;唯与惟通;帑与孥通;说音悦;翅通作啻。因“四声别义”为古书中非常重要的别义手段,故该书对区分四声特别重视,涉及的相关字有“王、好、语、劳、来”等。正音工作通常不标明所据音书,但有时列出所引书名者,常引的有《经典释文》《广韵》《礼部韵略》《玉篇》等。如“法语”,“陆音鱼,鱼据反”。此处“陆”当指陆德明《经典释文》。有时引《朱子语录》来指明读音,并以《广韵》印证之。如关于“果”字,“《语录》赵氏以果为侍。《广韵》从女从果者亦曰侍”。有时引《广韵》等来判定音义,如关于“殍”。《四书集注》“莩,饿死人也”。《四书纂笺》引《广韵》说:“《广韵》四纸殍注,音圯,草木枯落也;三十小殍注,饿死曰殍,亦作莩。十虞莩注,音敷,亦曰饿死。皆一义也,则莩死者,取草木枯落之义也。”凡例指出:“句读用王文宪所定及温州点本参订为之。”但笔者所见本未有断句,可知非原本。
二、训诂
《四书纂笺》采用《尔雅》《说文》《礼韵》等字书、韵书对《四书集注》展开了正文字、通训诂的考证。
其一,正字。《四书纂笺》指出有些文字存在差异,表现为正本与俗本之别。或指出俗本有误,如“邦无道能沈晦”之“沈”,俗作“沉”,“非”[3](P99)。或指出字的通用,不同的字在某个意义上可通用,如“陷于‘阱’通作‘穽’”[3](P250),“予通作与”“赈通作振”。或考察字形演变史,如“景即影字,古只作景,至晋葛洪始加氵”[3](P164)。或从音变的角度分析字体,如“勾吴,吴言勾者,夷之发声”[3](P124)。
其二,释义。一是近义词辨析。《四书纂笺》在“吾有知乎哉”章指出:“‘吾’‘我’二字,就已而言则曰吾,因人而言则曰我。如此章及‘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贱’、‘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此类皆不可不辨。”[3](P135)或引《说文》区别义近词,如“《说文》种曰稼,敛曰穑”[3](P135)。或引历史事实作为字义之例,如“偾,覆败也”,“左隐三年郑伯之车偾于济”[3](P13)。引《说文》对字展开综合解释,包括字形、造字法、字义、文献用例。如“博,《说文》作簙,局戏也。六著十二棊也。古乌曹作簙。《说文》弈从二十,言竦两手而执之,围棊谓之奕”。或引《尔雅》由某字之阐发进入一组词义的阐发,如“屋漏”,《四书纂笺》引《尔雅·释宫》作对应之解。“《尔雅·释宫》文云:室西北隅谓之屋漏,西南隅为奥,东北隅为宧;东南隅为窔宧,东北阳气始起,育养万物,为饮食之所。窔音杳,深也。”二是据字书判定歧说。如关于镒存在24两、20两不同之说,《四书纂笺》据字书判定20两说更确。“镒,二十两也。《丛说》《国语》二十四两为镒。孔注、赵岐皆云二十两。按:《字书》曰:镒益同数,登于十则满,又益倍之为镒,则二十两者为有义。”三是结合韵书解义。《四书集注》“纟昷,枲著也。”[4](P115)《四书纂笺》引《礼韵》解,认为贮、著可互通。“《礼韵》贮字亦作著,通作禇。”
三、考制度
考证《四书集注》所涉礼制,为《四书纂笺》中心任务之一。具体涉及面甚多,大略言之,或关乎古代官制。如司徒之职、典乐之官。引书交代其来源,“《书·舜典》,帝曰:‘契,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又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又如《四书集注》言:“士师,狱官。”[4](P183)《四书纂笺》详细交代此官制来源及其构成。“舜命臯陶汝作士,士之名始见于刑官,《周礼》秋官司寇之属有士师之职。刑官曰士,其长曰师。”再如《四书集注》云:“陈,国名。司败,官名,即司宼也。”《四书纂笺》指出此说源于《左传》,但在《程氏职书》中未见,且史料中亦未有据。“《左传注》陈楚名司寇为司败,《程氏职书》未见陈之司败,若楚之司败,见于文十年宣四年。”或关乎教育制度,如《章句》提及“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四书纂笺》引熊氏说对此详加解释,多达200余字。也有的关乎历法。如指出《孟子》七八月之说所用为周历,相当于夏历五六月。“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孟子》内并以周月言,与《春秋左传》同。”[3](P250)因礼制讨论最多,故引《周礼》《礼记》《仪礼》说甚多,如引《坊记》论述祭礼“七日戒三日齐”;婚礼“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别也”等。对礼的重点疑难处讨论颇详。如引孔颖达疏、金履祥注对伐冰制度详加解释。引吕氏说详细述期之丧的两种类型:正统之期与旁亲之期。引胡氏及傅寅说详论《四书集注》所言“饮、射、读法”。涉及古代重要的赋税、俸禄、军队、土地制度方面的,亦详加解释。如《四书集注》言:“大国地方百里,次国地方七十里,小国地方五十里。”《四书纂笺》首先指出“《集注》三说皆本《王制》”,并以一页半篇幅对此详加引证。
四、辨名物
名物是《四书纂笺》笺证的重点。此处仅举两例以窥一斑。对某些不好解释的名称问题,《四书纂笺》在《四书集注》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申发。如“小童”,《四书纂笺》引王柏之说,认为男贵女贱的价值观决定了对有地位女子的称呼,女子只有尊贵者方可比于男子。夫人之所以自称为“小童”,就是自比于小男子的意思。至于“孺人、夫人、后”皆是类比男子而得到的称号。“王文宪曰:天地之间男贵女贱,女子贵者方得比于男子,故夫人自称小童,比于小男子也。大夫之妻曰孺人,亦比小男子也。公侯之妻曰夫人,则比男子矣。至为天子之妻,始曰后,则在男之上而比于继体之君矣。”[3](P215)关于“五谷”,学者有不同看法,《四书纂笺》则引傅寅说。认为黍是穄,稷是鲜粟,稻是晚禾,梁是糯粟,豆是黒豆。傅氏还引王氏说指出,有人从五行的角度理解五谷,从三农的角度理解九谷,从种类众多的角度理解百谷。“傅杏溪《九谷考》云:黍,今穄也。稷,今鲜粟也。稻,今晚禾也。梁,今糯粟也。豆,今黑豆也。小豆,今菉豆也。麻,今油麻也。苽音孤,《周官太宰》释云:‘雕胡也’。王氏曰:‘有言五谷者,以五行所属而言;有言九谷者,以三农所生而言。有言百谷者,号其多而言。’”[3](P227)
五、究本末
考《四书集注》说之来源为詹道传此书的重点,把握《四书集注》说的出处本末,显然有助于对《四书集注》的了解。《四书纂笺》或指出《四书集注》字义训释的出处,如指出《四书集注》“暴虎徒搏,冯河徒渉”此8字为《尔雅》训释文。或涉及人物出场活动的背景。《四书集注》曰:“师尹,周太师尹氏也。”《四书纂笺》指出:“按《诗传》尹氏盖吉甫之后,周大夫。家父作此诗以讥王之用尹氏也。”[3](P14)或关于书名。如《四书集注》“《秦誓》,《周书》”。《四书纂笺》则引春秋说阐发《秦誓》之来由。“《春秋传》僖三十三年,秦穆公袭郑,晋襄公率师败诸殽,归而作《秦誓》。”[3](P17)有些是《四书集注》已提供线索,隐而未发,《四书纂笺》则对其本末详加引述。如《四书集注》云“《楚书》,《楚语》。言不宝金玉而宝善人。”《四书纂笺》则引《国语楚语》相关原文,佐证此说。
《四书集注》用语甚精,善于锤炼经典已有之文,用作注文。《四书纂笺》常采用“某字(句)出某某书、本某某说、见某某书、所引乃某某说”等点出其出处。如“齐之为言齐也,所以齐不齐而致其齐也”二句出《礼记·祭统》篇,“固其肌肤之会筋骸之束”见《礼运》。从《四书集注》所引之书见其引三礼为多,如“勤苦难成之患”“躐等陵节”皆出《学记》;“所谓起予则亦相长之义也”出《学记》“教学相长也”。“可谓能继其志矣”出《学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或交代《四书集注》两说之来源。如关于八佾,《四书集注》保存了两说:一是每佾人数不定,与佾数相同;二是每佾人数固定不变,皆为8人。詹道传引《左传》注疏为证,指出“人如佾数”说出自杜注,而服虔疏则主张每佾八人说。关于五霸说,《四书集注》分别采用赵氏与丁氏说,《四书纂笺》指出二说最早来源分别见于《国语》《春秋》,杜预注采用二说,故《集注》亦采用之。《四书纂笺》有时提出在面临两种解释时《集注》之取向。如关于公子赤还是公子恶的问题,《四书纂笺》引倪氏说指出《四书集注》取《公羊》说而放弃《左传》说:“左氏以为恶,公羊以为赤。《集注》曰子赤,本《公羊传》也。”[3](P213)
六、补未言
《四书纂笺》在阐述《四书集注》时,对《四书集注》略而未言的史实、背景多有补充、阐明。如《四书集注》言“自文武至此七百余年。”《四书纂笺》则具体列出文武至此的周代历王年限,分为春秋前、春秋、春秋后三个阶段,证实《四书集注》所言“至此700余年”说当属于周烈王、显王时。如《集注》言,“文子……又不数岁而复。”《四书纂笺》引杜预注指出文子“自出奔复反于齐”仅隔了二年。再如“司城贞子”,《四书集注》仅言“亦宋大夫之贤者也。”《四书纂笺》则进一步解释宋国司城实际为司空。“宋以武公讳,改司空为司城。”[3](P374)关于耦而耕,则引顾氏说论述牛耕制度之产生。“新定顾氏曰:古未用牛耕,《易》只言‘服牛乘马,引重致远’。最可考者,古人于蜡祭,迎猫迎虎,凡有功于田者,无不报祭,独不及牛。可见古未知以牛耕。自汉以来,方有卖刀买犊之说。”[3](P226)
《四书纂笺》也尽量地表达一些自身看法。或对《集注》反复重复的诠释内容表示关注,指出:“《集注》引程子慎独凡三章。仲弓问仁章云‘惟慎独便是守之之法’。子在川上章云‘其要只在慎独’,及此章为三。”[3](P233)或分析四书对五经的引用。如概括《孟子》对《诗》《书》的引用次数。“《孟子》援《书》凡二十九,援《诗》凡三十五。”[3](P261)讨论《大学》引用《尚书》的“活引”特点,指出《大学》“康诰曰克明德”及“天之明命”较原文皆少引数字,这种引经之法很灵活,而《章句》并未提及此点。“《康诰》本文云:‘克明德慎罚’,此只取上三字;下文引《太甲》‘顾諟天之明命’,亦去‘先王’字,皆引经之活法。”[3](P7)推测古注来源的存佚。引辅氏说指出赵氏不孝有三说,当源于今已不存的古传记。“辅氏曰:此必见于古传记,赵岐时其书尚存,故引之。”
考察《四书集注》说的根据。如《四书集注》引洪兴祖说,认为《论语·季氏》篇是《齐论》,《四书纂笺》则引胡氏说,指出洪氏说根据所在,认为其说并不是很充分。“胡氏曰:疑为齐论,以皆称‘孔子曰’,且三友三乐九思等条例与上下篇不同,然亦无他左验。”[3](P210)指出《四书集注》说的演变过程。如对《大学》开篇“子程子”加以说明,首先提出大、小程子之字号,进而指出《四书集注》对“程子”的处理有一个从分到合的变化,即最初以大程子、小程子来分别二说,其次以伯子、叔子区别之;最后则认为二者学同,不需要加以区别,故统称程子。詹道传还指出“子程子”之说乃仿效《公羊传》“子沈子”之例,“子”好比“先生”,是对有德之人的称呼。“《集注》初以大程子、小程子为别,次称伯子叔子,最后以其学同,通称程子云。子者,有德之称,犹今称先生。然子程子仿公羊传子沈子之例也。”[3](P6)为此,本书不区分二程说,而金履祥《论孟集注考证》则对二程详加区别。
七、列异说
《四书纂笺》还常提供与《四书集注》不同之说,为读者理解原文提供多种参照,亦表明《四书纂笺》对《四书集注》采取理性分析的态度。
其一,注音方面,指出《四书集注》注音与韵书的差别。如:“胫,按《韵书》形定反。《四书集注》云‘其定反’,音小异。”《四书纂笺》还对《四书集注》未注音者提出质疑。如指出“屏”有上、去二声,据音义一致原则,“屏四恶”之屏当读去声,旧读上声可疑。“按:《韵书》屏字上声者注云:‘蔽也。’去声者注云:‘除也’。屏四恶之屏,当去声读而旧音丙可疑。”又如“鹤鹤”的读音,《四书集注》认为“鹤《诗》作蒿,户角反。”《四书纂笺》则引许谦《丛说》提供另一种读音,“《丛说》禽名之鹤音涸,在铎韵。鹤鹤之鹤音学,在觉韵”[3](P245)。当然,《四书纂笺》对《四书集注》的叶韵说并无怀疑。
其二,人物方面。如关于公冶长,《四书集注》仅言“孔子弟子”。《四书纂笺》引《弟子传》说为齐人,既而又引《家语》说为鲁人,两说并存。“《弟子传》名苌,字子长,齐人。《家语》鲁人。”[3](P90)又如漆雕开,《四书集注》言“字子若。”《四书纂笺》指出《家语》《史记》在漆雕开的字与国上皆不同。“《家语》字子若,蔡人。《史记》云:字子开,鲁人。”[3](P92)关于公子纠与管仲孰兄孰弟。《四书纂笺》指出,《荀子·仲尼篇》言“齐桓公杀兄而争国”,此说为司马迁、杜元凯、韦昭所采用。独程子从义理上据春秋笔法以子纠为弟[3](P190)。关于“达巷党人”,《四书集注》认为,“其人姓名不传”。《四书纂笺》则提出:“《董仲舒传》孟康注云:项槖。”[3](P133)
其三,制度方面。制度方面颇多异说,如车乘制度,马融主张800家出车一乘,包咸则主张80家,二者差别甚大。朱子倾向于马融说,马融所据为《周礼》。《四书纂笺》指出包咸所据为《孟子》《王制》,并指出时人傅寅倾向包氏说。《四书纂笺》并未明确表明自身态度,仅客观列出二说,其实已显示其不专主《四书集注》的立场。“马说八百家出车一乘。包氏说八十家出车一乘。一乘甲士三人,歩卒七十二人,牛马兵甲刍粮具焉,恐非八十家所能给也。马融千乘之说,依《周礼》……包云:……盖依《王制》《孟子》大国地方百里之说,而傅杏溪《百考》是之。”[3](P60)关于乡党邻里,《周礼·地官·遂人》与《大司徒》看法有异。詹道传认为,二者所指对象不同,分别指郊外之制与郊内之制,并以郑氏说为据。“愚按:大司徒掌建邦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此郊内之制也;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图经田野,造县鄙,形体之法,此郊外之制也。郑司农云:‘田野之居,其比伍之名,与国中异制’。故亦异其名。”
其四,其他方面。其他方面异说也不少,如指出《孟子·离娄》下“子濯孺子章”存在异说,《四书纂笺》所引“古疏”说与《孟子》之描述不同。“孟子之言与此不同,是二说必有取一焉。”[3](P356)《中庸》篇章的异说。《四书纂笺》指出,《史记》《孔丛子》皆言子思困于宋作《中庸》,《孔丛子》且言作四十九篇。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载《子思子》一卷,提出“所谓四十九篇,岂非混《子思子》与《中庸》为一书与?”[3](P452)历法的古今差异。《四书集注》提出夏代历法斗柄建寅之说,《四书纂笺》引金氏说指出《四书集注》所言乃古代历法,进而引沈括说指出今历与古历有别,不主建寅说。“金氏曰:‘此古历也’。沈括云:‘今正月斗柄指丑矣,盖岁差也。但以冬为亥子丑,春为寅夘辰,不必因斗建也。’”[3](P203)
八、辨错谬
四库馆臣在明陈士元《论语类考》的提要中指出:“张氏、詹氏皆于《集注》舛误之处,讳而不言。”此说不确,詹道传虽笃信《四书集注》,于其误处却不乏批评。上文所列各种异说,已多少表明《四书纂笺》对《四书集注》的不满,不过未直接批评而已,但《四书纂笺》还是直接对《四书集注》展开了多方面的批评辨正。
其一,字音之误。《四书集注》曰:“子贱,姓宓。”詹道传据韵书指出,此“宓”字读“密”不确。作为人姓当作虙,音伏,虙、伏相通。“考之《韵书》,此字音密。子贱之姓,当作虙,音伏。《家语》宓音密,《史记》宓与伏通,济南伏生即其后。”《四书集注》对“齕”的注音有误。“齕下没反,《四书集注》音核,乃下革反。恐误。”[3](P251)对《集注》“盻”的注音提出质疑,“盻”,《四书集注》据《经典释文》五礼反,认为普苋反不对。《四书纂笺》则引《纂疏》说,主张《礼部韵略》的胡计反、吾计反,认为《释文》五礼反误。再如“懥”,《四书集注》“勑值反。”《四书纂笺》提出《广韵》《玉篇》说与之不同。“懥,《广韵》《玉篇》并陟利反。”
其二,字义之误。詹道传引邵氏批评《章句》“盘,沐浴之盘”说,邵氏认为就事理及经典记录言,沐浴非日日之事,此盘当是盥洗之盘而非沐浴之盘也。“新定邵氏曰:日日盥頮,人所同也。日日沐浴,恐未必然。《内则》篇记子事父母,不过五日燂汤请浴,三日具沐而已。斯铭也,其殆刻之盥頮之盘欤!”[3](P8)引金氏说指出《四书集注》“五十字”当为“吾字。”“金氏曰:五十字当是吾字之误。”[3](P118)又如“贼者,切害之意。金氏曰:当作窃。”
其三,袭古注之误。《四书纂笺》引郑玄《考工记》注指出,“纟取”并非《四书集注》所言的绛色,而是黑色;再引饶鲁说指出《四书集注》之误在于沿用《檀弓》古注说。“郑注:染纟熏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黒,则为纟取,如爵颜色也。再染以黒,则为缁矣。饶氏曰:《檀弓》练衣纟原纟录,古注误以纟原为纟取。”[3](P145)批评《四书集注》对《孟子》“九河”的理解沿袭郭璞说而误,郭璞认为“九河”包括“简、洁”二河,《四书纂笺》据蔡沈《书集传》指出,简洁为一河而非两河,《孟子》实仅列八河,此外一河则为河之径流。“蔡氏《书传》云:《尔雅》九河……其一则河之经流也。先儒不知河之经流,遂分简洁为二。然则朱子亦因郭璞注而误也。”[3](P313)指出《四书集注》沿袭古注,把“策”释为“简”,过于简单,不够准确。“《丛说》:《春秋传序》‘大事书于策’,小事简牍而已。《正义》云:‘简容一行字,数行者书于方,方所不容书于策。’……今但训策为简,从古注也。”[3](P467)
其四,未及修改之误。《四书纂笺》引金氏说,认为《四书集注》“史迁所谓农家者流也”有误,盖太史公并无农家说,农家说始于《汉书·艺文志》,并委婉指出《四书集注》之误是未及修改之故。“金氏曰:太史公《六家指要》无农家,至班固《艺文志》分九流,始有农家者流。此《集注》未及改。”[3](P311)
其五,引文之误。《四书集注》在颜渊死章引胡氏说,认为君子用财视义之可否而非吾之有无,《四书纂笺》引金氏说反驳之,认为胡氏说用意虽善,但会造成寡恩之弊。“金氏曰:考其时则颜渊之死且葬,适当厄陈蔡之后,自反陈之余,此正夫子之穷也。夫丧事称家之有无,夫子既以此处其子,安得不以此处颜渊乎!夫子遇旧馆人之丧,尝脱骖以致赙矣,而不能为颜子之椁。彼一时此一时,贫富不同也。胡氏之说虽善,然不考于事而其流少恩矣。”[3](P154)《四书纂笺》指出,《四书集注》所引《家语》夫子讥伯子有误,此说见于刘向《说苑》,且“欲同人道于牛马”并非夫子之说,乃刘向评论之语。“刘向《说苑·修文》篇,孔子见子桑伯子……子桑伯子易野,欲同人道于牛马,故仲弓曰太简。按:《家语》无其文,《集注》误也,而‘欲同人道于牛马’一句,亦非夫子所讥。”[3](P101)引文理解之误。《四书集注》认为,《大学》“瞻彼淇澳”章“如切如磋”等以下文字,是“引《诗》而释之”。詹道传提出质疑,认为此非《诗传》所释,而是《尔雅》所释,其别仅在于少一“者”字,“疑非《诗传》所释,《尔雅·训释》篇已载其文而无‘者’字。”[3](P9)
其六,史实有误。《四书集注》云魏“亡其七邑。”《四书纂笺》则据《史记》指出“七邑”当为“八邑”之误。“按:《史记》魏襄王十二年,楚败我襄陵,不言邑数。楚怀王六年得邑八。《四书集注》作七邑者,恐误。”引《春秋世谱》说批评《四书集注》“子产公孙侨”说。“按《史记索隐》子产,郑成公少子也。按《春秋世谱》乃公子发字子国之子,以其出于公族,故氏公孙。”[3](P95)《四书集注》据《春秋传》认为武子在文公有道之时无所表现,可证武子知之可及处。《四书纂笺》引杜注指出,武子之父死于成公二年,此后武子方为大夫,由此可推武子在文公时并未出仕,故《四书集注》之说证据不足。“以此考之,宁庄子当死于成公二年左右,而后子俞为大夫,则武子未尝事文公。《集注》云然,未知何据。”[3](P98)《语录》说不合史实。《孟子集注》金声玉振章,《四书集注》云“倪宽云‘惟天子建中和之极,兼总条贯,金声而玉振之’,亦此意也。”《语录》指出,倪宽之时尚无《孟子》书,推定金声玉振之说乃古语。《四书纂笺》认为《语录》说不确。盖《孟子》书已经见于文帝时也。“然《孟子》之书出于文帝,而董仲舒亦尝辩孟子性善之说,况倪宽又在后。乃未详《语录》之意。”[3](P377)
其七,两说冲突之误。如《孟子集注·滕文公上》“惟尧则之”,注:“则,法也。”《四书纂笺》指出,《论语集注》则将“则”注释为“准”,二说不同,当以“准”说为是。“《论语》注:‘则,犹准也。’当以为正。”[3](P314)再如“仞”,《论语集注》是七尺,《孟子集注》是8尺。《四书纂笺》考之《周礼》,认为当是《孟子集注》的8尺。“八尺曰仞。《四书集注》于夫子之墙数仞云:‘七尺曰仞。’今按《周书》‘为山九仞’。孔安国云:‘八尺曰仞。’郑玄云:‘七尺曰仞。’《集注》两存其说欤?……愚证之《周礼》……‘寻,八尺也。仞亦八尺也。’以此观之,则孔说为是。”[3](P428)
其八,《四书集注》与朱子他书相冲突而误。如关于“不舍昼夜”之“舍”的读音,《四书集注》是上声。但朱子晚年著作《楚辞辨证》则批评“舍”读上声。此两种看法相互冲突,詹道传认为当以晚年说为准。“不舍昼夜,‘舍’上声。《楚辞辨证》骚经‘忍而不能舍’也。洪氏注引颜师古曰:‘舍,止息也。屋舍、次舍皆此义。《论语》不舍昼夜,谓晓夕不息耳。今人或音舍者非是。’按:《辨证》文公著于庆元己未三月,明年庚申四月公易箦矣。《四书集注》舍上声者旧音,读如赦者,定说也。”[3](P138)又,詹道传还据《朱子格言》对《孟子》“浩然之气”章的“非义袭而取”作出与《四书集注》不同的新解。“按《朱子格言》云:‘非义’当一读,盖非义则是袭而取之者。若三字连读则不成文理。今按《集注》与此不合,谩记于此。”[3](P279)关于谅阴之说,《四书集注》言“天子居丧之名未详其义”。但《四书纂笺》引蔡模说,指出朱子晚年主张谅阴是“居丧于梁闇”之义。“蔡氏模曰:《丧服四制》谅闇三年。郑注云:谅古作梁楣,谓之梁闇,……《书》云:‘王宅忧谅阴’,言居丧于梁闇也。模按:谅阴之义,先人得于先师晩年面命者如此。”[3](P197)
其九,《四书纂笺》有时以罗列诸说的方式来质疑《四书集注》说。如《四书集注》言“鲁地七百里”。《四书纂笺》先后引《王制》《孟子》《周礼》说为证,表明公侯之地皆不足700里,唯有《明堂位》言700里。《四书纂笺》对此不同看法的态度是“当详之”。“《王制》《孟子》为三等之地,公侯皆方百里,……《明堂位》云‘周公致政于成王,成王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当详之。”[3](P210)
其十,《孟子》《史记》之误。如提出《孟子》“中古棺七寸”所说未见得可靠。《四书纂笺》先引《礼记》棺4寸椁5寸说,再引丧礼棺有8寸、6寸两种不同尺度说,证明古籍并无《孟子》所谓“中古棺7寸”,又引古注说天子与平民棺材厚度一样,反驳《孟子》之说。“《记·檀弓》‘夫子制于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而《丧大记》云:‘君之棺八寸、上大夫棺八寸、下大夫棺六寸、士棺六寸’。注云:‘皆周制,舍此未见有七寸之文’。此章旧注云:‘天子至庶人厚薄皆然。’乃未详。”[3](P295)指出《史记》的孔子弟子传有所失载,陈亢在《孔子家语》中已记为弟子,《史记》却失之,“《家语》亢在孔子弟子中,《史记七十二子传》却无之。”[3](P62)与之类似失载的还有林放。“林放,鲁人,《史记弟子传》不载,《礼殿图》有之。”[3](P74)《四书纂笺》还引金氏说批评《史记》所记伯夷叔齐名字关系不对,乃出于纬书附会之名。“《史记列传索隐》:‘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齐名智,字公达。夷齐其谥也。’金氏曰:《史记》载夷齐名若字,出《春秋少阳篇》,古无此名字之例,乃纬书附会耳。”[3](P99)
其十一,引时人说以批评古书之误。如引曾以德说批评《礼记》王霸不分。“曾以德曰:《春秋传》昭三年郑子大叔曰:‘文襄之霸也,令诸侯三岁聘,五岁朝,则此乃霸者令诸侯以事已尔’。《记》以为诸侯之事天子,则误矣。”[3](P471)批评许谦《读四书丛说》“沽”音之误,许谦提出沽有平声、去声两种,分别指向买、卖。《四书纂笺》认为此与《论语》不合。“《丛说》:‘沽去声训卖,若平声则训买。’于此义不相当。”[3](P138)辨通行本断句之误。引金氏说指出“羿善射奡荡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中“然”有两种断句法,金氏认为“然”应当作为下句开头而非上句之结尾。“金氏曰:俗连‘然’字句者非。若由也不得其死然,于未死之前,期词也;则已死之后,断词也。‘然’字唤起下文,便见尚徳之意。”[3](P185)
九、结语
综上所述,《四书纂笺》具有两个鲜明特点:羽翼朱子而不乏批评,汇聚众说而断以己意。该书所有的考证几乎皆是站在前人肩膀上,尤以元人著作为主,体现了集元代《四书集注》考证之大成的特点。虽詹道传极少自出己意,然诸说之选取裁定,则体现了著者的学识与眼力。该书虽以羽翼朱子、疏证朱子为目的,但并未遵守“疏不破注”的原则,而是对《四书集注》作出了多方面的批评,而态度则表现得很委婉。这表明四库馆臣论其讳言《四书集注》舛误的论断实属偏见无稽之谈。以清人汉学的眼光看来,该书考证仍有不够精密之处。尽管如此,该书已充分显示了著者深厚广博的知识,亦充分展示了朱子四书之学对汉唐学术实有着深刻之继承与发展,同时为清代汉学的产生亦埋下了伏笔。故此,《四书纂笺》对于准确掌握《四书集注》、深入理解元代朱子学、切实把握朱子四书诠释的考证路向,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朱熹.朱文公文集[M]朱杰人,等.朱子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2]永瑢;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9.
[3]詹道传.四书纂笺[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05.
[4]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责任编辑:近复
【上一篇】【宋希仁】中国传统伦理学的特点
【下一篇】【赵文宇】王阳明对佛学的批判
作者文集更多
- 【许家星】饶双峰文献的钩沉、整理与新见 10-13
- 【许家星】吴仲迂《语类次》思想及其诠释 12-13
- 【许家星】张栻的道统思想 04-27
- 【许家星】道之辩——以船山对双峰《学》··· 02-16
- 【许家星】并非“塞责抄誊”:《四书大全··· 12-08
- 【许家星】即气论以论仁学——李存山先生··· 10-07
- 【许家星】精一之传——王阳明道统思想探幽 05-28
- 许家星 著《经学与实理:朱子四书学研··· 06-26
- 【许家星】朱子的道统世界 10-23
- 【许家星】“羽翼朱子而有功于圣门”——论··· 07-09
微信公众号
儒家网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

微信公众号
儒家网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