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仲人】《父母等恩》:丧服礼制史里的宗法与孝道
《父母等恩》:丧服礼制史里的宗法与孝道
作者:孟仲人
来源:澎湃新闻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庚子正月廿五日辛卯
耶稣2020年2月18日
故事的主人公是明太祖朱元璋。
洪武七年(1374),孙贵妃去世。贵妃生前没有产下皇子,因此明太祖命贵妃长期抚养的周王朱橚,以生母的丧服(“慈母服”)来行三年斩衰之礼。这一下子引起了礼部官员的反对,因为按照传统《仪礼》的规定,只有父亲过世之后,才能服三年斩衰。母亲去世则需根据父亲是否在世,分为父亲身故,为母亲服齐衰三年(较斩衰次一等);父亲在世,为母亲服齐衰杖期,即服丧一年。既然朱橚的皇帝父亲还在世,那么服三年斩衰,无论从服制还是从年限都不合古礼。
众所周知,朱元璋虽然出身贫寒,但自从跃登宝位之后,潜心苦读儒家经典。朱元璋读书或许可说是颇具“批判精神”,他常常不赞同儒家圣贤所言,比如他对孟子“民贵君轻”的说法就不以为然。同样的,朱元璋对礼部官员执着于古礼,感到非常不可理解。他认为父、母对于子女的恩情是同样,而丧礼中却偏要将同样的恩情分出个轻重,甚至父亲若健在,遇母亲逝世则不过守丧一年,实在太违背人情。所以朱元璋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断,他要改变丧服制度,让同样的恩情在丧服制度中予以同样的表现,人子为父母、庶子为其母,都服斩衰三年。而且,朱元璋还制作了《孝慈录》一书,作为明代丧服制度的定本,甚至将其列入《大明律》中,成为影响深远的定制。
萧琪在《父母等恩:<孝慈录>与明代母服的理念及其实践》(东方出版中心,2019)中,便从这个故事展开来她对“母服”的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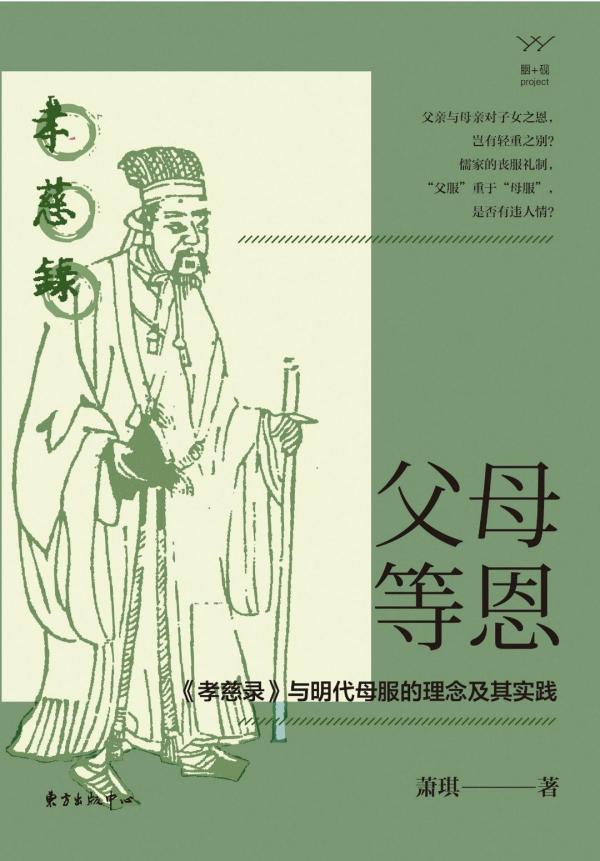
《父母等恩:〈孝慈录〉与明代母服的理念及其实践》,萧琪著,东方出版中心2019年8月出版,240页,52.00元
从儒家的经典来说,父母等恩不等服虽然有违背人情的一面,但这样的设置却对维系父系宗法制度,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虽然“亲亲”是制礼时重要的伦理原则,但正所谓“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国无二君、家无二尊”,虽然父母与子女的亲情相同,但是却要区分开来,要强调“父母有别”,因此“尊尊”自然凌驾于“亲亲”之上,父服要远比母服来得隆重,而形成“礼胜于情”的制度。
这种对于母亲之恩的忽略,从女性主义的视角来说,也代表着传统宗法社会中对女性地位的长期忽略。所以以常理来看,当女性统治者出现之时,自然会立刻着手改变这种忽略母恩、违背人情的丧服制度,即所谓“缘情制礼”。果然,武则天就主张,为了报答母亲生养劳瘁之恩,不论父亲在世与否,人子为母亲都须服齐衰三年之丧。她说“禽兽之情,犹知其母”,将母子之情视作为禽兽亦有之“常情”,因此人既然有情,就应当在礼法中加以重视和维护,而不是简单地忽略与排斥。因此,过往的研究者大多据此认为武则天的女性身份、女主干政的政治行为,是理解唐代改制的重要突破口。
可实际上需要注意的是,武则天虽然主张孝子对母亲恩情的回报,与父亲是否在世无关,但始终没有将母服提升至与父服相同的地位。应当说,武则天时期的母服改制始终未能突破“家无二尊”的制礼原则。所以纵使当时有儒生提出,圣人制礼是要“别禽兽、异夷狄”,却很难否认母亲恩情需要回报,也无法阻止武则天的母服改制。
真正的突破正是在明太祖朱元璋的母服改制。将父母等恩与父母等服直接对应起来,则完全突破了礼制中的“家无二尊”。唐、明两次母服改制的对比,正如萧琪在书中所说,“认为女性统治者为母的经验,是母服制度发生变革的关键,但此一说法若放在明代的丧服改革中,则显然失去效用。”不过在萧琪来看,明太祖的改制更多地是其个人对于孝道、治国、制礼观念的结果,也就是说直到此时,以孝、亲亲、尊尊为基础的丧服制度实际上还是一般人所接受的知识、观念,也形塑着他们的行为。
但是,自从明太祖改制以后,明代社会也出现了一系列的改变。萧琪在书中提到,明代中前期的士人不少都相当拥护太祖之制,认为《孝慈录》中恰当地展现了母子之情,所谓“礼以义起而缘乎人情”,所以纵使现实的制度违背了儒家的经典,在他们来看却是对圣贤道理的进一步发展。这样也就牵出一个问题,“孝”应当如何被表达?
“孝”是中国文化中最为重要的关键词之一,以政治来说,从两汉、魏晋直至明清,“孝治天下”的倡言屡见不鲜;以社会而言,夫人孺子耳熟能详的故事中,“二十四孝”不可或缺。除了比较短的几段时间里,“孝”曾被质疑其存在是否必然,此外的大多数时候“孝”都是传统中国巩固家庭、形塑社会、维系统治的价值基石之一。因此,“孝”不仅是个人的品质与行为,在重视家庭、家族、宗法的古代,更是代际之间最重要的连接点,并且与礼、法共同构成一定的社会轨范。所以,以个人的行为来说,“孝感天地”或有种种不合常理的行为举动,但礼仪制度中的孝却须遵循一定的限度。
《孝慈录》和“父母同斩”的丧服制度弥补了礼制中对母亲之恩的忽视,将孝子之情得以充分地展现。可是,由逻辑上来说,这种情感的表达又冲击了宗法制度的根基。所以,随着明朝衰亡,明末清初士人反思明朝政治得失之风兴起,《孝慈录》和“父母同斩”的丧服制度受到了顾炎武等人的群起挞伐。这些士人认为宗法制度从根基上动荡,是整个社会走向衰败、乃至明清鼎革、夷夏之变的原因。
可是,对于情感的认识却早已深入人心。萧琪在书中也关注到,对《孝慈录》的挞伐似乎局限于古礼的考据,而没有影响社会生活中对“今律”的遵循。所以到了清代,“父母同斩”的丧服制度广泛地渗入万民生活之中。换而言之,在学术与生活交错的不同维度,存在有对父母丧服的不同理解和对“父母等恩”的共同信奉,这是相当重要也饶富趣味的发现。
需要注意的是,从明初到清代,虽然对现实的礼制是否要符合儒家的经典,士人往往有不同的意见,但对“母亲之恩”却万人同亲。这其实也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人伦情感虽百代之前亦有,可对情感的社会认识是否历百代而不变呢?正如明初母服改制,是与明太祖个人的思想、观念紧密相关,但由此对一般人“母亲之恩”的认识产生了怎样的改变?社会认识的转型又对一般人的知识、思想与观念产生了怎样的联动?这些问题在萧琪笔下的多个案例中都隐隐有所体现,也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或许应当说,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萧琪的这本书不仅仅是一本历史学的研究,实际上也打开了今日与往时的情感沟通。虽然过往的制度大多数已经崩溃,但是其中所透露出的母子之情、家庭关系,也是今天的读者不得不面临的难题。
责任编辑:近复
【上一篇】【张昭炜】扬雄“太玄”释义
【下一篇】【傅锡洪】王阳明“四句教”解义及辩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