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玉婷】朱子《中庸章句》的诠释特点与道统意识
朱子《中庸章句》的诠释特点与道统意识
——以郑玄《中庸注》为参照
作者:杨玉婷(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讲师,复旦大学哲学博士)
来源:《原道》第39辑,陈明、朱汉民主编,湖南大学出版社2020年11月出版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1年版)
内容摘要:“道统”说在朱子理论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对它的理解关系到对朱子哲学的整体定位。朱子“道统”说的成熟形态出现在《中庸章句序》,理解《中庸章句》本身有助于我们把握朱子的道统意识。
《中庸章句序》指出子思作《中庸》的原因在忧“道学”之不传,提出《中庸》的内容与“道统”的内容一一对应,“道统”与“道学”是统一而非分裂。
相对于郑玄《中庸注》的政治化诠释,朱子《中庸章句》的整体特点是立足于道德心性层面,关注的不是“礼”的制度和圣王政教,而是个人天性的发扬,将政治上的差等转化为道德上的平等,将对国家政治制度的考量转化为对人道德建设的关注。
道德建设是朱子《中庸章句》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此语境中的道统说也当是以内圣(道德)为规模。对朱子“道统”说的政治性解读是本末倒置,过度诠释。
关键词:中庸;道统;朱子;郑玄;道德心性;
儒家的“道统”,简言之,就是儒家传道的系统。儒家道统意识可上溯自先秦的孔孟,唐代韩愈在《原道》中明确提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的传道系统,而儒学中最具影响力的“道统”是朱子所提出,道统论的建构也是在朱子手里完成。
朱子在《中庸章句序》(以下简称《序》)中开篇即曰:“《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紧接着,朱子从道统人物、传承内容、核心要旨等方面展开了详尽论述。
近来学界对朱子的道统意识大体有三种定位:一是认为“道统”观念起于新儒学内部哲学发展的需要。陈荣捷指出:“道统之绪,在基本上乃为哲学性之统系而非历史性或经籍上之系列”。
二是认为朱子的“道统”是出于政治用意,以约束骄君和提高士大士政治地位为目的。“‘道统’与‘道学’同具深刻的政治涵义,是可以断定的。以‘道统’言,朱熹之所以全力建构一个‘内圣外王’合一的上古三代之‘统’,正是为后世儒家(包括他自己在内)批判君权提供精神的凭借。”
三是认为朱子提出“道统”是为了在心性学上应对佛老,建立起儒家的终极托付。刘述先说:“儒者由超越而回归于内在,完成了整个的圆周,故必辟二氏,以其弥近理而大乱真。……宋儒要建立道统就不能不接触到儒者与二氏的分疏的问题。”
三者切入视角不同,前者立足于理学的哲学根基,而后两者则存在政治与道德两个维度的对立。“道统”说在朱子的理论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对其不同理解关系到对朱子哲学的整体定位,尤其是后两种理解之间的冲突关系到是以外王政治还是以心性道德为朱子所关怀的第一序的问题。
朱子“道统”说的成熟形态出现在《序》中,《序》是《中庸章句》的一部分,那么《中庸章句》的整体诠释范式也就是《序》中“道统”的论域背景。理解《中庸章句》的范式能有助于我们把握朱子的道统意识。
本文通过对比朱子与郑玄二人对《中庸》的诠释,以凸显朱子《中庸章句》的整体特点,厘清其中政治与道德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分析朱子“道统”说的内容与定位。
一、“道统”统一于道、传承于心
《序》中首先表明子思作《中庸》的原因在于忧“道学”之不传。“《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朱子详细论述了圣学之功与失传之危险:
“吾夫子,则虽不得其位,而所以继往圣、开来学,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然当是时,见而知之者,惟颜氏、曾氏之传得其宗。及曾氏之再传,而复得夫子之孙子思,则去圣远而异端起矣。”
故子思“作为此书,以诏后之学者”。儒家的“异端”一直存在,很大程度上儒家学说是在辟异端的过程中而不断确立自身的理论形态。到朱子时,要应对的“异端”主要是当时极为盛行的佛教。

(唐宪宗迎佛骨)
“道学”之后朱子点明“自上古圣神继天立天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道统”的内容“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
尧以“允执厥中”传舜,此乃《论语·尧曰》中的“允执其中”,舜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传禹,此来源于《尚书·大禹谟》。
朱子解释“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微一”的意思:“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而以为有人心、道心之异者,则以其或生于形气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而所以为知觉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难见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虽上智不能无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虽下愚不能无道心。”
“人心”和“道心”的区别在于人所禀受的形气偏私不同,导致每个人的心显现不同。人心危险、懈怠,道心也就微妙而难以显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是凡人之心通常的状态,而“精”“一”则是使心达到“允执厥中”的工夫。“允执厥中”是道心主宰人心,天理胜过人欲,合于“中”道。尧、舜、禹相传,以及之后“圣圣相承”,也“不过如此”。
朱子认为《中庸》所载“道学”与先圣代代相承的“道统”是一致的:“其曰‘天命率性’,则道心之谓也;其曰‘择善固执’,则精一之谓也;其曰‘君子时中’,则执中之谓也”。
子思所作《中庸》,虽“世之相后,千有余年,而其言之不异,如合符节。”在朱子看来《中庸》完全能体现出前圣相传之道。可见朱子不是在区分“道统”与“道学”,反倒是意在将两者统一起来,以表明儒家的“道”在圣贤间相传,不会断绝。
此外,朱子对于“道”的载体和传承方法也做了说明。他认为尧舜禹相授受,即“天下之大圣行天下之大事”是“天下之理”,这从“事”到“理”进行了抽象。圣人之事和圣人之法本不相同,是多元的、历史性的,朱子过滤掉其中的差别,建立历代圣王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就是圣王之“道”。
前文已说明,“道”的内容是“允执厥中”,实现的方法是惟精惟一、道心常主、人心听命,都是落实在“心”上。朱子又说子思是“推本尧舜以来相传之意”,到了程子能“因其语而得其心”。
可见,“道”最关键的传承在于“心”。所以朱子说《中庸》“乃孔门传授心法”。后学通过经书所求的就不是“圣人之法”,而是“圣人之心”。这样,朱子的“心”主要指向成圣的道德修养。
道德与政治都是儒家所关心的话题,两者关系密切。但两者的区别也很明显:道德是个人修身之事,是无限性的,偏重于“内圣”一面,而政治是公众的事,是经验性的,偏重于“外王”一面。儒家整体而言采取的都是“内圣”与“外王”统一、德性与政治统一的立场,但是内部又有差别。先秦孟子与荀子就不同。
牟宗三先生曾指出:“孔子与孟子俱由内转,而荀子则自外转。孔孟俱由仁义出,而荀子则由礼法(文)入。”又说:“孟子敦诗书而道性善,正是向深处去,向高处提。荀子隆礼义而杀诗书,正是向广处走,向外面推。一在内圣,一在外王。”
所谓孟子偏在内圣,“由仁义出”,内圣是根基,对于道德的关怀是其哲学的第一序意义;所谓荀子偏在外王,“由礼法入”,荀子要人修身提高美德,目的在于建立一个平治的国家,对政治的关怀是其哲学第一序意义。
就“礼”而言,荀子所认为礼的首出意义是政治而非道德,所以强调“礼之所以正国也”(《荀子·王霸》)。反之,孟子认为礼的首出意义是道德而非政治,所以强调“辞让之心,礼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孟子·离娄下》)
相对于先秦内圣与外王的横向区分,宋代更关注于“道”的体与用的纵向差别。但“体”落实在“用”的哪一方面又有不同,朱子看来“道”的载体是“圣人之心”而不是“圣人之法”,这就对“内圣”与“外王”有不同的侧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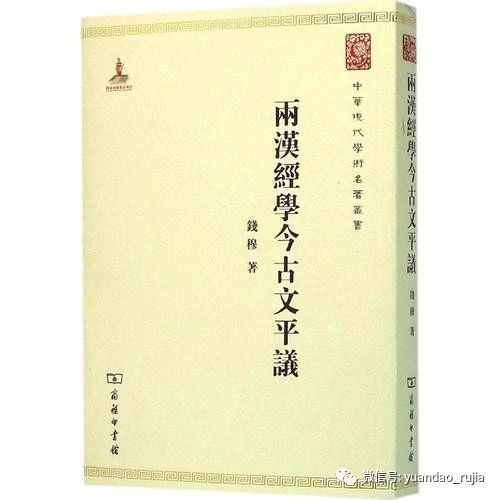
(钱穆:《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
理学家一方面扬孟抑荀,另一方面,对道德修养的重视远超过对政治制度的思考和政治活动的参与,即使是对君主的谏言也是以“正心诚意”为主。正如钱穆先生所言:
“因此而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地位也变了。他们之更可看重者,也全在其内圣之德上而不在其外王之道上,于是远从《尚书》‘十六字传心诀’,一线相承到孔孟,全都是‘圣学’,不再是‘王道’”。
钱穆指出从尧舜禹三代的“十六字传心决”到孔孟以降,都是以内圣为基础,德性修养成为理学家关注的重点,而政治则只是道德的自然延伸。
朱子所讲道统说的根本指向性在于以“十六字心传”为中心,建立一条由心性工夫出发通达道体的工夫进路。郑玄《中庸注》的解释则与朱子进路有明显不同。以下将通过朱子与郑玄对《中庸》诠释的具体文本比较说明此差别。
二、朱子与郑玄《中庸》诠释的分野
朱子的《中庸章句》和汉代郑玄的《中庸注》,诠释方法和范式不同,呈现出中庸学在两个时代的不同特色。朱子的《中庸章句》相对于汉唐注疏的特点是弱化政治性,强化道德性。
一方面,郑玄从政治角度理解《中庸》,突出其中的“圣王”作用,圣王制礼作乐,由外在约束使人成为好人,国家治理在于对圣王制度的召唤和维护;与之相对应,朱子则突出“圣人”价值,认为每个人都有成圣的先验基础,通过开启人的良知良能使人自觉提高德性,这需要对每个人内在理性和德性的召唤和培养。
朱子对《中庸》的诠释作了道德范式的转换,将郑注中政治上的差等转化为道德上的平等。(一)圣祖之政教与学者之道学
郑玄将“中庸”题解为:“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孔子之孙子思作之,以昭明圣祖之德也。”他认为《中庸》篇记“中和之为用”,目的在于“昭明圣祖之德”。
“中和”出于《中庸》首章:“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郑玄注曰:“中为大本者,以其含喜怒哀乐,礼之所由生,政教自此出也。”“中”之为根本,含有人的喜怒哀乐之情,礼是为对治人的情感而产生,政治与教化也是出于对治人的性情。
郑玄说“礼之所由生”,并非孟子式的礼由情生的意思。郑玄第三章注云:“过与不及,使道不行,唯礼能为之中。”“中”是指人情感恰到好处、无过与不及的状态,“礼”是由外以规范情感使之达于“中”的工具。
那么礼是如何产生的呢?郑玄与荀子一样,认为是圣王制礼作乐。他说:“言作礼乐者,必圣人在天子之位。”中庸之道至美却人罕能至,需要圣王制礼乐,实现教化,以使人的性情达于“中和”,实现“中庸之道”。所以,要达到“中和”的性情以至于“中庸”的政道,必有一个圣王制“礼”的环节。
郑玄说:“为政在人,政由礼也。”郑玄的“礼”是以政教为目的的外在强制性手段,他将“礼”与“政教”相连:“礼之所由生,政教自此出也”。礼由圣王出,教化由君王作,郑玄从“治”的角度言“教”:“治而广之,人放效之,是曰‘教’。”孔颖达疏:“‘修道之谓教’,谓人君在上修行此道以教于下。”
在郑玄看来“道之不行矣夫”、“民鲜能久矣”、“知者过之,不肖者不及”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民”、“知者”或“不肖者”,而是在“无明君教之”。行中庸之道的主体是君王,所以郑玄才会说《中庸》是“以昭明圣祖之德”。

(郑玄)
“圣祖”就是具有制礼作乐资格、有其位的“圣王”,其“德”也就是出于治理的需要制作礼乐以教化、规导人民,使其合于中道的能力。在君权上确立了君之位,在功效上肯定了君之德,而民众、百姓、知愚等下民则处于被动地位。
朱子与郑玄不同,他将“中庸”与“中和”直接打通,弱化了郑玄设于中间的“礼”的环节。朱子注曰:“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体也。达道者,循性之谓,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离之意”。
“中”从“性”上说,是“体”,“和”从“循性”上说,是“用”。“中庸之道”不可离,就是“性情之德”与“中和”不可离,其中并没有郑玄所说“礼之所由生,政教自此出”的中间环节。从人的“性情”可以直接导向“中庸”之道的实现。
在“性道教”的解释中,朱子承认“圣人之教”的地位,即“圣人因人物之所当行者而品节之,以为法于天下,则谓之教”。这与郑玄主张君王的教化相似,但是郑玄是从君王执行礼乐的外在形式入手以明教化之义,而朱子说:
“盖人之所以为人,道之所以为道,圣人之所以为教,原其所自,无一不本于天而备于我。学者知之,则其于学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
最后又重申:“此学问之极功、圣人之能事,初非有待于外,而修道之教亦在其中矣。”圣人所教不是从外在的规范来约束性情,而是本于人内在天生的善性。
朱子突出了每个人都拥有的“本于天而备于我”的本原之性和个人的努力,他要“学者知之”,学者若能知之,即使现在没有“圣人之教”,人们也可以而且应该“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学问之极功”放到“圣人之能事”之前,说明他更重视每一个学者发自内在的学问(德性)。
“修道之教”表面上看是圣人的功业,但实质是“初非有待于外”,它是“在其中”,即在人本性之中,圣人只是启发而不是创造,是顺应而不能强迫,关键在于学者的努力发觉,根本动力内在于己。这样“天地位,万物育”就不是郑玄所理解的国家政治秩序的平正,而是个人境界上的平和。
朱子关注的不是“礼”的制度和圣王的政教,而是个体如何能将其本具之天性发扬而“循其性之自然”,至于手段,可以是“圣人之教”,也可以是“学者之学”,且“学者之学”更重于“圣人之教”,圣王不常有,而学者当自学。“道其不行矣夫”是“由不明,故不行”,而非郑玄所说“无明君教之”而已。
(二)圣贤政治之异与圣凡德性之同
郑玄注中虽然只用“圣人”而没点明“圣王”,但就其语脉分析,他注中的“圣人”是就地位和特性而言其圣,即“圣人命在王位”。从政治上说,王者唯一,所以贤人与圣人(圣王)地位的差别不可跨越。
朱子的“圣人”则是就其“德”而言其圣,从德性的本质上圣人与凡人并无差别,二者道德可以实现同一。郑玄有意将圣人与贤人分开,主要是出于政治现实考虑,他对人性差别的主张也是出于政治差等的理论需要。相较而言,朱子突出人道德的平等和内在的超越。
第二十一章经文:“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朱子和郑玄都将“自诚明”和“自明诚”分别对应于圣人和贤人。
朱子注:“德无不实而明无不照者,圣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先明乎善,则后能实有其善者,贤人之学。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诚则无不明矣,明则可以至于诚矣。”
郑注曰:“由至诚而有明德,是圣人之性者也。由明德而有至诚,是贤人学以知之也。有至诚则必有明德,有明德则必有至诚。”两人对于“诚则明”与“明则诚”似乎是等而视之,然孔颖达的疏说得很清楚:
“此一经显天性至诚,或学而能。两者虽异,功用则相通。自,由也,言由天性至诚,而身有明德,此乃自然天性如此,故‘谓之性’。‘自诚明谓之性’者,此说学而至诚,由身聪明,勉力学习,而致至诚,非由天性,教习使然,故云‘谓之教’。……是诚则能明,明则能诚,优劣虽异,二者皆通有至诚也。”
在郑玄和孔颖达看来,圣人与贤人有本质上的差别,虽然达到“至诚”可以“相通”,但实质则并不“相同”。圣人是“自然天性如此”,从“性”上说的“至诚”,郑玄说“由至诚而有明德,是圣人之性者也”,这不仅是圣人之德的表现,而且是内在于圣人的本性。
贤人是“非由天性,教习使然”(孔疏),贤人所达到的“至诚”并没有本性上的基础,只是后天学习教化使然,是由外而强加于内。在郑、孔的语脉中,虽然“明”可以“通”于至诚,但还是存在“优劣”的差别,且这种差别是先天的,非后天可以突破。
如此,在圣贤之间有一道永远无法跨越的鸿沟。郑玄在接着两章的注中进一步加强了区分:圣人“命在王位致大平”,可以助天地赞化育,贤人“不能尽性而有至诚,于有义焉而已”。
孔疏曰:“贤人致行细小之事不能尽性,于细小之事能有至诚也……不如前经天生至诚,能尽其性,与天地参矣……不能如至诚尽物之性,但能有至诚于细小物焉而已。”贤人不能尽性,达到的只是细小事物上的至诚。圣贤的“至诚”只能是“相通”而不是“相同”。
在人性论上,郑玄主张性有差等,圣人之性与凡人不同。在政治上,圣人受天命而为王,地位最尊,影响最大,“至诚”的功绩也最大。统一的国家,王位唯一,贤人只能处下位以为臣,其负责的事务具体,其达到的功绩细微。
郑玄注第二十四章“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曰:“外内所须而合也,外内犹上下。”郑玄将“内外”解为“上下”,即君臣的上下关系,分工协力,以共建有序稳定的国家秩序。

(圣王与贤臣)
朱子对“诚明”的解释不是在君臣关系上下去区分圣贤,而是在道德修养、工夫境界上统合两者。虽然他也分圣人与贤人,但他更强调贤人通过努力“亦不异于圣人矣”。
朱子认为“人之性无不同”,圣凡之性都是来自于“天”,“盖均善而无恶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强弱之稟不齐者,才也,人所异也。”在人性本质上,圣凡并无差别。只是在现实上,凡人受气禀差别的影响,不能像圣人一样将本性自然呈现出来。
圣人之“尽其性者德无不实,故无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细精粗,无毫发之不尽也”,不过是将“天命之在我者”完全地充实,即“举其性之全体而尽之”。学者若也能将其本性推至极致、充分实现,则亦无异于圣人。
这需要一番学习修养的工夫,即“致曲”一章所谓。朱子注曰:“其次则必自其善端发见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极也。……积而至于能化,则其至诚之妙,亦不异于圣人矣。”从“致曲”到“至诚”,是从善端推而充之。凡人从“曲”入手而“推致之”,通过积累而达到至诚的广大。
朱子解“至诚”,不是在地位、功业上讲,而是在人人所具之“性”能否成全上讲。地位、功业上,圣人与贤人必有等级差别,但从每个人的“性”上,只要能达到“性之全体而尽”就无有差别。
朱子从“至诚”的无差别出发,对“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也”的解释不取君臣上下的模式,而立足于每一个人的人性:“仁者体之存,知者用之发,是皆吾性之固有,而无内外之殊。既得于己,则见于事者,以时措之,而皆得其宜也。”“内外”是一个人由内在之德性显发于外在之德行。外在的德行和功业建立在内在的德性之上,才能“皆得其宜”。
朱子从道德心性学层面充分肯定凡人通过做工夫可以达到圣人境界。也可以说,圣人与凡人是同一个人的两个阶段,它体现为工夫与境界的差别,凡人是做工夫之前及做工夫过程中的状态,而圣人是工夫纯熟后的境界。如此,圣凡打破差别的鸿沟,成为一个人生命的两种不同的状态。
总之,郑玄从政治角度强调圣贤之异,体现为政治公共秩序的差等。朱子从道德角度强调圣凡之同,体现为心性学内部的统一。
三、朱子以道德建设代替制度考量
朱子对《中庸》文本的解读以道德修身为主,但并非没有对政治的思考,而是将对国家政治制度的考量转化为对人的道德建设的关注。这在“哀公问政”章注解中有突出的体现。
经文曰:“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也者,蒲卢也。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郑玄:“敏,犹勉也。树,谓殖草木也。人之无政,若地无草木矣。……螟蛉,桑虫也。蒲卢取桑虫之子,去而变化之,以成为己子。政之于百姓,若蒲卢之于桑虫然。……在于得贤人也……取人以身,言明君乃能得人。”
郑玄将“蒲卢”训为“蜾赢,谓土蜂也”,取“变化”之意。这与荀子“化性起伪”相似,荀子说:“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在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荀子·性恶》)
“从人之性,顺人之情”会导致争夺,说明人性本恶,礼义是外在对治情欲的手段,所谓的“化”,是使人压制本性里的欲望而合于外在的善,“状变而实无别而为异者,谓之化”(《荀子·正名》)。
蜾蠃偷取桑虫之子,使之变为自己的孩子,桑虫原本不是“己子”,内在没有成为己子的本性,顺其自然生长不可能成为“己子”,必须要外在的手段强制扭转。治理百姓就像蒲卢对待桑虫,是对人性的对治、逆转,必然会伴随着勉强和反抗,所以郑注说“敏,犹勉也”,是一个勉强的过程。
朱子独取沈括的“蒲苇”说,注曰:“敏,速也。蒲卢,沈括以为蒲苇是也。以人立政,犹以地种树,其成速矣,而蒲苇又易生之物,其成尤速也。言人存政举,其易如此。……言人君为政在于得人,而取人之则又在修身,能修其身,则有君有臣,而政无不举矣。”
他解释不取旧说的原因:“蒲卢之为果蠃,他无所考,且于上下文义,亦不甚通,惟沈氏之说,乃与‘地道敏树’之云者相应,故不得而不从耳。”
撇开第一点考据理由不说,重要的地方是第二点,果蠃之“变化”之于上下文义不通,是因为朱子认为民有内在的善良德性,为政不是使“桑虫”变为另一类的“蒲卢”,而是使蒲苇顺其本性生长。朱子将“敏”训为“速”,就是认为为政顺应人的本性则快速而“化则有不知其所以然者”。
朱子将重点转向统治者自身的道德建设,即“诚”。首先,修身是为政的根本,诚是修身的根本。他说:“人君为政在于得人,而取人之则又在修身,能修其身,则有君有臣,而政无不举矣。”
如何修身?是从外在的规范入手还是由内在的德性出发?朱注曰:“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故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欲尽亲亲之仁,必由尊贤之义,故又当知人。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皆天理也,故又当知天。”修身在于“亲亲”“尊贤”,二者都皆归于天理。

(《贞观政要》)
“性,即理也”,天理就在性内,所以当反求诸己。“五道达、三达德”皆要内返于“诚”。朱子将“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所以行之者一”的“一”解为诚:“一则诚而已矣。达道虽人所共由,然无是三德,则无以行之;达德虽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诚,则人欲间之,而在其德矣。”
由此推之,无诚,则无三达德、五达道,则无以知天理的根本,不能亲亲尊贤、修身、得人,不能为政。其次,诚也是“治国九经”的根本。朱子同样将“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所以行之者一”的“一”解为诚:“一者,诚也。一有不诚,则是九者皆为虚文矣,此九经之实也。”
并且,他认为“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也是指“凡事皆欲先立乎诚”。“诚”是从国君之本然出发的德性,是“治国九经”的基础。反之,如果只有“治国九经”及议礼制度等规则,没有统治者内在的德性作支持,民不信而国不治。
再看第二十九章经文:“上焉者虽善无征,无征不信,不信民弗从;下焉者虽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从。”郑玄注:“上谓君也。君虽善,善无明征,则其善不信也。下谓臣也。臣虽善,善而不尊君,则其善亦不信也。”
郑玄将“上”、“下”解为君臣,在上位的君王,他有内在的善而没有外在的验证,他的善也不会被人信任。同样,在下位的臣子,他有内在的善而不遵守外在的尊君之礼,则他的善也不会被相信。
善的内在本质和外在表现,在孔子那里是“仁”与“礼”的关系,两者之间既统一,又存在张力。仁是礼的本质内涵,礼是仁的外化形式,形式因内容的需要而产生,但“形式”一旦外化就存在脱离内容的可能,变为无内容的空形式,所以孔子发出“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的感叹。
朱子此句注为:“上焉者,谓时王以前,如夏、商之礼虽善,而皆不可考。下焉者,谓圣人在下,如孔子虽善于礼,而不在尊位也。”上下是指时间上的先后。
他将后文“君子之道:本诸身,证诸庶民,考诸庶民”的“道”解为“议礼、制度、考文之事”,即是外在的法则,君王实行外在法则必须要有“本诸身”的内在德性,且这种德性是与民一致而可以“考诸庶民”的。
郑玄强调外在制度,认为内在的善必须依凭于制度来表现。朱子看到制度的缺陷,圣王制礼作乐,如果没有内在的根据,而仅依靠外在的权威和强压,会存在很多不稳定因素。
一方面,“礼”作为一种外在的法则,随时代变迁、历史更迭,可能会有损益,使后人无所考究、无所适从;另一方面,如果人民对礼的遵循是受迫于“圣王”的制度权威而不是道德感化,那么即使后来有像孔子一样有德的圣人出现,也会因其无位也无法得到人民的遵从。
制度会流于变迁,而圣人之心一致,重点就在于抓住内在的“心”,如此才可以重建先王盛世。由此可见,心性道德的建设始终是朱子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他对理想政治的向往融贯于道德心性的建设之中,道德建设才是其根本所在,而此与郑玄解有根本性区别。
四、朱子“道统”论以内圣为规模
通过以上对《中庸章句》内容和《序》语脉的分析,我们可以确定,朱子的“道统”说是以内圣(道德)为规模。之所以如此,有一重要原因是朱子“道统”意在辟异端、立正统。
前文已指出,佛教是朱子面临的最主要的异端。宋代最盛行的禅宗主张明心见性,朱子也正是要在心性上严辨儒佛,遂其用力的重心就从汉唐的制度哲学转向了心性哲学。
朱子说佛教徒“虽自以为直指人心而实不识心,自以为见性成佛而实不识性”,又说:“释氏自谓识心见性,然其所以不可推行者何哉?为其于性与用分为两截也……释氏非不见性,及到作用处,则曰无所不可为,故弃君背父、无所不至者,由其性与用不相管也。”

(苏轼与佛印)
我们可以说,朱子《中庸章句》中一以贯之的道德转向正是在应对佛教的心性学上“逼”出来的,这也是《序》最后落脚到批老佛之徒是“弥近理而大乱真”的原因。
有的海外学者从政治的视角解读朱子的道统说,认为朱子《序》中的“道统”与“道学”分别指两个历史阶段,“道统”一词有极强的政治意义,甚至以政治意义是朱子“道统”区别于“道学”的主要内涵。
但是,从“道统”的提出和内容来看,它出现于《中庸章句序》,又关联着整个《中庸》思想。《中庸》是《四书》之一,《四书》是朱子特意编辑以供学者学为圣人的阶梯。“道统”与“道学”合并在一起,主要强调的是学者所学之“道”的统一,而不当是强调两者的区分。
在辟佛视域下,朱子《中庸》学从“天命之谓性”的天道性命相贯通上立“道体”,从“中和”心性上承接“道”,主要目的是收拾人心、安顿人的终极归属。从前文与汉代郑玄的比较也可知,以内圣为主,外王为次,以内圣包外王,而不是以外王包内圣,当是朱子学的主要特征。
既然整个《中庸章句》的文本都以道德心性为解读范式,那出现在《序》中的“道统”也就应当置于这一语境来理解,此乃符合孟子“以意逆志”的解经方法。
总之,朱子的“道统”说是以“内圣”为主要内涵,而政治性解读,说是对朱子“道统”的发挥则可,说是朱子“道统”的原意或所谓微言大义,则是本末倒置,过度诠释。
责任编辑:近复
【上一篇】【孙向晨】重温《论语》:理解仲尼之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