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明】八十年代多重要李泽厚就多重要,跟余英时有差异
 |
陈明作者简介:陈明,男,西元一九六二年生,湖南长沙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博士。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儒教研究室副研究员,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儒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现任湘潭大学碧泉书院教授。一九九四年创办《原道》辑刊任主编至二〇二二年。著有《儒学的历史文化功能》《儒者之维》《文化儒学》《浮生论学——李泽厚陈明对谈录》《儒教与公民社会》《儒家文明论稿》《易庸学通义》《江山辽阔立多时》,主编有“原道文丛”若干种。 |
八十年代多重要李泽厚就多重要,跟余英时有差异
作者:陈明(《原道》主编,湘潭大学碧泉书院教授)
时间:西元2021年11月5日

二〇〇三年,李泽厚与陈明
儒家网:众所周知,您与李泽厚先生是忘年交,交往甚密。李泽厚先生逝世的消息,您是如何得知的?您第一感受是什么?
陈明:我是在去外面吃中饭的路上,唐文明打电话告诉我的。说实话,有点不知所措。一方面九十多的人了,他自己都说,八十以后过一年是一年,九十以后过一天是一天。另一方面,又觉得太突然了,因为半个来月前,他转来一篇稿子要我交儒家网发表。后来我听说他又摔跤了,电话过去无接听,然后又是他的电话过来,我有没听到。打回去吧,又见他留言,说是拨错号了,并没什么事。既然这样,那就再说吧,结果……真是太无常了!
界面文化:能否请你谈一谈和李泽厚的交往?
陈明:在上个世纪80年代,李泽厚先生很热门。那时候我在湖南一个中学教书,想要考中国哲学的研究生,就把自己的一篇文章寄给了他。没有想到,他给我回了信,这也鼓舞了我。后来我就去考研、读博了。
90年代初我博士毕业后办了一个叫《原道》的儒学刊物,邀他写稿。当时言论不是很宽松,他也需要发声平台,支持力度很大,唯一一个要求就是他的文章要“放在头一篇”,“气一气某些人”,非常率真。
21世纪初,盛洪想组织一些中老年学者对谈,于是就有了《浮生论学——李泽厚、陈明2001年对谈录》,这里面亦庄亦谐,谈了各种各样的思想、学术,乃至还有人生、八卦,颇招惹了一些是非。
到了2006年前后,方克立提出“大陆新儒家”的群体已经出现,又是一阵骚动。名列其间的我也确实由此对自己的思想观点有了某种自觉性,意识到自己坚持的中体西用与李泽厚的西体中用,确实存在某种性质上的不同甚至对立。李泽厚对大陆新儒家不认同,也不是很愿意倾听别人说的东西,比如说他会把我和蒋庆等人观点完全看作一样,实际上我们几个的个体差别是很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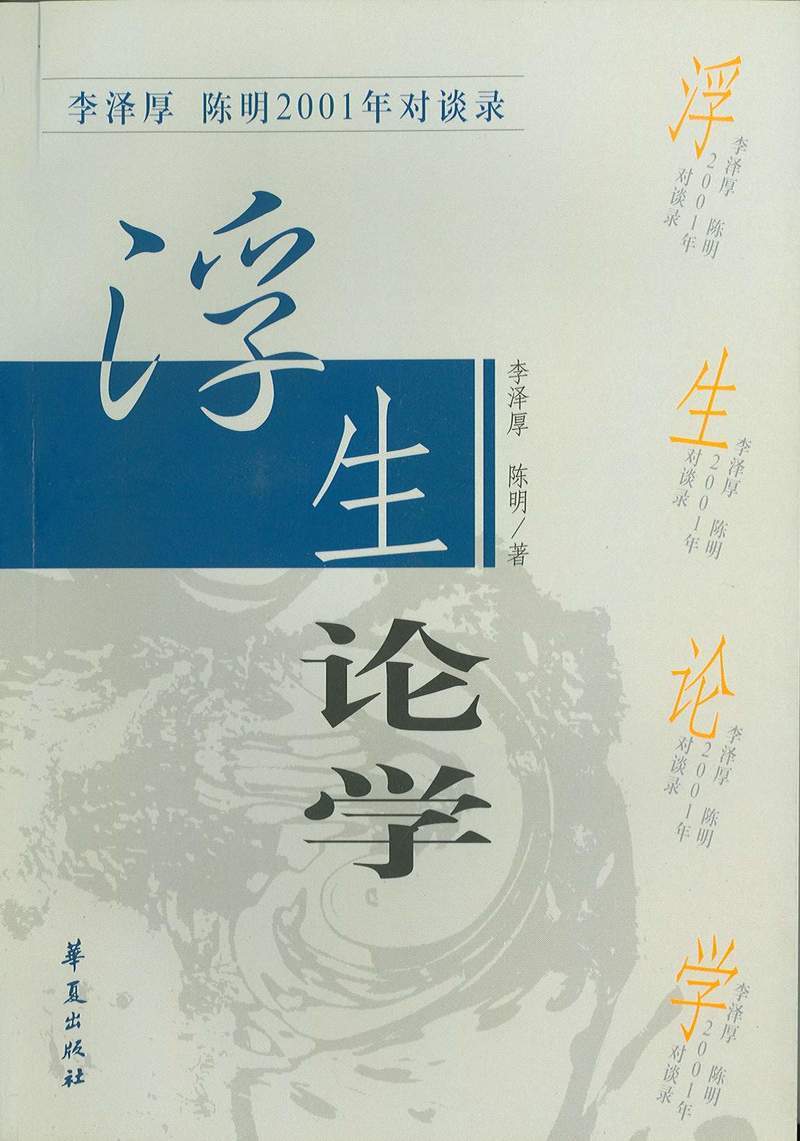
《浮生论学:李泽厚、陈明2001年对谈录》
作者:李泽厚 / 陈明
出版社:华夏出版社
出版年: 2002年1月
界面文化:李泽厚对大陆新儒家主要不认同的地方在哪里?
陈明:一个是大陆新儒家在学术范式上倾向从宗教的角度理解儒家;而他们会倾向于从哲学角度理解儒家。第二点是,他倾向于把五四的民主科学作为价值标准去看待儒学的现实意义;我们则对这种标准的正当性比较怀疑,我们觉得儒学的理解与评价首先要回到历史中,从儒学和中国人的安身立命、社会的整合凝聚以及国家国族与文明的建构这个角度,看它做了些什么,做得怎样。简单说他们是一个现代性视角或外部性视角,我们则是一个文明论视角、内部视角。
界面文化:在我看来,一般人观点不一样就很难再交流下去。
陈明:没错。一般人观点不同就会觉得话不投机半句多,观点不一样心理上就会疏远。但我们不是。我们虽然观点不同,关系还是非常好。原因之一是他虽然持自由主义立场,但并不是恨国党,他像鲁迅那样,对国家、对民族有很多的反思和批判,但深层还是有一种家国情怀。再一个就是我们的气质之性比较接近,都喜欢直来直去,说什么评什么经常所见略同不谋而合。
心理上讲,他名气太大了,觉得我们后生小子不足畏。我也会认为,你是长辈,思想属于那个时代。既然是思想史意义上的紧张,那就自有后人评说,不必影响我们的交情。所以后来我们就多谈人生,谈饮食男女、风花雪月了。譬如给他当司机去看望他的师友,像任继愈、何兆武等。
界面文化:也会谈到死吗?
陈明:我们经常会谈啊。他经常说父母死得早,担心自己活不长。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有次孔子基金会请客吃饭,他70岁不到,就问比自己长一辈的宫达非长寿的秘诀是什么。我过年给他打个电话一般都会祝他健康长寿。84岁那年他特别担心,我说没问题,过了84,一马平川。他说一马平川是什么意思,我说直接奔90啊。他说,那也很快啊。
九十一,很高寿了。他教过我两个养生的秘诀,一个是睡好觉,“吃安眠药没问题”。他四十来岁就开始吃安眠药,五十年把全世界的安眠药都吃完了。还有一个就是“多吃菜,少吃饭”。我们都是湖南人,湘菜重口味,我一般都是几个钵子饭。他说,你一看就是苦孩子出身,现在不要这样了,这是不对的。后来我看了一些书知道他说的是对的,所以我现在也在跟他学。
其实我们讨论死都是很随意的,比如说讨论怎么死比较好,都认为自我了断比较好,可能是搞哲学和宗教的缘故吧。对肉身朽坏比较在意,可能跟他的情本论有点关系吧?他留下来很多的文字,这是比石头都要长久的存在呢。
儒家网:今年去世的余英时先生和李泽厚先生,在华人思想界都极具影响力,您认为二者的异同是?
陈明:二人很值得拿出来比一比,除开都生于1930,学界地位也都属超重量级。
好像有人说起过,如果在国外,余英时的地位会不会是属于你的?他的回答是,就是现在,我也没觉得不如他!
在我看来,李泽厚是思想家,余英时是思想史家。虽然都比较推崇西方,但李泽厚的主体意识比较强,西体中用是说把西方的东西拿过来为我所用。余英时则是把西方的东西当做普世规范,或者把中国的说成那样,或者把那些东西当成我们的标准、我们的未来。
李泽厚还有国情意识,有家国情怀,譬如说能够理解几千年的中央集权体制,高度肯定秦始皇,强调吃饭或发展经济头等重要。余英时的中国则是抽象的,虽然也有山川、文化,但对历史和亿万百姓的生活需要却缺乏体认同情。这可能与他的意识形态偏执有关。
学术上,李泽厚讲巫史传统,重在辨析中西差异——乃至认差异为本质在我看来很有问题,但这还是延续五四以来的西方参照系。余英时讲哲学突破,讲轴心期,则是将西方的学术范式用于对中国历史和文明的阐释——他的著作几乎每一本后面都有一位洋人的影子。
还一个差别就是,余英时对传统尤其儒家传统感情上似乎比李泽厚更深,李泽厚受历史唯物主义影响更大。
当然,这只是大概言之。

李泽厚与陈明在北京蓝旗营湘菜馆五方院
儒家网:有人认为,李泽厚先生的逝世宣告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您认同吗?
陈明:认同。我在一个纪念庞朴先生的座谈会上说过,李泽厚、余英时、余敦康以及袁伟时、资中筠他们都是“五四下的蛋”。那种对科学和民主的激情和崇拜,对于救亡、对于改革开放的态度十分正常,也十分应景。但是,由这二者构成的西方想象其实是不真实的。
科学是普世的,民主是一种政治现代性。科学已经被全面拥抱,成绩也很大,至于民主,作为一种价值与作为一种制度是不完全一样的。建立国家不是为了实现什么价值,而是为了生活得更好,而不是实现什么乌托邦理想或抽象价值。
现在把中华民族的复兴当做发展目标,它的意思应该就是中华民族能过上更好的生活。这是社会整体的一种成熟,从救亡到复兴,可以说是一种时代转换。
在这个背景上可以说李泽厚的逝世是一个时代的结束。
他对我离开北京回湖南不太赞同,其实我对他离开中国去美国也一样不赞成。这些年中国的变化很大,主要就是救亡到复兴的转换。这是一种转换,也是一种回归——救亡和复兴都是以中华民族为主词,是对中间曾经具有主导性的以阶级和个人为主词的革命叙事和启蒙叙事的某种扬弃。这是我说的转变内涵之所在。也许因为远隔重洋,这些没有在他的作品中有所反映。他跟我聊的,主要是伦理学,对人肉炸弹的解释。当我说对这些我不太关心时,他很失望,甚至生气。
儒家网:对李泽厚先生的以下几个学术观点,一是“儒学四期”说,特别是其中关切到的“实践—外王”问题,二是中国思想起源的“巫史传统”说,三是“举孟旗、行荀路”说,您如何评论?
陈明:四期说九十年代他曾在给我的信中完整表述过,不知那是不是第一次提出。港台新儒家的三期说我不赞成,汉代确立的“霸王道杂之”这一治理结构具有文明论的意义,虽然李先生只是从荀学的角度阐述。在我看来,汉代不是荀学,而是经学,荀子的东西要放到春秋学脉络里去理解定位。
再就是当代的展开,他的语境还是五四或后五四的,也就是现代性的,我觉得需要转为文明论。因为五四的地位和意义被严重夸大高估了,在它被与启蒙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它就被从原来所属的历史脉络或救亡语境中抽离出来了。事实上它原本只是救亡的一个环节,现在需要重新摁回去,重建救亡和复兴的整体性,这也是今天从文明论理解儒学理解历史的前提。
所谓的实践外王,也需要从这个框架里去理解。
至于巫史传统,根本不成立,中国这么大的一个文明,基础、精神或本质怎么可能是巫史?孔子自己也清楚说他与巫史是同途而殊归——你说一个思想的性质应该是由发生的起点决定还是由它追求的目标决定?becoming区分于being,他是从巫术角度去理解,其实从“天地之大德曰生”,从“成己成物”角度去说,它的后面或根据是“天”;这才是究竟义。
可以进一步说,李泽厚这样的认知存在方法论上的错误,那就是把差异当本质,把差异的寻求当做自己研究的目的。这是五四时期中国人把西方当作参照系的影响的当代遗存。文明是有差异,但同才是基本面,那些差异可以理解为某种共同本性与需求在一定历史环境中的历史表现形态。因为人性是相通的。这是可以理解的基础,也是可以互补的根据。
至于“举孟旗,行荀路”,这还是内圣外王的某种翻版。社会有其自身的逻辑,儒家可以自己想象一种理想的方案或形态,但最终的落实,必然是思想与社会互相选择的结果,并表现出某种有机统一性。董仲舒与汉武帝达成合作,是有所调整的,是互相妥协的结果。从儒教或儒家角度说,你讲“举孟旗,行荀路”,那我要问,孔子在哪里?董仲舒的工作怎么解释?

2005年,李泽厚与陈明在北京李宅
儒家网:坊间有所谓李泽厚先生“有学生,无弟子”之说,您怎么看待?在李泽厚先生逐渐淡出学界直至逝世的当今时代,如何传承他的学术思想遗产?
陈明:这个很有意思。他的学生也不算少,但走他那条路子却找不到,可能是一般的学生学不来,太好的学生又不愿学吧——他自己曾说,他从不强求学生做什么,但说这话的时候又有点可惜。像他最欣赏的赵汀阳,做的东西他并不很认可。他曾说你们按照我的路子走可以走得很远,但你们偏不,迟早会后悔的。赵汀阳已经自成一家,不可复制。我这个忘年交则是回归传统——张之洞、董仲舒、孔子、文王。这实际是一种时代转换或代际变化。其他学生,也听过他的评点,网上也可以多少搜到,很难说有谁克绍箕裘。学生很多,是因为八十年代他提的一些东西被各界广泛接受,美学热之类的,现在看,本身应该属于社会现象而不是学术或思想现象。
他实际从未淡出学界,只是影响力不如从前。这主要是时代转换的必然。从这次刷屏的情况就可以知道,主要是八十年代记忆。他身上集合了儒家、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多种因素,这种综合性对我们的提醒也许是非常重要的吧?这三种传统都已在中国社会生根结合为一种生态,也都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意义。
儒家网:您对李泽厚先生的历史定位是?
陈明:私下里我也问过这个问题,以前就把他与牟宗三并列。但据一位跟他聊得多的朋友说,他自己是把自己承接康有为,后来又更上层楼接到朱子。别的不说,我觉得他还是在儒家的坐标里找自己的位子,而不是往休谟或者葛兰西那边靠,挺好。
只是,从刚办《原道》的时候起我就问他是不是儒家?愿不愿意成为儒家?他一直回避。去年通电话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自己是儒家,但马上又改口——你看他内心其实到生命的最后岁月还在纠结。
八十年代多重要李泽厚就多重要。八十年代某种意义上说是国家社会的青春期。青春充满躁动,意味着多种可能性。现在的模样,很难说是李的思想逻辑之展开、那种现代性的展开。二者之间的紧张为许多的刷屏提供了动力,但只有对这种紧张进行理解诠释,才可以把他的著作从个人记忆与情感内重新嵌入思想史,在这样的坐标里进行评价讨论。这应该才是对一个思想家最好的纪念和尊重。
作者文集更多
- 【陈明】天人学与心性论的系统紧张与整··· 02-29
- 敷赞圣旨、莫若注经:陈明著《易庸学通··· 01-23
- 陈明 著《江山辽阔立多时》自序暨目录 12-22
- 【陈明】我的中小学老师 09-27
- 【陈明】宝古佬与云山院 09-27
- 【陈明】从朱张思想互动看湖湘学特征与··· 08-10
- 【陈明】《原道》第44辑编后记(附内容··· 01-26
- 【陈明】文化视域里的哲学之思 ——从Me··· 12-31
- 【陈明】君子儒的期待 ——孔子与子夏关··· 12-31
- 【陈明】天人之学与心性之学的紧张与分··· 12-31
微信公众号
儒家网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

微信公众号
儒家网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