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克劳斯】我们注定要拥有理性主义的、无爱的未来吗?
我们注定要拥有理性主义的、无爱的未来吗?
——哈里斯·波尔著《坚守人性》简评
作者:保罗·克劳斯 著 吴万伟 译
来源:译者授权儒家网发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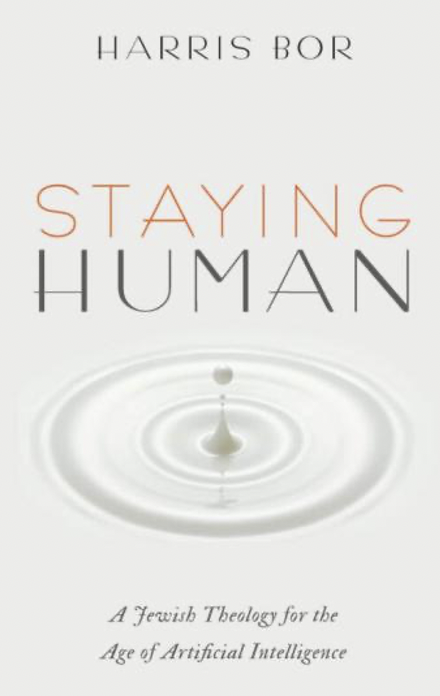
本文评论的书:Harris Bor. Staying Human: A Jewish Theology for the A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ugene, OR: Cascade Books, 2021.
科幻小说是现代性占支配地位的文化神话。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给我们提供了科幻小说的最好定义,他说,这个体裁是“文学的一个分支,探讨的是人们对于科学技术变化做出的反应。”尤其是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技术毁灭人类的幽灵已经根植在我们的文化心理之中。我之前在多家期刊上发表过不少文章,涉及到科幻小说中充斥的神学和哲学主题,这些在有学问的人中并不是任何新鲜的东西---萦绕在我们身边的技术幽灵似乎唤醒了人们的神学想象力和欲望。哈里斯·波尔(Harris Bor)在其令人难忘但充满希望的新书中同样写到“现代版本刻画的不是圣经版上帝,但在性质上仍然属于宗教。”神学必须满足于“人类针对科学技术变化做出的反应。”波尔在其新书中尝试在做的恰恰就是这样的事。
波尔在《坚守人性:人工智能时代的犹太神学》中假设,未来主义者的技术超人类主义前景在某种程度上将成为我们的现实。未来将不再有技术奇点(technological singularity)的失败,不再有反乌托邦,也不再有科学让生活陷入黑暗之中的传统概念之痛。这并不是假定波尔乐于接受技术超人类主义的未来,认定他是乐观主义者。远非如此,本书的本质是试图在技术转化和奇点中的惨淡无望的技术世界为人性和仁爱伦理学开辟出空间。在波尔看来,不是屈服于超人类主义的诱惑,而是将“理性主义神秘主义”品牌与启蒙理性主义的更好一面(尤其是斯宾诺莎)重新联结起来才可以为我们提供前进的道路,而“理性主义神秘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广泛的现代主义犹太圣经综合论。
我们都感受到了技术科学主义色彩越来越浓厚的世界中令人担忧的问题。最近,很多研究已经显示社交媒体和其他技术上瘾症给人们的心理健康带来消极的影响。技术科学主义体制常常被用于实现极权主义目标,虽然这并非什么新鲜玩意儿,包括埃里克•沃格林(Eric Voegelin)在内的数不清的20世纪作家和知识分子都详细阐述过此类观点。势头越来越强劲的超人类主义意识形态非常乐观地期待彻底消除人性和生物学本质而去追求超验性的前景。波尔注意到,“死亡已经成为需要克服的障碍。”但是,正是死亡的现实赋予了生命以神圣性、意义和目的。无论是在诗歌还是在神学中,最高形式的爱几乎无所不在地与死亡捆绑在一起。
在这困难重重的是非之地,波尔试图提供一种妥协之路,一方面坚守人性,但同时在总体上拒绝技术和科学主义世界观。在他看来,该工程的关键是“完善斯宾诺莎”,同时再稍微补充一些有关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交流讨论。斯宾诺莎无需我来介绍,他的诸多观点如上帝是自然、理性应该控制激情、激情对人类生活来说有危险等已经引起回响多个世纪了,他那睿智的理性主义哲学认定理性探索能够推动知识、伦理甚至对上帝和人的爱。斯宾诺莎的哲学鼓吹一种单一性,认定万物最终都浓缩成为一体和共同体,虽然他不是哲学一元论的缔造者,但他的著作的隐含意义帮助复兴了一元论,而过去这种一元论一直被视为从前时代的各种中世纪神秘主义而不屑一顾。
这本新书的作者显然是斯宾诺莎爱好者,他知识渊博,受到过良好的教育,他甚至专门留出一章论证“为什么斯宾诺莎是正确的”。但是,斯宾诺莎是正确的吗?作者给出了一长串清单,列举了科学和哲学中受到斯宾诺莎式单一性诱惑的人,不过,令人非常好奇的是,所有的人都已经一百多岁了。理由其实很简单,在当今科学范式中,一元论已经声名狼藉,它的断言和主张在当今已经站不住脚了。而且,激情真的那么糟糕?理性真的那么好吗?对理性、科学和技术的崇拜已经释放出20世纪的最大恐怖梦魇,催生了这个世界见证过的最恶毒、最具破坏性的极权主义运动。电影和文学中大量出现的是我们内心对人工智能未来的充满焦虑,担忧完全建立在纯数学和科学基础上的技术恐怖---其中所包含的无情感的精神,其隐含意义是技术科学主义占支配地位的符合逻辑的后果必然是毁灭人类的种族灭绝。我们有很多理由(reason)不把理性(reason)视为把我们从堕落中拯救出来的天恩,请原谅我在此使用的双关语。技术科学主义力量带来恐怖、暴力和专制独裁,这样的世界观虽然声名狼藉,但在斯宾诺莎的整体世界观中仍然根深蒂固。对于这个事实,波尔在书中并没有忽略,他甚至承认了这一点,虽然尝试在框架之内做一些修改。“我们的技术世界观遵循了斯宾诺莎的脚步,我们必须承认,斯宾诺莎的观点尽管非常吸引人,但其观念中也存在黑暗面。”
波尔可能引起争议的问题的核心是,去人性化的技术试图通过人工的超人类主义奇点(它将真的剥夺人类权力和削弱人性)将人统一起来,在这样的时代,究竟什么东西能够让我们保持强大,在名义上追求共同的未来前景的同时维持独特的人性。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波尔重新推出自柏拉图以来已经老掉牙的答案:理性。“理性是我们共享的语言,是能把我们团结起来的纽带,是人性应该依赖的基石。”但是,这种说法存在问题。谁的理性?我们谈论的理性是什么类型?
理性呈现为两种可辨认出的学派,一个是经典,一个是现代,虽然这样说在总体上有过分简单化的倾向。经典理性统一在真和善的概念之上,让幸福主义美德(eudemonistic virtue)的目的论成为可能。经典理性认为,人们应该认识超验性道德秩序,而且要在生活中将其体现出来,因此,过一种满足的、有美德的幸福生活。但是,波尔指出了相反的论证,即真理不是宗教甚至不是哲学所关心之事,只不过是描述现实的人类幸福的另外一种简单语言,可以说是麻烦不断的时代的解药(因为当今生活的时代是某种哲学神学复兴的时代)。
因此,波尔抛弃了理性的古代概念,接受了理性的现代概念,而这种认识从终极性上说带有物质主义的、实用主义的立场,是超人类主义者同样拥抱的立场,“如果我们通过科学理解推动或者破坏我们身体和精神幸福的机制,以及这样的机制如何影响了我们的观念如自我价值、社群、人际关系,那么科学就赢得了指导我们生活的权利。”(黑体为作者添加)只要把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约翰·洛克(John Locke)、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的画面放在那个命题旁边就一目了然了。现代人对理性的理解是从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和托马斯·霍布斯开始的,现在经过中介进入超人类主义者的阶段,这是其穷尽性的逻辑结论,总而言之,就是摆脱(身体)伤害的世界。因为死亡是有害的,所以死亡必须被战胜。理性就是展现出获得物质需要和避免物质伤害的最有效手段来。这是明显不同于经典传统中的理性,那里,理性是连接现象学领域和超验性领域的桥梁,人们依靠认识善恶而找到一种将真善美统一起来的生活。
而且,为什么科学“赢得了指导我们生活的权利”?而且,谁的科学概念?科学是涵盖范围广泛的意识形态,包括20世纪某些最糟糕的种族灭绝运动:优生学、纳粹主义等。提出相反的论证就是故意混淆科学能被用来实现可怕目的这个明显事实(本书中简要称赞的科学代理人如斯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从来不愿意承认这一点),科学遭到谴责与科学常常得到推崇和称赞的理由其实是一样的。“非真正苏格兰人谬误”(The No True Scotsman fallacy)是科学主义意识形态分子使用的典型的反驳方式,无论他们属于何种派别品牌或倾向,在遭遇这个问题时都会利用这一策略。其实,这就是不愿意承认事实真相的行为,即科学并非天生有益的。确实存在能切实改善生活的科学,这种科学带给我们舒适、健康、安全等好处。但是,科学还有另外一面,它能实现控制、独裁和老大哥的干涉,这种科学有毁灭星球的风险,更不用说破坏我们的灵魂了。两者常常是连在一起分不开的。
这是波尔自己也深陷其中难以自拔的棘手问题。他公开地、不断地承认技术和超人类主义意识形态的黑暗面(他花费一整章的篇幅探讨这个问题),但他不想接受这个旨在用来坚守人性的不言自明的框架,因为他担忧的正是这个框架刺激超人类主义者不惜采取欺骗手段。他想鱼与熊掌兼得。他希望用人文主义寺庙取代超人类主义寺庙,以此挽救超人类主义寺庙的基石,就好像基石不会影响所建造的寺庙一样。
斯宾诺莎启蒙哲学是理性主义的、机械的、从终极上说是还原性的唯物主义哲学,这必然导致波尔试图避免的危机。任何数量的理性主义神秘主义以及负责“存在和生成”的上帝都拯救不了我们,它更多是19世纪现代主义神学在21世纪的更新版。简单的事实是现代主义神学就像传统神学一样已经走到了尽头。我们的任务不是要改善或放大过去的传统(虽然有名字更改,进步主义神学或现代神学仍然是过去的传统)而是要拥抱全新的东西(波尔声称自己在做之事,但真正提供的是过程神学的复兴或修改)。在我们将伴随着现代神学而来的不可避免的人工智能作为神的意识形态来辩护的情况下,提供“存在和生成神学”的努力仅仅是缓和接受超人类主义胜利的痛苦而已。
本书的下半部分阐述了用犹太术语改善的斯宾诺莎,但是,其普遍意义足够以为其他一神教传统(尤其是基督教)提供营养和洞察力。提供“存在和生成”神学是学术研究和综合性努力的惊人成就。波尔勇敢地迎接我们不知不觉陷入的挑战,说服我们相信他的理论,虽然其构建可能不够完美。任何敏感的、受过教育的人当然都能从波尔的论述中受益。我们的作者渴望成为人文主义的朋友,即使他的偶像从终极上说是人性的敌人,这一点应该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让人团结起来并赋予我们生活的理由的语言是爱和死亡而不是理性和实用伦理。爱的问题是它是具有强烈的特殊性,很容易变成嫉妒。这是理性主义者的仇恨。提醒各位,斯宾诺莎遭到爱情的唾弃和冷落,一辈子都没有结婚。所谓启蒙的许多伟大的理性主义哲学家都属于同一个类别:未婚的、缺乏爱心的、没有品尝过浪漫爱情甜蜜的男人,他们觉得充满爱心的、享受浪漫爱情的已婚男人是这个世界的问题,毫无疑问,这种看法影响了他们对激情的负面看法,他们带着蔑视、厌恶和嘲讽去看待骑士、将军、劫掠的海盗。没有激情的世界是没有爱的世界,而没有爱的世界必然导致现在遭遇的技术的黑暗面。这是知识分子的问题。他们痴迷于理性和理由,他们缺乏的其实就是刺激和感动大部分人生活的东西:爱情、激情和瞬间情绪的热度。
现在请让我简单偏离话题,谈一谈艺术想象力的优越性,这是斯宾诺莎贬低的东西。与该哲学总是导致的极权主义相反,波尔的确高贵地试图在其改善的哲学重建之内为其辩护,并推荐人们去培养艺术想象力。想象力比冷酷的理性更优越,艺术更优越于哲学(我是以接受过六年哲学教育且主要从事艺术和文学批评的人的身份说这话的)。过去50年,很多伟大的文化创造一直无意识地或者下意识地感受到波尔试图在本书中矫正的同样问题。那就是技术科学主义世界里的爱的问题,是技术科学主义世界给爱和爱所体现的精神带来的威胁。
这里最明显的例子是《星球大战》。黑暗面是什么?是技术科学主义星系帝国(奇点?)的罪恶和作为其技术科学主义命令结果,它拥有实施种族灭绝的威力。它如何被打败?通过爱。父亲达斯·维德/安纳金·天行者(Darth Vader/Anakin Skywalker)对儿子卢克·天行者(Luke Skywalker)的爱,男人汉·索洛(Han Solo)对女人莉亚公主(Princess Leia)的爱。这是导致帝国崩溃的东西。最近,《阿凡达》和《星际穿越》之类电影大片也显示出同样的担忧,它们以充满想象力的艺术方式给我们提供了同样的答案:爱能救赎和拯救技术和科学造成的破坏。
最终来说,斯宾诺莎站在星系帝国一边,资源开发管理总署(the RDA)和布兰德教授(Professor Brand)和任何站在斯宾诺莎一边的人,要么在那边毁灭,要么必须背叛他,并将他抛弃。作者试图维持斯宾诺莎式人文主义的妥协,这虽然值得称赞,却是一条哪儿也到不了的死胡同。实际上,它是通向技术科学主义极权主义的桥梁。在思想者中间,斯宾诺莎是现代性的偶像,你要么拥抱这个偶像,要么抛弃这个偶像。波尔为了现代性而试图拯救拥有想象力的诗性神学,这样的努力虽然值得称道,但依靠改善斯宾诺莎并不能实现这个目标。
人是拥有爱的生物。理性正是从爱中产生的,它是试图解释推动人类心灵活动的内心情感。将理性凌驾于爱情之上最终将杀死爱情。要坚守人性,人们就必须爱。因为爱是乱哄哄的,尤其是容易变成嫉妒的,若用约翰·哈曼(Johann Hamann)的话是“比理性更高”(Höher als alle Vernunft )。爱是形而上学,因为现代理性和科学不能应对形而上学,只能对付实用性和现实性之物,理性无法维持人性,因为人也是形而上学生物,成为有爱的生物就意味着有能力“认识”爱是什么。
哈里斯·波尔参与到里程碑式的英雄举动中,但在我看来,这种反对现代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危险和过分行径的捍卫行动存在缺陷,它仍然牢牢抓住不言自明的基础不放,正是这个基础把技术科学主义崇拜给人类生活带来了绝对权力和恐怖。就算承认技术科学主义的权力和恐怖等危险,若没有能力拥抱不同的形而上学和范式,也是注定要失败的。最后,真正关心斯宾诺莎的是谁?普通信徒当然不关心。这个问题就像普通天主教徒不关心圣托马斯·阿奎那(Saint Thomas Aquinas)一样。普通信徒现在不关心将来也不会关心这些圣人,他们关心的人通常都是和民众区分开来的人。在我当学生和这么多年与学生在一起的教学经历中,我只遇见过一个学生(在耶鲁上学时)痴迷于斯宾诺莎和斯宾诺莎神学或哲学。相反,我遇见过很多学生对神学在艺术和想象力的应用激动不已。如果坚守人性是目标,我们必须到他们所在的地方与其会面。
波尔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了不起著作,作者知识渊博,文笔优美,谈论的是当今时代面对的真问题,而非电视和社交媒体垄断和算法炮制出来的吸引人们关注的稍纵即逝的问题。人们当然能够从斯宾诺莎那里学到很多,认识到他的影响和超越人类主义的危险和前景,同时,我们也看到作者好心的尝试,企图在划时代的转化这个旋涡中拯救人类的共同精神和心灵。我特别同情这些试图在去人性化的人工智能、技术和超越人类主义者面前维持人文主义的人的努力,愿意为哈里斯·波尔充满勇气的新书欢呼。这是一本了不起的作品,即使你并不完全赞同作者的观点。虽然同情该书整体上的人文主义倾向,但我仍然不赞同斯宾诺莎或“理性主义神秘主义”是前进路径。人们可能说---理性主义神秘主义---遵从埃里克·沃格林的某种矫正和洞察力---是激励和感动超越人类主义/去人文主义奇点的东西,这正是波尔竭力想摆脱的东西。不过,在此问题的挣扎中,波尔实现了神学的最高级召唤。
任何关心超越人类主义问题和思考人类未来的人,都应该捡起《坚守人性》阅读一番,相信你会受益匪浅。我自己有切身的体会。重新回顾一下我抛弃的教育学科是非常有意思,恰恰是因为那个学科引导我们来到冷酷的、贫瘠的、极权主义,却不能像艺术和想象力的世界那样提供任何有意义的、人性的东西。如果除了是理性主义极权主义科学崇拜的婢女之外,哲学还拥有未来的话---自斯宾诺莎以来一直如此---它将来自那些捍卫艺术和想象力的首要重要性,但坚决反对隐含性的极权主义理性主义的哲学家。终极而言,这意味着抛弃斯宾诺莎。
作者简介:
保罗·克劳斯(Paul Krause),《沃格林评论》主编,著有《爱的历程:基督教伟大著作指南》(Wipf and Stock, 2021),为《当今学院演讲》(Lexington Press, 2019)和《认识疾病和灾难》(Routledge, 2022)供稿。曾在俄亥俄州鲍德温华莱士大学(Baldwin Wallace University)、耶鲁大学和伯明翰大学接受教育,经常为报刊撰写有关艺术、古典学、文学、宗教、政治的文章。
译自:Are We Doomed to a Rationalist, Loveless, Future? A Review of Harris Bor’s “Staying Human”
https://voegelinview.com/review-harris-bor-staying-hum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