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旭】中国法治的历史哲学沉思——王人博《1840年以来的中国》读后感
中国法治的历史哲学沉思
——王人博《1840年以来的中国》读后感
作者:王旭(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来源:《原道》第40辑,陈明、朱汉民主编,湖南大学出版社2021年8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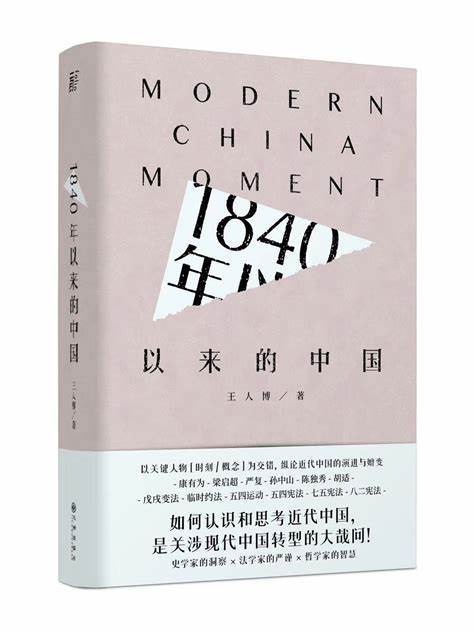
传统中国知识人的学问人生,追求“会通”的境界。史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这样,诗人“读书之乐何所在,数点梅花天地心”也是这样。牟宗三总结为“通孔的智慧”,意谓透过个体生命理解十方世界,徜徉宇宙天地,诠释世道人心。
然而,现代学术体制应了庄子那句话,“道术为天下裂”,治学者被囚禁于所谓职业化与技术化的智力牢笼,不但文字与人格高度分裂,知识、性情与见识也渐行渐远。
而中国法学因其高度的知识碎片化与技术化,更走上了背离“会通”与“绵延”一途,以部门法和实在法的名义,向“区隔”与“断裂”迈进。作为一种法学意识形态,“部门法”意识完成了对整全知识的区隔,“实在法”意识则加剧了系统与意义世界的断裂。
在主流的法教义学思考框架里,法律知识及运用是没有时间意识的存在的,不需要追问知识的根源,只需根据此在(此时此地)职业共同体的惯习进行妥当操作,成为“未完成的理论协议”——法学在现代化的同时也完成了法学研究者的机械化与客体化。
在我看来,王人博先生《1840年以来的中国》最大的抱负就是要在法学,尤其是宪法学领域,接续“通孔的智慧”之一途,对经过法教义学洗礼的法学意识形态进行清理,恢复人在法律秩序中的思考主体性,恢复法学思考者的历史感和尊严。
中国的宪法秩序何以如此,根据何在,这是作者的根本追问。而这种根据并非哈贝马斯所讲的“理性的同一性”意义上的价值整体,也非自然法意义上的不变的价值设定,而是包含着文化中国与历史中国的演化,从而也就是中国人参与历史进而形塑、抉择历史的过程。
“1840年以来的中国”这个表述本身,就是一种时间场域的设定,以截断众流的笔力给中国法治设定早已冷却的历史温度。法学知识的很多价值前见与技术路径已经成为法律人和研究者“日用而不知”的心灵积习,但作者告诉我们:“积习”是思考向时间的投降,而思考与反思“积习”才能恢复历史中的人的全部的尊严。因此,我认为,这本书是为中国法律知识人赢得尊严的作品。
法治建设的高歌猛进本身就完成了一种“历史的狡黠”,按王人博先生在书中借用布迪厄的用语,它让思考者不再思考实践场域的再生产机制本身,不再追问再生产机制的内在根据与正当性,这必然又使得法治在具体领域成为无目的与无方向的行动,充满偶然、徘徊与挫折。
然而,1840年以来的中国究竟是如何遭遇法治的,缘起何处,何以至此,要对这个再生产机制进行理论解说,毫无疑问超出了法学的视域,属于“中国学”的一部分,属于中国与西方遭逢的整体叙事的一部分。
因此,本书的上半部分其实是王人博先生的“中国学”概论,下半部分则切入到我概括为“宪法的历史生成”这个细目,以此为线索,在个殊中试图回答本相。
有意思的是,很多有影响的中国学研究都是大开大合,倾向于整体架构叙事脉络,远溯到孟德斯鸠、黑格尔、马克斯·韦伯的学说,是将中国作为丧失了文化亲近性与主体性的整体世界图景变量或异数加以对待。近代以来,费正清学派的“冲击—回应”模型本质就是这种思考的延申。在这里,中国不是一个文明的自变体,它在世界历史图景中并没有主体性的位置。
20世纪70年代开始,以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的主张为代表,到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海外中国学开始剖析中国内在的社会肌体,但这并不意味着研究中国就可以得到某种对世界历史普遍图景的理解,甚至仍然可能只是对他者的研究,或仅仅是反思研究者对自身文明研究局限的一种手段,例如沟口提出“作为方法的中国”对近代日本研究本身的刺激或反思。
王人博先生的理论抱负显然不是重复咀嚼前述研究的心得。《1840年以来的中国》充分展现了,一个具有主体意识的中国人研究中国、进而借助研究中国对世界普遍性表达看法的理论能力,试图从中国人的性情、观点、视角与生活世界为我们自己建立历史哲学。
在这个历史哲学里,“宪法的历史生成”就有了理论根基和文化依凭,用唐君毅的话说,这是“灵根自植”的课业。掩卷遐思,不揣冒昧,我想把王人博先生的宪法历史哲学概括为四对关键词。
一是时间与意义。与近代解说西方国家来源的典范的社会契约论不同,“自然状态”表达的历史哲学是“没有时间的空间”。无论在霍布斯、卢梭还是洛克,乃至罗尔斯的版本里,“自然状态”就是一个哲学拟制,是为了解决社会稳定性问题而设定的文明开端,但它恰好没有历史,没有时间。
但“1840年以来”本身就是一个有具体时间感的设定与起点,这里面有鲜活的思想、事件和人物,在王人博先生看来,中国人的历史哲学必须伴随有“语境”的时间开展,从“革命”“临时约法”“共同纲领”直到“八二宪法的建设者”概念,离开对历史的情景化分析与理解,就没有历史哲学。
时间是“物”的存在,但中国人的历史哲学并没有物化,我们对社会秩序演化的认知是建立在“物”背后的意义分析基础之上,这的确与以社会契约论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文明有很大的不同。
我们善于由物及情,进入意义世界,正如陆机在《文赋》里所讲,“尊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由此,时间世界与意义世界,构成了《1840年以来的中国》的基本线索,前者是表,后者是里,前者为纹路,后者为血肉。全书看似由时间世界铺展开,其实作者是要在时间里安放意义,建立中国历史哲学的意义坐标。
于是,就有了第二对关键词:普遍与特殊。要建立意义坐标,马上就会遇到一个难题,参照系何在?普遍/特殊能否对应西方/中国?在中国的意义世界里是否可以发现普遍性,还是我们就是特殊性与例外?林林总总的中国学研究,在这个问题上无非几个版本。
一是,“中国就是自成一体的普遍”。所谓的天下体系、历史枢纽观、“涡旋论”,在这个角度是一致的,“我就是我”,我界定普遍,达到普遍,而不是成为外在于我的普遍的一部分。由于是意义世界,因此,普遍/特殊与现实国力可以无关。我们看《清帝逊位诏书》就可以发现,现实与力量已经如此不堪,但文化与价值的骄傲仍在。
二是,“中国只是特殊,但无需融入普遍”。新文化运动中的很多传统文化辩护者既看到了某种外在于我、声势浩大的“潮流”,但不认为改变与融入就是一种必要。
三是,“中国是一种需要融入普遍的特殊”。王人博先生的思考非常有意思,他其实是在发问:如果真有普遍/特殊,就不该有西方/中国,因为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都是对普遍本身的割裂,都是一种特殊,只有中国本身能够体现普遍,而这种普遍又是为包括中国在内的每一个特殊所体现,普遍才成为普遍,特殊也才有意义。
正所谓,“我思维着普遍的世界思维”,才是真正的普遍。由此,我们没有必要执拗于哲学上的二分法,因为作者在书中告诉我们:如何让普遍在特殊中真正体现出来,一草一木也能投射万千世界;如何让特殊真正与普遍圆融自洽,互相亲近,才是实践的大课题。
对于今天的现实人类生活和变动的世界秩序,这一哲学思考无疑具有重要意义。进而,如果说西方/中国的二分其实是一种特殊与另一种特殊的划分,而非普遍与特殊的划分,那么圆融之途是否可能,以及何在?
这就需要我们分析这两种“特殊”究竟是什么,由此可以引出第三对关键词:道义与功利。在书的序言部分,王人博先生贡献了一个观察两种“特殊”的很有意思的视角:力量因素与价值因素。中国因为力量的弱小而无法维系价值的再生产,不得不审视一个他者的价值体系。或许我们可以沿着这个思路进一步归结,其实力量本身也是意义世界的一部分,而不纯然是时间世界的现象。
西方力量的背后是功利主义哲学的支配,由霍布斯奠定根基,伴随欧洲文明一系列近代大事件而进入时间世界进而书写现实时间。法兰克福学派传人霍耐特曾经说,欧美文明的现代演进可以归结为两种价值观:斗争形成秩序与团结形成秩序。前者就是以实力主义为代表的社会功利主义。
而中国的意义世界里虽然也有所谓推崇“霸道”的法家思想,但毕竟更有丰沛的儒家道义哲学作为支撑。道义不崇外在实力,而讲心灵秩序,所谓董仲舒说的“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道义是多元而一体,情理法交融,形成关系性伦理和互惠性人格(例如“给面子”)。
实力是整齐而率一,最终对外形成基辛格所言的“均势的条约体系”,在内形成由强制力保障的“法治国”传统。但道义也有可能坚持朱子的“以理抗势”,从而落入空洞与被歪曲。实力也有可能因博弈、对峙而形成世俗的宪法文明。
1840年以来的中国,在意义世界里,直到今天,我们还在纠结于“道义与实力之间”。那么,何者能够胜出,多元价值观如何对话与安放在一个政治共同体里,这是现代宪法的最大课题,用我的话说就是,“开放的宪法如何融贯的实施”是中国宪法实施的真正基础理论。
但这更是一个价值哲学的千古难题。罗尔斯后期的政治自由主义退守到“重叠共识”与“公共理性商谈”,德沃金则提出“价值的一体性”,柏林更悲观地认为“价值的内战”绝无避免之可能。但中国的历史哲学似乎都不主张上述理论,这就要看我们如何认识时间与价值的关系。
由此可以从《1840年以来的中国》中提炼出第四个关键词:直线与绵延。我们一般认为,西方的历史哲学有基督教文明背景下的进化论和线性历史观,但线性观更体现在西方人理解价值的直面相逢和一次性决断。西方价值哲学总是试图跳脱开具体的历史起伏来一次性解决价值的序列问题,20世纪分析哲学对于价值问题进行纯粹脱离历史的概念分析就是典范。
所谓的“元伦理学”就认为,价值问题就是概念分析问题,只要在概念使用上做到清晰,价值问题就可以解决。然而,王人博先生研究中国多部宪法文件的几篇论文则启发我们,中国人对待价值问题很少在终极意义上来讨论,相反地,呈现出的是日本学者和田清所讲的“波纹式循环发生”现象:
中国人总是基于历史的机锋和具体处境,通过价值与具体历史条件的相符合、相匹配,来接纳和排序价值。只有这样,我们也才能理解“富强”为何成为历部宪法确定的第一个国家目标,也才能理解为什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会在1993年写入宪法。
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历史哲学里的实用主义和生存主义,呈现出“绵延”,而不是“直线”的价值观:“绵延”允许起伏,但不会断裂;允许高低错落,但不会彼此抵消。“绵延”是在具体历史时间里此消彼长,相印成趣,看似方向不同,但整体又连成一片——它不是效力等级森严的价值金字塔,而是阴阳流转、相反相生的太极图,包含着生存的智慧。
《1840年以来的中国》是一部中国法治的历史哲学。它没有进行抽象的哲学建构,它的贡献恰好就在于不予以抽象建构,因为,诚如雅斯贝尔斯所言,哲学不能教授,只能唤醒。《1840年以来的中国》试图唤醒的,正是研究者的主体意识和由此在历史过往中维系的思想尊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