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兰·霍米尼】不自由
不自由
作者:亚兰·霍米尼 著 吴万伟 译
来源:译者授权儒家网发布
将不自由作为新基础之一来谈论似乎有些怪异。为什么不是自由?毕竟,自由是我们最珍视的政治理想之一。自由是激励人们行动和革命的东西。战争,无论是冷战还是热战都是为自由而战。人们为了自由甚至愿意甘冒丧失性命的危险,无论是摆脱警察暴力还是拒绝接种新冠疫苗的自由。我们可能认为在西方政治思想传统中,自由理想是最根本的基础。
但是,自由也是引起争议的理想和危险的理想,恰恰就是因为它得到人们如此珍视。比如,自由被某些人看作为是文明的区别性特征。它是我们有而他们没有的东西,是西方区别于世界其他地方的标志。如果回顾一下乔治·布什(George W. Bush)在9-11袭击之后的发言,“他们憎恨我们的自由,我们的宗教自由,我们的言论自由,我们的投票自由、集会自由和拥有不同意见的自由。”布什有个很好的哲学家伙伴:黑格尔(G. W. F. Hegel),黑格尔在《世界哲学史讲演录》中写到他们,“不知道人类是天生自由的生物,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一点,他们自己也不自由。”在黑格尔看来,更糟糕的是,非洲甚至不是人类历史的组成部分,而是“世界史的自然背景,”因为“奴隶制是基本的法律关系”,“奴隶制的基本原则是人们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自由。”对布什和黑格尔来说,这种缺乏自由赋予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某种合理性。在黑格尔看来,历史就像太阳一样是从东方升起到西方落下。西方已经沿着历史轨迹再往前走了,让世界其他地方文明化也就成了西方的使命。自由是美国人带到中东的东西,是带到越南、菲律宾、墨西哥、南美洲的东西。自由在我们称为西方的内部也是危险的。它成为反疫苗运动和零工经济(gig economy)剥削和反社交媒体公司的标语口号,这些公司天天推出误导人的和带有偏见的各色信息。
因此,就像任何高尚的理想一样,自由也很危险。我们或许将某种自由凌驾于其他所有自由之上,认为它应该不惜付出任何代价也要保护。就拿美国最高法院洛克纳诉纽约州(Lochner v. New York (1905))的裁决为例,法院认定个人签订契约的自由是绝对的,不能受到干涉,即使这样的契约在签订时,雇主和雇员之间的权力极其不平等,工人们被迫在遭受剥削和不安全的条件下工作,并无改变的自由。或许我们认为,我们强迫他人接受我们认定的自由是合理的。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尤其担忧“积极”自由的概念,个体只有在遵照其“真正自我”而行动时才是真正自由的。因为,或许其他人---哲学王、殖民地管理者、共产党官员---比我本人更清楚我的“真正自我”。果真如此,柏林担忧,他们强迫我自由就有了合理性。
如果我们将焦点集中在自由的高尚理想上面,就像泰勒斯一样,抬头仰望天空,我们可能对眼前的各种不自由形式视若无睹。
自由可能误导我们。如果我们将焦点集中在自由的高尚理想上面,就像泰勒斯一样,抬头仰望天空,我们可能对眼前的各种不自由形式视若无睹。不自由是事物的正常状态,它就在我们眼前。工人如果有幸找到工作的话,这工作注定要使其遭到异化和剥削。女性即便有意前往堕胎合法的地方堕胎,高昂的费用和长途跋涉也让这种打算根本实现不了。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群体被赶往贫民窟,如果那些地方变得值得向往之后,他们又因为房租上涨和生活成本高昂而不得不离开。生活有残疾者没有能力享受基本生活设施服务,不得不依靠他人的帮助才能过上比较体面的生活。全世界南方地区还有北方地区越来越多的国家陷入债务危机中,不得不采取一些并非服务于国民的经济政策,而是只能满足跨国公司的短期利益。不自由不仅是常态的,而且是系统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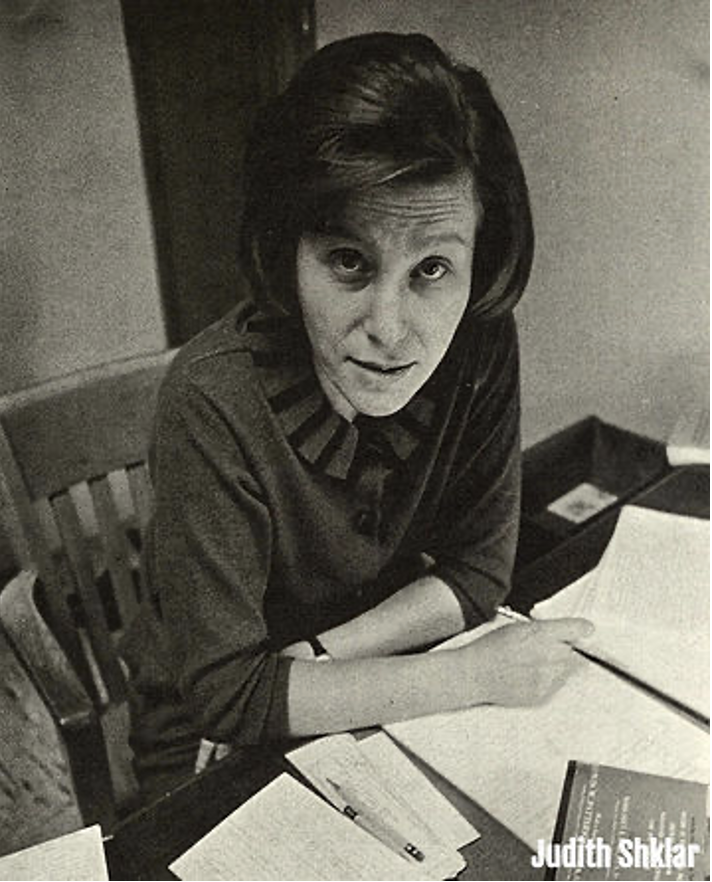
朱迪丝•施克莱(Judith Shklar)
从这个角度看,不自由就是美国政治理论家、哈佛教授朱迪丝•N. 施克莱(Judith Shklar)可能说的“首要经验”。但是,因为它就在我们眼前,我们有一种趋势,将关注焦点转向我们更少了解的目标,如“自由”或者“正义”---然后将消极状态简单地视为我们了解更少且在理论上引起争议的积极状态的缺乏。相反,正如施克莱认为的那样,我们应该将消极状态本身理论化,应该从不自由、不公正、不完美开始。从不自由开始是一种将非理想作为起点的非理想理论。
***
从不自由开始意味着什么呢?我们能够从“解放”这个词以及将解放作为奋斗目标的运动那里获得灵感。“解放”邀请我们提出问题:从哪里获得解放?因此,解放的第一步就是理解我们渴望获得解放的不自由状态。
这种方法也是实用主义方法。在实用主义者看来,当人们遭遇问题时,哲学探索就开始了。问题促使人们探索。不自由是问题,自由是对其做出的反应。从不自由开始意味着我们并不假定自由概念是开端,而是让那个概念由能改变我们不自由的东西来决定。
这样一来,正如约翰·刘易斯(John Lewis)所说,“自由是我们都必须采取的持续不断的行动。”按照约翰·杜威(John Dewey)的观点,实用主义者的第一步是适当刻画出问题的特征,然后将一种感到不轻松自然的状态变成某种更具体之物。因此,不自由体验是什么呢?请让我将不自由再次与不公正做对比。施克莱将不公正的特征描述为产生对冤屈的一种义愤填膺的怒火。对不公正的回应是高喊“这不正确”和“这不公平”。不公正的特征是一种不公平的感受和对不公平的愤怒。不公平的体验从哲学上说具有建设性,它揭露出不公平与冤屈、不正义的联系,由此也将公平、正义、权利联系起来。
不自由不仅仅是一种世界状态,而且还是这个世界影响和塑造我们的思维方式、情感和行为的方式。
相反,我们在说到不自由时,将涉及到一种受到限制和遭受拒绝的体验。有些东西我应该能够做或者想做或者想得到却怎么也得不到。这种体验产生一种挫折感。挫折感是不自由的实验性指南。它要求我们理解造成那种挫折感的原因以及如何才能消除这种情感。当然,并非所有这种体验都是真正的不自由案例,并非所有不自由都有这样的感受。仅仅因为人们有一种受到限制的感受并不意味着这种感受是合理的。正如让·雅各·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说的,人们可能慢慢喜欢上自己的枷锁。这就是说我们未必充分掌握我们不自由的现有状态。我们不得不更深入地考察那些体验以便了解其揭示的内容。我们的不自由本身或许误导我们认为,我们的不自由是与真实面目不同的东西。但是,实验性方面给我们某种用来认清不自由到底是什么的把手。这种体验向我们揭示不自由和能动性之间的联系。不自由不仅仅是一种世界状态,而且还是这个世界影响和塑造我们的思维方式、情感和行为的方式。
不自由和能动性之间的这种联系很重要。从不自由开始将我们的注意力指向我们能够用来让自己变得更自由些的能动性工具。这些工具或许在理想自由的画面中并没有存身之地,因为这些在那种地方有什么用呢?比如,我们可能认为在理想的自由社会,愤怒就没有存身之地,因为没有让你感到愤怒的东西。但是,对限制我们自由的体制和机构的愤怒正是进行政治活动和政治变革的重要动机。因此,类似团结之类也是抵抗不自由的工具,如果我们的焦点集中在自由理想上,它们就不可能出现在画面中。团结是一种将种种不自由---我们遭遇的不自由和并没有直接遭遇的不自由联系起来的手段。
因此,如果不自由体验是挫折感,那不自由是什么?当然,不自由可呈现为多种具体形式,从奴隶制到威权主义到以群体为基础的压迫和支配,再到意识形态虚假意识。但是,在最笼统的意义上,我们能够说不自由是施事行动潜能及其体验的社会引起的系统性贫瘠无能。
不自由是施事行动潜能及其体验的社会引起的系统性贫瘠无能。
不自由不是生活中天生的不可能性问题,如我在没有外力协助情况下飞不起来的无能。它是社会引起的,因为我们与其他人的社会关系造成的无能。我心里想的并非和别人在一起生活造成的种种微小不便,这些限制我们都能很容易克服。相反,最深层的不自由是系统性的,它藏在塑造我们生活和机会的基本社会制度中---我们谋生所依靠的经济制度,决定我们相互之间地位的父权制和帝国权力。
我区分了施事潜能和实施那些潜能的活动用以阐明不自由的不同形式。我们的施事潜能的实施可能在若干方面变得贫瘠无能。最简单的是强制性:动用权力阻止我们做某些事,如因为被捕或被关进监狱,或因为边界和高墙。但是,施事能力变得无效也存在其他的、更复杂的形式。
能动性的实施要求资源。有效思考和行动要求时间和空间;正如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所说,“自己的房间”。它要求物质支持---金钱、身体、书籍、食物。这些资源可能从我们身边夺走,或者被囤积起来供他人所用。我们可能丧失这些东西,从而无条件做自己想做或需要做的事。
或者动员起别人的能动性来挫败我们的能动性。殖民地管理者使用“分而治之”的策略让不同族群相互残杀。当地族群被给予某些特权和权力来支持当地殖民政府,形成“买办”阶级,他们以牺牲殖民地其他族群的利益为代价获得物质利益。比如在殖民地时期的印度北部,本地统治者柴明达尔(the Zamindars)---被东印度公司授权拥有土地所有权,他们反过来代表公司征收地租。
父权制区分“好女人”和“坏女人”(“好男人”和“坏男人”)如果你遵循性别法则,你将不断进步。但是,如果破坏法则,成为假小子或娘娘腔的男人(camp man),或者依靠改变性别或成为酷儿---你将不得不接受惩罚。资本主义让我们陷入争夺有限资源的激烈竞争。岗位和升职机会只有这么多,我们都得为之争夺。(撇开“移民抢走了我们的所有工作”的事实不谈)。还有比姆拉奥·拉姆齐·阿姆倍加尔(B. R. Ambedkar)所说的分级不平等。等级差异体系很少是简单地一分为二,它们往往有很多层级。为维持现状,每个层级都有动机竭力踩他们下面的人。

比姆拉奥·拉姆齐·阿姆倍加尔
等级差异体系和压迫结构能够限制我们发挥能动性,使其失效。但是,这些制度的影响更为深刻。它们依靠塑造潜能采取的形式而且破坏它们令我们的施事潜能变得贫瘠。比如,我们都拥有希望和梦想,但资本主义将那些希望和梦想均塑造成为个人成就方面的梦想。我们的希望是自己的成功,是功成名就、飞黄腾达。连同资本主义产生的激烈竞争,这意味着实现我们的希望很可能是以牺牲他人为代价的,或者踩在别人的背上取得成功。集体希望受到打击,或者正如法国作家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注意到的那样,这是一种我自己也体验过的感受---在白人至上主义横行下的有色人种逐渐觉得,他们能做的最好之事是成为白人。这是包括肤色歧视、肤色主义(colourism)在内的众多现象的理由---在种族或民族群体中,肤色浅的人比肤色深的人更受欢迎---还有医疗干预措施如漂白皮肤或割双眼皮手术。这些希望和欲望是生活所在的社会机构(资本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塑造出来的产物。
有些施事潜能可能彻底遭到破坏。就拿想象力潜能为例,想想我们可能严肃地想象替代资本主义的其他选择吗?正如马克·费舍尔(Mark Fisher)的名言所说,想象世界末日也比想象资本主义的末日更容易些。或者拿因为个人意识不断遭受攻击而引发的彻底焦虑、恐惧和自我怀疑为例,这些都是种族主义、厌女症、和其他形式压迫的地方性流行性效应罢了。这样的焦虑破坏人的自我决定潜能、说出自己想法的潜能、独立思考的潜能,而所有这些都是政治行动和政治变革必不可少的东西。这种贫困不仅仅限于受压迫者,压迫者同样也不自由。查尔斯·赖特·米尔斯(Charles Mills)等人所说的“白人无知”正是这种贫困---自我设定的无能,没办法完全遭遇自己在白人至上主义机构中的角色。这是对个人自我认知潜能的破坏。同样,享受特权者可能缺乏对遭受痛苦者的同情心。这是其惺惺相惜感同身受潜能的局限性。
***
因此,不自由是由外在社会限制和内在能动性潜能塑造构成的,前者限制能动性潜能的实施,后者由社会结构促成。但是,我们的能动性是我们用来改变现有社会结构和构建新结构之物。因此,不自由在两个层次上切入的事实提出了如下可能性:让我们不自由的社会条件(在第一个意义上)如此深刻地塑造和破坏了我们的能动性(第二个意义上),以至于我们不能改变那些条件。不自由或许造成一种恶性循环。社会条件限制我们的能动性,这反过来让社会条件更加根深蒂固、牢不可破。我们能称其为不自由问题:如果我们因为身不由己陷入的社会条件而落入不自由的境地,要改变那些条件需要行使我们的自由,那么,我们好像必须首先是自由的,才能变得自由。
我们如何应对这个不自由问题?这个问题很困难,本文现在难以回答。它涉及到更深入的调查,不自由的社会结构究竟如何塑造和限制了我们的能动性。解决该问题的办法之一是让不自由者相信他人,即那些已经自由的人。但是,这似乎要求理论性解决办法,付出的代价是强化产生该问题的同一个动态结构:那些自由的人将“自由”带给不自由的人。
我们将焦点集中在不自由的动力学上能在不求助任何自由理想的情况下实现大部分目标。
另外一条道路或许可以在集体行动的可能性中发现:一起努力工作以便理解集体不自由的条件,一起努力从内部摧毁这些条件。这里,我们的希望不是将他人当作救世主,而是将他人当作志同道合的同志。我们依赖他们,同时他们也依赖我们。这是团结之路、抵抗之路也是集体改造之路。
我们将焦点集中在不自由的动力学上能在不求助任何自由理想的情况下实现大部分目标。这样的哲学探索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生活的不完美状况。从那里,我们或许能从内在的不自由转向不同的自由理想。带着这种理解,我们或许能够行动起来让我们的生活条件变得更好一些,包括每个人在内,一个人都不拉下。
作者简介:
亚兰·霍米尼(Yarran Hominh),巴德学院哲学副教授。在巴德之前,他曾经在达特茅斯学院哲学系讲师和文科中心博士后研究员。研究兴趣是道德心理学和社会哲学政治哲学的交叉地带,利用全球实用主义传统,尤其是体现在约翰·杜威(John Dewey)、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和比姆拉奥·拉姆齐·阿姆倍加尔(B. R. Ambedkar)等人身上体现的传统,以及其他思想和实践传统。
译自:"Unfreedom": An Essay by Yarran Hominh From The Philosopher, vol. 110, no. 2 ("The New Basics: Society")
https://www.thephilosopher1923.org/post/unfreedom
本文得到作者的授权和帮助,特此致谢。——译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