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怀宏 赵占居】将无同?岂无异?——先儒论人性的共同性与差别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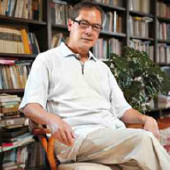 |
何怀宏作者简介:何怀宏,男,西历一九五四年生,江西樟树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著有:《契约伦理与社会正义──罗尔斯正义论中的历史与理性》,《良心论──传统良知的社会转化》,《世袭社会及其解体──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代》,《底线伦理》,《选举社会及其终结──秦汉至晚清历史的一种社会学阐释》,《道德·上帝与人》,《新纲常:探讨中国社会的道德根基》等。 |
将无同?岂无异?——先儒论人性的共同性与差别性
作者:何怀宏 赵占居
来源:《孔子研究》2023年第2期
摘 要:人性显示出各种共性,也包含着各种差别性,且往往难分难解,值得仔细分析和梳理。先儒在春秋战国时代,对人性就有丰富深入的探讨,但以论人的共同性为主。孔子“性近习远”之说,预示了人性论探讨的基本方向和广阔空间。孟子所持的性善论,相当充分地发掘了人心向善的资源。荀子所持的性恶论,从社会制度着眼,也是积极主张人努力向善,化性起伪。汉至唐的儒家则更重视人的差别性,认为性有品级和等差。而纵览这些论述,可以发现先儒所论人的同异中,一个很重要的差别性分类是少数圣贤(包括“希圣希贤者”)和多数民众的差异。这也构成了传统道德两分的一种人性论基础。
作者简介:何怀宏,郑州大学哲学学院特聘首席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伦理学、人生哲学、社会史。赵占居,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伦理学、心灵哲学。
中国古人对人性讨论甚多,众说纷纭,现尝试做一梳理,拟以人的共同性和差别性为中心线索,范围主要限定在儒家的思想。但本文不会论及所举思想家人性论的全部,而是集中于人的共同性和差别性的部分。在人的共同性中自然主要是讨论人与其他动物相区别而非相联系的共性;在差别性中,则主要讨论群体之间的殊性而非个人之间的殊性。
世界充满着差异,但也显示着共性。所以我们可以做各种分析和归类。差异是比较显明的,共性则还需要一些抽象。“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但它们是“叶子”,乃至于是某一棵树,甚至某一种树的叶子又是共同的。我们其实都是在差异中谈共性,在共性中谈差异。我们谈人的特有共性往往是在人与其他动物的差别中定义的。我们谈人类内部的种种群体和个人差异,又是在人的共性的框架内谈论的。但我们不必动辄“一言以概之”,也不必“完全不概括”。分析可能还是基础性的,首先要弄清一个事物是什么,但我们又要注意它和其他事物千丝万缕的联系和由这些联系建立起来的某些共性。
就一个具体的人来说,他首先不是一个机器,是一个碳基的存在而非硅基的存在,具有一种有机的生命性;然后他是一个哺乳类或灵长类动物,和其他的同类动物一样具有某种动物性;其次他还是一个人,和其他人一样具有一种共同的人性。而他同时还属于某个性别,某个种族,某个阶层或阶级,还具有某个国家的国民性或民族性,以及某种职业性或地域性等,最后他还拥有他自己的个性,那不仅是通过一种人际比较形成的,还要根据一个人前后连贯的行为来确定。这里的种种属性看来都是根据范围而定的,而我们对这些属性往往会有不同的权重和关注。在此我们关注的是共同的人性和群体之间的差别性,这也是先儒所论最多的。
一
孔子在《论语》中论人性只有一句,却意味深长:“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孔子谈性只有这一句也说明了子贡说的是对的:“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孔子很少谈性,也很少谈天道,那么,这是否说明孔子不重视人性的问题呢?并不一定。孔子显然是很重视天的,在他心里,“巍巍乎,唯天为大”(《论语·泰伯》),但他在《论语》中说“天”甚多,却竟无一言谈到“天道”。他很少谈“性”与“天道”的原因可能是同样的,即他认为它们虽然很重要,但与其玄妙莫测地谈“性”与“天道”,不如更切实地言之。
但就这一“性近习远”的思想已经预示了日后儒家讨论人性的基本方向,为后来者的探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孔子说“性相近也”,亦即肯定人有基本相同的共性,同时又说“习相远也”,则是肯定人们后来的习性会差别很大。这句话还涉及先天与后天的问题,即这相近应该是在人出生伊始的时候,相距遥远却是在后来的时候,甚至可以从人整个的一生来看,是从“人之初”到“人之终”。那么,这里的“性”是指什么?“习”又是指什么呢?按照后来儒者经过千百年理解达成的基本共识,也是沉淀在普及启蒙读本《三字经》中的共识,这一“性”的意谓看来是指“人之初”的“本性”,也就是说是指人出生时候的人性。这一人性我们通常也可以称作人的自然本性,或者说“天性”“天赋本性”。而“习”则是指人后天的,天赋与环境、遗传与经验互动形成的“社会本性”,或者说“习性”,即后天习得的属性。这种“习性”也可以说还是属于人性,虽然是第二位的人性,是有差别,而且差别甚大的人性。这些差异明显地表现于人类群体与群体、个体与个体之间,是人类的内部差异。而第一位的自然本性则是属于人类外部的差异,也就是人和其他动物之间的差异,比如人特有的精神和意识;也包括由人和动物的共性改变和升华了的一些共性,比如某些情感和意欲。这种“人禽之别”的差异同时也就是人类的共性,后来发展出来的千差万别的习性则是人类的殊性。
所以说,孔子这一句话已经涉及人性理论的数个基本主题:本性与习性、自然与社会、先天与后天、共性与殊性。本文将主要就传统儒家所言来讨论人的共性与殊性,或者说人的共同性和差别性。孔子没有怎么形而上学地谈性,但在对人、民、知、仁、君子、小人等诸多问题的言说中,已经有丰富的对人的共性与殊性的言说。
在人的本性或共性方面,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论语·里仁》),说的就是人的自然“本性”。但人们对待它们的态度却有所不同,君子对富贵,如果“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论语·里仁》);对贫贱,如果“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这“不处”和“不去”就是体现了学习和教化之功的“习性”。当然,这学习和教化也不完全是单独的后天因素在起作用,其中的先天因素也会结合进来起作用。所以,孔子只是谨慎地说“性相近也”,还没有直接说“性相同也”,这或许是因为一些后来的差异也在先天就有其天赋的种子。但为了明确概括和对比起见,说“同”亦无不可,只是记住“同”总不会全同。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原则也是着眼于人的共性,并根据人格平等的原则提出待人的基本和普遍的态度。孔子的弟子子贡对这一忠恕原则的另一表述是“我不欲人之加诸我者,吾亦欲无加诸人”(《论语·公冶长》)。也同样是在表述人的共性,并要对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人一视同仁地对待和宽容。还有进一步的如“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也是对普遍的人而言。他在马厩被焚之后只问人伤了没有,而没有问马,则是将人的生命归于一类而置于动物之上。孔子的“有教无类”的教育原则是认为人是普遍可以被教化的。而“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则说明可以向任何人学习。但他也并不只是主张向外用力,“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点出了人心中共有的一点善念。
孔子论人的习性或差别性可能更多更丰富,这大概是因为孔子极其重视人的学习和教育,《论语》首句即“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而学习的目的则不仅是学文求知,更要在道德上努力向圣贤看齐。他始终勉励人要努力向上向善,但他似乎也知道最后还是会有“人之不齐”。由《论语》可见,孔子有许多话是对君子与小人做鲜明对比,诸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成人之美,而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等等。这些对比多不是地位、身份上的,而首先是道德上的。
这里比较有争议的可能是孔子对民众的认识与态度。一方面,他主张仁政,主张统治者要安民、保民、养民、爱民、“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但另一方面又认为民众往往是不愿自己立志向学的。孔子的教育一方面主张“有教无类”,不设门槛,无论何人,不管他是贵族还是平民,只要肯学,都可以来学;但另一方面,基于他对人性多数与少数的认识,他实际上又认为愿意来学或有能力学成的人不会太多。所以他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论语·季氏》)但他否定自己是“生而知之者”,而只是“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他还说“唯上知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但他并没有说“上知”就不需要学习,也没有说“下愚”就不能被影响和教化,他的意思也许只是说无论怎样教化和改善,他们不可能转移和脱离这样两个大类。所以他实际上应是主张适用于君子和民众的两种道德并行,君子追求“希圣希贤”“内圣外王”的高尚道德,而民众则也能和君子共有“人伦纲常”和“亲亲孝悌”的普遍道德。“修身齐家”是人人都应该努力做到的,但“治国平天下”则只有少数人才能做到。在社会和政治上应该将有道德和学问的贤人推举到上层,对他们提出更高的道德要求,这样,就能示范和引领整个社会的道德风尚。这也就是:“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论语·泰伯》)“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论语·学而》)这一思想也是源远流长,《诗经·小雅·大东》中就有言:“君子所履,小人所视。”
最具争议的可能是孔子这样一句话:“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这里的“由之”是指在行为上“遵循”,对“不可”则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不让”,即禁止民众知道,实行愚民政策;但还有一种理解应该是“不能”,即不指望他们都能够立志向学且理解,都能知晓行为规则后面的“道”,他们能在行动中养成这样的道德行为和习惯就可以了。孔子这里说的意思应该是第二种含义。朱熹《论语集注》对这句话的解释是:“民可使之由于是理之当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这也可以用孔子整理的经典中的两段话来印证。《诗经》中有一句话“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诗经·大雅·烝民》)。《周易·系辞上传》中也有一段话:“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亦即让民众在行动中遵守道德法则,跟随道德榜样,即便他们并不清楚这后面的“道”,不能知晓这“懿德”和原则后面的根据。后来的孟子也有类似的话:“行之而不着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孟子·尽心上》)
老子《道德经》中则含有第一种解释的意思,即不仅是不指望,甚至是希望民众不要知道得太多而产生太多的欲望,如:“是以圣人之治……常使民无知无欲。”(《道德经》第三章)“绝圣弃智,民利百倍……见素抱朴,少思寡欲。”(《道德经》第十九章)“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道德经》第六十五章)但统治者首先要自己做到少知寡欲,清静无为:“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道德经》第五十七章)
二
孟子论性不仅强调人的共性,而且强调这共性就是善性。但是,他看来也承认人的生理共性、身体共性,且用这种共性引出人心的共性、道德的共性:“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孟子·告子上》)人均是同类,既然同类,怎么会没有共性,“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圣人,与我同类者”(《孟子·告子上》)。如果没有这种善性,那就不属于人类了。这种善性也就是“仁义礼智”,尤其是其中的“仁之端”——恻隐之心。“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他在另外一处说这“四心”没有提“端”,但提“端”应该是一个更加贴切的说法。“端”也就是源头,就是人出生伊始已经具有的一种可能性;它还隐而未发,但已经普遍地潜存于每一个人的心里,即“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而这种共性也就是人与动物的首要差别,也就是表现于“人禽之别”的殊性。纲常中忠孝最重要,“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人如果横逆狂暴,“则与禽兽奚择哉”?人如果不存清明之气,“则其违禽兽不远矣”。这种来自“人禽之别”的共性,是宝贵的,又是稀少的:“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离娄下》)在这句话里同时显示出人的共同性和差别性。
亦即这最后一句话又把我们引向了人的差异性,而且还是少数君子与众多民众的差异。既然性善其实只是人禽之别的“几希”,是很容易放逸而去的善念,那么,存养、推扩也就相当不易,从而也就会有后来种种的“习相远”。但孟子论人性的确主要还是以论其共性为主,而以论其殊性为辅。公都子问他:“钧是人也,或为大人,或为小人,何也?”孟子回答说:“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公都子还继续追问人何以会或从其大体或从其小体,孟子答道:“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孟子·告子上》)也就是说,差别在于是不是能思考和反省自身。他重视的是心灵,所以要“尽心”以“知性”而“知天”,要努力“求放逸之心”。但“尽心”虽然是向所有人开放,可能还是只有少数人能够通过持久的“尽心”而知性知天。这里又一次出现士君子与民众的差别:“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孟子·梁惠王上》)孟子学说一个重要的内容是义利之辨。对于民众,孟子并不要求他们放弃对利益和恒产的追求,而且主张为民制产。他甚至也不奢望君主放弃自己的快乐和利益,只是希望他们不要“独乐乐”,而是“众乐乐”,“与民同乐”、与民共利。但是,对士君子来说,他却希望他们严守义利之辨,要求他们在必要的时候舍生取义。他为君子设立了一个独立自足的至高道德理想人格,这种理想人格不是从外在的功绩判断:“广土众民,君子欲之,所乐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乐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虽大行不加焉,虽穷居不损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孟子·尽心上》)孟子还从社会分工的角度谈道:“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孟子·滕文公上》)并认为这一分工是一个普遍的规则:“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孟子·滕文公上》)
三
孟子为什么要大力提倡性善论,也是有时代和个人际遇的关系,其时天下已然大乱,七国争雄,盛行的是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而大乱或又还是初起,拯救还有希望,当时也还有游说国君的机会,所以,他不仅希望君子存心养性,也希望唤起君主的一点善念。
而荀子为什么提倡性恶论,也可能有其时代的关系,尤其到他晚年,当时天下道德已经崩解,他没有出去游说国君的机会和意愿,暮年只是做一个兰陵令维持自己的生计而潜心著述。他看来是更寄望于制度的长期建设而非立即唤醒人的心性,而制度的建设倒是不妨从承认人的恶开始。他主张人们化性起伪,改恶从善,认为所有人,包括圣愚、天子庶人,其人性都是共同的,但这共有之“性”却不是善,而是恶:“凡人有所一同: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目辨白黑美恶,耳辨声音清浊,口辨酸咸甘苦,鼻辨芬芳腥臊,骨体肤理辨寒暑疾养,是又人之所常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荀子·荣辱》)孟子是用人的感官欲望打比喻来说明人心的共同善性,而荀子直认这普遍欲望就是人性之“恶”,而这“欲望”还可能是无上限、无休止的。“夫贵为天子,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人之情,食欲有刍豢,衣欲有文绣,行欲有舆马,又欲夫余财蓄积之富也,然而穷年累世不知不足,是人之情也。”(《荀子·荣辱》)
性恶论的思想渊源有自,因为荀子更重视的是人的身体,而不是像孟子所重视的是人的心灵。人有身就会有欲望,这首先是物欲,因为他要靠物质的资料才能活下去。但人似乎又和动物不一样,不会“食饱即安”,他还要储存,还要聚敛,还要用物质财富换取其他的东西,诸如地位、权力和名望。在荀子看来,这“性”是所有人天生就有的,谁都要摊到一份,谁都不可能拒绝,否则就无以为“生”了:“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荀子·性恶》)荀子虽称欲望为“恶”,但也不完全否定人的欲望,因为它是来自人不可逃避的人性。所以他说:“故虽为守门,欲不可去,性之具也。虽为天子,欲不可尽。”(《荀子·正名》)
人虽性恶,却也有化性起伪的能力,这是不是也是所有人共同具有的呢?荀子看来也是肯定这一点的。他同意“涂之人可以为禹”。说“凡禹之所以为禹者,以其为仁义法正也。然则仁义法正有可知可能之理。然而涂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皆有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然则其可以为禹明矣。”(《荀子·性恶》)这种普遍的“恶之华”是怎样产生的呢?是因为人皆有可以知道仁义法正的素质。但荀子说,无论如何,这种能力却不是来自普遍的人性。“凡礼义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荀子·性恶》)荀子如此区分“性”与“伪”:“若夫目好色,耳好听,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后生之者也。夫感而不能然,必且待事而后然者,谓之生于伪。是性伪之所生,其不同之征也。”(《荀子·性恶》)
圣人之所以要起而作伪,就还是要归到人心的一种善愿。荀子大致描述了这一“性—情—虑—伪”的过程:“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应,不事而自然谓之性;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情然而心为之择谓之虑;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伪。”(《荀子·正名》)圣人的这种善愿正是因为看到了人性普遍恶的事实,才试图起而化性。“凡人之欲为善者,为性恶也。”“夫薄愿厚,恶愿美,狭愿广,贫愿富,贱愿贵,苟无之中者,必求于外。故富而不愿财,贵而不愿势,苟有之中者,必不及于外。用此观之,人之欲为善者,为性恶也。”(《荀子·性恶》)俗话说也就是缺什么补什么,但为什么人们不接受欲望这一事实而一定要补善呢?善愿又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其实还有待说明。人性有恶的事实并不是人向善的原因和动力,向善还得另有动因。但无论如何,我们可以看到,荀子和孟子一样都是鼓励人积极有为和努力向善的,孟子是说你心中本来就有善端,你必须将其发扬光大才能成就为有别于动物的好人;而荀子是说,你有身即有物欲,就有恶性,你就必须有所作为摈弃这恶性才能成为善人。孟子重在内心扬善,荀子重在行为克恶。而善恶的可能性或者说“端”其实在初始的人那里都存在,且如果一定要给出究竟是人性善还是人性恶的结论,大概还是应当赞成性善论,因为在人的初始本性中,善端还是超过恶端那么一点点的。
无论如何,在荀子那里,论及人的差别性,他同样认为在圣人与民众之间、君子和小人之间,还是会存在差异,甚至是巨大的差距,虽然在荀子看来,这不是“性”的差距,而是“伪”的差距,是“积”的差距。“圣人者,道之极也。故学者固学为圣人也,非特学为无方之民也。”(《荀子·礼论》)“君子道其常,而小人道其怪。”(《荀子·荣辱》)“君子,小人之反也。君子大心则敬天而道,小心则畏义而节;知则明通而类,愚则端悫而法;见由则恭而止,见闭则敬而齐;喜则和而理,忧则静而理;通则文而明,穷则约而详。小人则不然,大心则慢而暴,小心则淫而倾;知则攫盗而渐,愚则毒贼而乱;见由则兑而倨,见闭则怨而险;喜则轻而翾,忧则挫而慑;通则骄而偏,穷则弃而儑。”(《荀子·不苟》)这种圣人与众人的差别看来还主要是一个能力的问题,尤其是道德的认知能力。他在回答“涂之人是否均可以为禹”的问题时,区分了“可以为”和“可以成”的不同:谁都可以立志且努力为禹,但能不能成禹却“未必然”,然而即便“不能成”,也无害于“可以为”。几乎没有人走遍天下,亦无损于我们说人有“遍行天下”的能力。是不是所有人都能像荀子所说的“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皆有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的能力呢?人们的道德认知能力和意志能力还是有差距的,荀子也承认:“有圣人之知者,有士君子之知者,有小人之知者,有役夫之知者。”(《荀子·性恶》)
荀子主张人性恶,主要目的还是要建设一个好的政治秩序和道德教化,“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圣王之治、礼义之化,然后皆出于治,合于善也。”(《荀子·性恶》)至于何为好的社会政治制度,荀子谈到了它的目的,他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故古者,列地建国,非以贵诸侯而已;列官职,差爵禄,非以尊大夫而已。”(《荀子·大略》)这种民本主义应该说是儒家的一致意见,即他们赞成一种君主制和等级制,并不是为了君主和尊贵者,而是为了建设一种“为民”“向善”和“归仁”的制度和社会。在上者应该比民众更加克制自己的物质欲望,限制自己的经济利益,“从士以上皆羞利而不与民争业,乐分施而耻积臧;然故民不困财”(《荀子·大略》)。荀子也和孟子一样主张让民制产,让民富裕:“不富无以养民情,不教无以理民性。故家五亩宅,百亩田,务其业而勿夺其时,所以富之也。”(《荀子·大略》)
四
从汉至唐,儒家学者却有一变,多强调性有品级,有差等。这大概是因为汉唐儒较为贴近社会政治,有强烈的社会现实感,既是从差序明显的社会和政治出发,也维护这种差序。而儒家在“外王”层面的思想和制度的发展,也大致是到唐朝就基本完备。以下论董仲舒等,我们也就从他们所论人的差别性开始。
董仲舒有强烈的“正名”或“实名”思想,认为应该“事各顺于名,名各顺于天”(《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名实必须相符,甚至以名责实。用到“性”“善”两名上,在他看来,性就是“生”,或者说是“质”,而“善”应是已经表现为行为和性格的昭然之善:“今世暗于性,言之者不同,胡不试反性之名?性之名非生与?如其生之自然之资,谓之性。”(《春秋繁露·深察名号》)“性者,宜知名矣,无所待而起,生而所自有也。善所自有,则教训已非性也。”(《春秋繁露·实性》)这就像米(善)是出于禾(性),但禾(性)并不是就是米(善),“善出于性,而性不可谓善”(《春秋繁露·实性》)。“性者,天质之朴也;善者,王教之化也。”(《春秋繁露·实性》)所以他的人性论既非性善论,亦非性恶论,而是把人性看作是一种中性之“质”,以后可善可恶,人也必然要分化。所以,董仲舒强调的其实是人后来的差别悬殊的习性。但是,如果一定要给人的本性一个统一的说法,究竟如何名性呢?董仲舒的做法是取其“中”,也可以说取中间的大多数人,既不以“圣人之性”名性,也不以“斗筲之性”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春秋繁露·实性》)。
董仲舒把“性”只是看作一种人出生伊始就有的自然资质,从中可能生长出善,也可能生长出恶,加上后天环境和努力的差别,于是世间就有善人恶人之分,有圣人和大奸之分。但这两种人都是少数,大多数人还是“中人”。这三种人已经预示着一种“性三品论”。而且,董仲舒还倾向于认为世间总会有这三种人,这种状况就像“天不变,道亦不变”一样是不会改变的。不过,我们还可以另外提出两个问题:一是当出生伊始,新生儿是否已经有比重不同的向善或者向恶的资质,这种资质的比重就足以让我们说他们或善或恶?二是说是否所有人都有这样两种资质,他们的善恶资质只是多少的不同,而不是有无的不同,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是否还是可以总体衡量人们的这两种资质究竟哪种为强,从而承认一种性善论或者性恶论?董仲舒看来倒是不否认所有人都潜藏有这样两种资质的,但他不同意孟子把人性中的“善端”就看作“善”,说孟子之所谓的“善”只是将人与禽兽相比,是指“万民之性善于禽兽”;而圣人所说的“善”是“循三纲五纪,通八端之理,忠信而博爱,敦厚而好礼,乃可谓善”(《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如果将人与动物比较,那么,所有人都还是有一种“人禽之别”的共同性,甚至可以说这种共同性是一种善性,但如果将人与人比较,则不能说这种“万民之性”是一种善性:“质于禽兽之性,则万民之性善矣;质于人道之善,则民性弗及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董仲舒又将善恶与天道阴阳的宇宙论联系起来,认为:“身之名取诸天,天两有阴阳之施,身亦两有贪仁之性;天有阴阳禁,身有情欲栣,与天道一也。”“身之有性情也,若天之有阴阳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在这里,他也看到了一种“同”:“天人之际,合二为一。”但无论如何,圣贤和民众的差距还是巨大的。董仲舒还是正名索义,说“民”的意思就是“瞑”,也就是未开悟者,有待教化者。但是否他们全都能被教化,或者能够被教化到什么程度,则还是未定之天。不过,董仲舒坚决主张从“万民”中选拔政治精英而反对世袭制,他的“举贤良三策”开启了让察举制度化的道路。
西汉末,扬雄认为众人与贤人有别,而贤人又和圣人有别。所以人应该努力学习以向上。如果不学,而只是让情欲统治自己,则还是属于动物,知道礼义才能入“人门”。王充也认为:“生而兆见,善恶可察。无分于善恶,可推移者,谓中人也。……夫中人之性,在所习焉,习善而为善,习恶而为恶也。至于极善极恶,非复在习。”(《论衡·本性》)圣人和恶人居于两端,不可推移,但绝大多数人都在中间,可上可下,向上的关键就是学习做人的道理和习染德风良俗。
荀悦也持“性三品说”,他甚至对三种人给出了一个大致的数字:“或曰:善恶皆性也,则法教何施?曰:性虽善,待教而成;性虽恶,待法而消。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其次善恶交争,于是教扶其善,法抑其恶。得施之九品。从教者半,畏刑者四分之三,其不移大数九分之一也。一分之中,又有微移者矣。”(《申鉴·杂言下》)
唐朝韩愈著有《原道》《原性》《原人》等篇,他也是坚持一种“性三品”的观点。而且认为不仅“性”有上、中、下三品,“情”也有上、中、下三品。韩愈写道:“性也者,与生俱生者也;情也者,接于物而生者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为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为情者七。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导而上下也;下焉者,恶焉而已矣。其所以为性者五:曰仁,曰礼,曰信,曰义,曰智。”(《原性》)对三种人在自己的性情中所占的比重,韩愈也有一个大致的估计:“上焉者之于五也,主于一而行于四。中焉者之于五也,一不少有焉,则少反焉,其于四也混。下焉者之于五也,反于一而悖于四。性之于情,视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为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惧,曰爱,曰恶,曰欲。上焉者之于七也,动而处其中。中焉者之于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于七也,亡与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于性,视其品。”(《原性》)
自汉至唐的学者虽然多强调人的差别性,但也看到人的共同性。承认“生之谓性”“生生大德”就是承认“同”,认为人皆有神形、皆有性情也是“认同”。荀悦表达了对古代尚同的一种理想:“大上不异古今,其次不异海内,同天下之志者,其盛德乎!”(《申鉴·杂言下》)韩愈在《原人》中对人的认同和关注不仅跨越国界,甚至延及禽兽。他说:“形于上者谓之天,形于下者谓之地,命于其两间者谓之人。形于上,日月星辰皆天也;形于下,草木山川皆地也;命于其两间,夷狄禽兽皆人也。”他认为这三者中还是有主之者,人就是天地两间生物的主之者,但是人行“主道”的时候绝不能残暴,圣人会“一视而同仁,笃近而举远”。
五
先儒对人的共同性的论述,当然都是比较聚焦于道德。或性善,或性恶,甚至最原始的本性之空白论,都可以说是性一论。而对善恶的来源,也是后来分化的根据,则论说不一。一些学者或以为这是承接了不同的气禀,善是来自人之有心,恶是来自人之有身,人一旦成形(出生)恶也就与生俱来,因为人一旦有身就会有欲望,恶是来自欲望。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情也是恶的来源之一,但另一些学者则否认。至于辨别善恶的“知”的能力,应该是所有人都初备的,不过分量和成色似乎也大有不同。但即便对最愚笨的,也还是要有一种“生生”的人道对待。
在先儒对人的差别性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注意到他们关注的一个最重要的差别,那就是一种多数与少数的差别,即少数圣贤、士君子与多数民众的区分。这种少数和多数的差别似乎是一种模糊的差别,但多少的数额比重又是固定的,多不会变成少,少也不会变成多。这一区分是来自陀思妥耶夫斯基,划分的标准大致是多数比少数人更重视物质生活而非精神生活,更惰于或弱于对公共事务独立地运用自己的理性,也就是说,划分的根据是价值追求和认知能力的不同。这一划分不能等同于某种身份或地位,或者统治阶层和非统治阶层,但在某些社会里又有相当大的重合。在传统中国,通过先是察举后是科举的选举制度,少数和多数之间甚至是可以在制度上定期流动的,上层的少数对下层的多数是开放的,向学和上进的大门是敞开的,基本不限于社会出身,而且结果就是许多士君子来自民间。但无论怎么流动,大门怎样敞开,进门的人又还都会是少数,多数人还是在门外。于是就有了一种实际上的道德双轨制,少数士人“希圣希贤”,并通过科举跻身于社会的上层,但对他们的道德要求也更高;多数民众属于被统治的阶层,他们的道德风俗则主要表现于人伦纲常、亲亲之爱,而并不要求他们向圣贤看齐。这种道德的两分不是独见于古代中国,而是同样流行于域外的传统社会。但是,现代社会终于开启了平等的浩大潮流,正在走向多数的统治或至少以多数的意见和价值诉求为旨归,道德也就必须统一地面向所有人,平等地要求所有人。但这里的确会遇到一个人性的挑战,即如果人性除了共同性也还有差别性的话,那么,普遍的社会道德也就可能是必须就低而不是蹈高。这也可以说是现代“底线伦理”的一种人性论根据。
大略言之,先秦孔子开启了探讨人的共同性与差别性的方向。孟子性善论、荀子性恶论都是更强调人的共同性,且都不同意告子的“性无善恶论”和道家的“性超善恶论”——虽然这两者也承认人的一种共同性。儒家学者都强烈地关注道德,孟荀的理论都可以归在一个普遍的“性善论或性恶论”或“性可善可恶论”的大名号之下。汉至唐的儒家学者的人性论则是更强调人的差别性,他们的理论可以归在“性有差等论”“性有品级论”或者“人有善有恶论”的大名号之下。后来的宋明理学则将人的共性和殊性都放到“性理”的内部,将“性理”分为第一位的、共同的“天地之性”或“义理之性”和第二位的、分殊的“气质之性”,而在王阳明的心学中则归一于“良知”。清儒戴震认为“血气心知之谓性”,比较通融和贴近人身的“血气”,对人们的欲望有一种比较宽容的理解。不过,他们的思想虽然各有侧重,但论述都是异中有同,同中有异,大要既不离普遍地观察人类,也不离社会的层序结构。“将无同,岂无异”不仅适用于他们所论述的对象——人性,也适用于整个儒家思想的客观平衡,乃至于他们各自的论述内容本身。
【上一篇】【杨泽波】儒学发展一主一辅两条线索概览
作者文集更多
- 【何怀宏】君子的人格 12-29
- 【何怀宏 赵占居】将无同?岂无异?——··· 06-07
- 【何怀宏】我们想要怎样的人类文明? 08-11
- 【何怀宏】政治、人文与乡土 ——当代儒··· 07-06
- 【何怀宏】人应该依靠什么样的伦理道德··· 08-08
- 【何怀宏】对新文化运动人的观念的一个··· 10-28
- 【何怀宏】儒学可以在政治上有作为,这··· 07-27
- 【何怀宏】抗议性政治不应成为主流 07-13
- 【新书】何怀宏:谈成功的书多,谈生··· 03-30
- 何怀宏著《新纲常》出版 11-19
微信公众号
儒家网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

微信公众号
儒家网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