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扬】西政七八级非典型学者之:蒋庆同学
西政七八级非典型学者之:蒋庆同学
作者:舒扬
儒家网编者按:此文节选自《我们的1978:西南政法学院纪事》一书,系西政七八级法律本科生舒扬先生所著,南方日报出版社2008年出版。作者舒扬,重庆人,毕业后留校任教。1988年调广州大学工作,曾任广州大学副校长、广州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广州市广播电视大学党委书记、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主要社会职务有:广东法官学院教授,广东省法学会副会长,广州市法学会副会长,广东省文化学会副会长,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立法顾问。此文标题是编者所加,并对原文段落予以重新编排。

蒋庆同学被公认为非典型学者,不是因为他在国家级学术期刊和越来越滥的中文核心期刊上发表了什么文章,也不是因为他被破格提拔过职称,或得过什么“家”,什么“师”的称号,是因为西政七八级的同学,无不认为他才是真正的纯粹的学者。
蒋同学出身于中国上世纪一个非常标准的革命家庭,本人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里呆过,他对现实的界入与关心,程度还是比较深的。
蒋庆与梁治平,还有李庆、于安等都是从贵州贫困生活圈中走进西南政法学院的(当然,相比之下,他们并不是生于贫困之家)。这使人怀疑,法律思想家的贵州兵团有点像前几年中国文坛上的“湘军”和“老陕”部队。
蒋庆除了喜欢带着淡淡的忧伤唱歌,平时表现真的有点懒得发话的味道。大学本科毕业将至,同学们大都在狂热地准备考研究生,蒋庆同学似乎有点身处世外,他淡定地看着“大师培养计划”中可能出现在目录中的那些书。我猜测,他是没有看上哪一个法学专业和某位导师,谁有资格去做他的导师呢?什么专业可以对得上他的口胃呢?
蒋庆毕业时主动选择了留校教书,而且是在法制史教研室,这跟江必新、叶峰、夏勇、何力等的观点比较一致,其他专业和教研室就那么几本书可读,半年下来就没有什么可选可看的了。
法制史教研室则不一样,在它静水流深的学术之海里,再牛的学者也不过像是水面上飘浮的一片稍微宽大一点的落叶。
蒋庆这片叶子不知是从哪里临水的古树上掉下来的。他现在被海内外不少知书识礼的人称为现代新儒学大师。他的文选在台湾、日本、东南亚,包括香港、澳门等地是比较好销的。可以说,蒋庆的名气是出口转内销方才有些红火的。
蒋庆的书,我也在图书馆借阅过,但是,基本上等于没看,因为未真正看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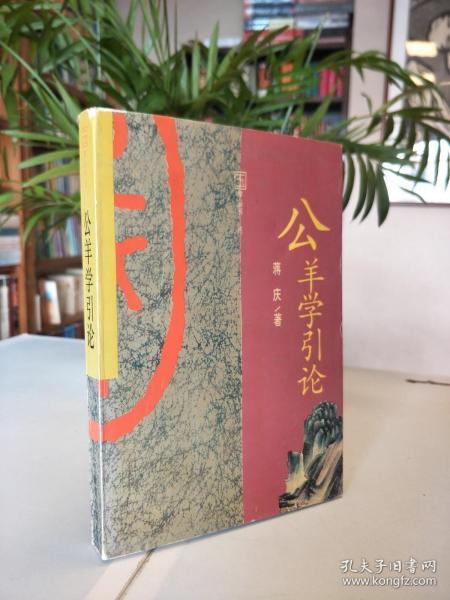
蒋庆著《公羊学引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这是蒋庆先生公开出版的第一部学术著作,亦是成名之作。
不像当学生时蒋庆写的《回到青年马克思》,虽然浅薄幼稚一些,但激情如雷电直击心境,能把我们这些有相同好奇心的人搞得十分亢奋,产生莫名的冲动。
当时领导和老师们对蒋庆是尊重有加但又有些掩饰不住的另眼相待,学校还组织过有理论水平的教师团组轮番与蒋庆谈话聊天,希望纠正他的看法并转变一下他的学术思路和风格,使之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补:蒋庆同学以大字报形式发表此文,尽管在当时受到了学校领导的“善意批评”和“帮助”,但其对于七八级同学的逆向思维所产生的潜移默化影响,可谓且深且远且长……)
蒋庆似乎很执著顽强,虽痛爱着他的学校和老师,但好像更强烈地爱着心中的真理。事后,教师们都说对蒋庆同学的思想转变工作效果不大。既然无力转变一个人的思想,那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完整全面成体系地去成熟自己的思想。
在西南政法学院宽松的意识形态环境下,蒋庆同学更来劲了。似乎他已不认为自己还是位在读的大学生,而是自己建立的思想小王国中的国王、老臣、奴仆、卫士的集合形象。为了把自己这个理想主义的乌托邦弄得美轮美奂,蒋庆同学如饥似渴地读书,把自己搞得来有点像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那副模样。
蒋庆同学在坚持己见、小有积累之后,便有些心绪飞扬,他可能还是有博取更多人关注的动机,专拣当时社会的焦点问题和热门事项发表自己颇为独特的议论。《关于雷锋精神的联想》就是他投向思想的平湖,溅起一个局部的小水花的石头。
记得当时在学生饭堂前的绳子牵出的一溜大字报中,我看到蒋庆的说法,感觉到蒋同学此文又将产生轰动效果,但还是认为这位蒋氏思想家走得快了一些,也偏远了一些。
不久,学校派我去桂林参加当年共青团中央组织的大学生干部夏令营活动。其时,中国青年报的一位主任记者,一看我是从重庆高校来的,就不断向我询问蒋庆的情况,还准备筹划一些能够引起全国青年热议的话题让蒋庆来写、来说。

蒋庆著《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5月版。
我返校后把这个情况给蒋庆讲了,他很是兴奋,连连问怎么与中国青年报取得联系。我看这时的蒋庆,真有点像要整装出阵,与大风车来一番激战的唐诘·诃德。可惜,蒋庆的大刀长矛还没有认真挥舞起来,那时从上到下的思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过了蜜月期,一下子进入理论潮汛的尾声。
试想,如果蒋庆当年给中国青年报有意无意地捣鼓成为宣传的某种需要,今天我们就无法长考和细读蒋庆了。
蒋庆的成功,多半取决于他早就比较主动地放弃对现实的急功近利式的关怀。
他后来迷上了儒学,在儒家经典中,他不知温饱饥寒为何物地咬文嚼字地过日子。尤其是他那令人羡慕,叫绝称奇的“重庆市三好优秀学生标兵”获得者、同窗同学、后来又发展成为妻子的吴芳龄,她几乎是为了蒋庆的舒适安好而宁可放弃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一切已属的光荣与梦想,让蒋庆兄几十年都像生活在一个吴芳龄人造的幼儿园里面搞他的什么文化与思想。
蒋庆是极为幸福、走运的。他只管翱翔在他的理想天国,耕作在他绿色的信仰世界。

蒋庆著《再论政治儒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我看他的思想极为沉重,这是因为广博丰富的缘故。而他的心灵绝对没有信仰之外的任何负担,蒋庆是个寡笑少言的思想者,但他内心里好像有许许多多欢笑和傻笑、怪笑着的孩子与他做伴,在以顽童之心仰望无限的星空之后,再以孩童般的纯粹摆弄现实社会的问题。
唯一见到他比较慌忙和吃力的事情,是邮差的大声吆喝打破了他家内的宁静,催他从楼上快点下来领取并自个儿搬运北京、上海、台湾、新加坡等地古籍书店打包成捆地给他寄来的读物和资料。
这时的蒋庆,一般会像饥民看到赈灾的米粮一样高兴得两眼放光,至今让我这样的邻居仍挥之不去的印象是,蒋庆穿着汗湿的白背心,踩着一对稍显偏大的塑料凉鞋,穿着一个军队人士中通行的大裆短棉布裤,高兴而吃力地把打成捆的书包往自家屋里搬。
旁人要出手帮忙,他会坚定地谢绝,好像这些书是开过光的佛像,别人沾手,灵气就跑到另一个地方去了。蒋庆爱书迷书,让他在现实世界经常显得有一种不适应的拘束。

说明:《政治儒学评论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9月出版。蒋庆先生“政治儒学”思想,不仅是对自由主义西化派蔑弃传统之民族虚无主义之有力棒喝,亦是对港台新儒学偏颇之积极矫正,乃儒家政治理想沉寂一百年后首次进入公共话语领域,表达出儒家独特而强烈之政治诉求,在中国学术界掀起了一场思想地震,其影响不仅于现在,更见于未来。本书以蒋庆先生“政治儒学”思想为中心,收录了来自各界的学术论文和思想性评论。
我与蒋庆在一个教研室呆过几年,相互之间还是可以有些共同语言,彼此的欣赏多少还有点。
有次他到广州城来看我,双方通过电话已经反复讲明在何地乘何趟车可到。我在家中沏好香茶等他上门,一两小时过了未见人影。我感觉似乎有什么事发生,即出门到客车大巴终点站去迎接。在车站也久等不见,那时没有手机,我料想蒋庆同学找不到房门,会再打电话来问,这点能力他还是有的,于是我又跑回家在座机前守候他的来电。
终于,蒋庆的电话来了,他焦急万分地再问我家的地址,原来本该乘车到一条线路的终点,他却鬼使神差地跑到起点站去了。说好再重新上车,我在终点站等他不见不散之后,我心中生疑,蒋同学怎么了?说起话来如此张皇失措,像有什么完全忍不住的事情压在他身上。
果然,那天我见到的蒋庆脸色完全是菜绿色的,问他怎么了,他慌张地要回家以后再说。一进我家门,蒋庆同学全然顾不得讲究上的斯文,救火式地一下子冲进洗手间,我在外面听到里边响声挺大的。原来近半个下午蒋庆同学肚里兜着越来越沉重的东西,找车、问路、上车、下车,一直没有去厕所方便的可乘之机。我看他真是快憋坏了。
放松之后的蒋庆,开始向我抱怨广州的公共设施的不周到之处,还说广州人不友善,普通话问他,他粤语对你,完全就是鸡同鸭讲。
但是,蒋同学在情急之中忘了自己的所为,记错站名,不会用手势或哑语问厕所,不善于挤公共汽车而一再错失搭车赶路的机会,这在哪个城市里其实都肯定要给自己带来不便的。
我与蒋庆在广州的初见,生成了一个新儒学大师的慌张故事。此后再同蒋庆谈起,他竟然什么都记不得了,只记得我对他双手送来的自己写的书,没认真翻几下就顺手放到一边,张罗头等大事一般地招呼他赶快趁热吃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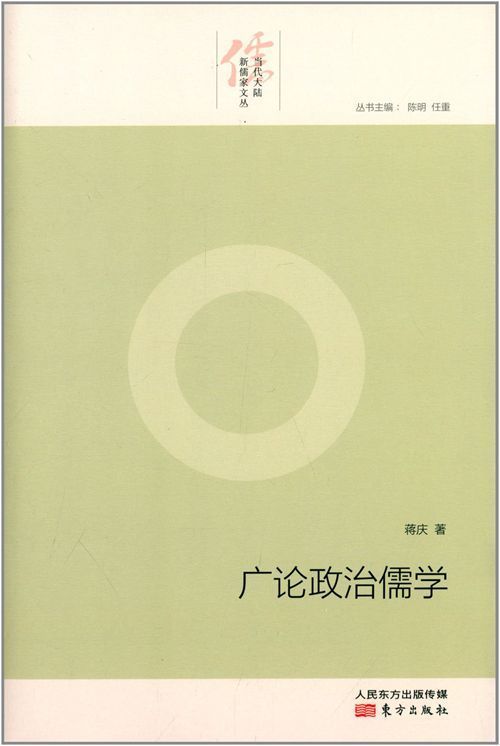
蒋庆著《广论政治儒学》,东方出版社2014年6月出版。
蒋庆同学名气做大了,人反而低调了许多。凡是西政七八级同学聚会,他也尽可能来参加,常穿件对门襟的布扣子的旧式唐装,然而也着西裤和黑亮的皮鞋,好像是使用着外形比较时髦的手机。
外界把蒋庆兄太传统化,太中国化了,描写他时完全像是在清风明月地说一位乡隐的道士,其实蒋庆同学的物质生活,现代得很呢。
不过,蒋庆后来也没有再拒绝同学们随行就市地称他为大师,有时他也稍微提醒一下,补充说是新派儒学大师,不敢去掠吵吵嚷嚷的那个法学世界的美。
我看蒋庆从学生时代起就没有真正关心过什么法律,只是偶尔顾及过法学中的个别有真趣一些的哲学问题罢了。在蒋庆大师同学眼里,如果把法律视为工具,那它就是一个人想要吃饭时的筷子。超出工具主义意义去理喻法律,那就可以不再哆哆嗦嗦地解释论证了,因为两千多年前孔子已经把好多工具主义的东西论及到了。

蒋庆著《政治儒学默想录》,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
蒋庆的思想很深刻,对搞法律和弄法学的人又有些显得无情的残酷,咱们好歹也是要吃饭的人,我们所干的理论活,也就是像吃上饭的人变着花样地用用工具主义的筷子,那又何必把问题搞得人为地复杂起来呢?
蒋庆同学一双利眼把世俗世界看得那么透,那么穿。
他每次同学聚会都心态超然地听法律俗务中的奇闻怪事,听同学们的牢骚、抱怨,叙事与叙旧,好像是在听一个陌生世界的声音。他那种静心辨认而又不近俗务的神色表情,让我们感觉到了哲人与凡夫俗子的精神距离。
后来,蒋庆同学给他发工资的单位打了报告提前退休,从喧闹的海角之都深圳退隐到了他的美丽无华的乡土贵州,在青山绿坡碧水环的贵阳郊区农村得到一块土地,蒋庆的朋友们雇当地的农人在这块地的四周遍种桃树,围成了一个真正的桃园。
听说蒋同学在桃园正中并没有建什么大成殿、结义堂之类的建筑,而是搞了一排像当年山西昔阳大寨村那样的庄舍,也许可以用时下房地产商的说法,是上有天下有地的连体别墅。蒋庆弄这些东西可不是要拿来卖的,他是用来招贤纳士,开门办学,布道儒家的。
听去那里看过的同学回来讲,那地方虽穷,但风景原始,有开发前的四川九寨沟之貌。蒋庆同学是得到了一些朋友的资助,当地政府又特别看重和支持办学这样的事情,几方面的通力合作,蒋庆同学才摇身一变由精神大师成了看炊烟袅袅思稻米香香的土地之主。
蒋庆撑起的乡下学堂必有许多很是世俗的故事,我在学校做过十几年的管理工作,深知好好地维系一个学校是何等的难事。以蒋庆的思想力,他当一个学堂的精神领袖那是绰绰有余的,但是说到行动力、掌控力,那可能就是另一回事了。
蒋庆的学堂哪怕就是一个以简约为美的,复古还原的私塾,也是需要多方面施以援手的。所以,西政七八级的同学们总是有想去亲眼看看的要求。
听有人讲,蒋庆特别欢迎西政七八级的同学前往,但附加了三个条件要大家去前考虑清楚。
一是随行若要带个女的,那只能是原配的夫人,最好夫人是读过西南政法学院的,如满足了这个条件,二婚三婚的只要正式办了手续也行。
二是不给带烟火。这条如是真的,有些令人费解,如果说是封山育林,禁带烟火,像有些地方张贴的标语:你在林子里点火,我就在你老楼内放火,那还勉强可以理解,但蒋庆的学园不给带火,岂不是到处都会冷秋秋的气氛寡淡?!要吃个重庆火锅或者来个野炊烧烤,那不是就成妄想了么?
三是不给带麻将、扑克牌一类的赌具,后来又听说放宽到围棋和桥牌一类的带点贵族玩法的东西可以带进去。可能是有的同学进到里面,桃园里转过几巡,也不见打理桃树的翠花、素芬一类的乡下妹仔,新鲜感一过,整天就只好无聊地搓麻将,昏天黑地地点火放炮,吆喝着点数收钱,这会大伤桃园学府的雅致和斯文。
我听着同学的添油加醋的议论,感觉到蒋庆同学像是在提倡一种过去半个多世纪前,一位姓蒋的委员长也说过的新生活运动。他们两人都姓蒋,会不会对现实生活中的一些方式有着共同的喜好与厌恶呢?

蒋庆著《申论政治儒学》,[台湾]新北:养正堂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版。
西南政法学院七八级的学生,几十年来过了多少桥、走了多远的路,大江大海都翻腾过了,什么样的猴事鸟事没有经办过?但一到贵阳桃花乡的蒋庆祠堂,可能都要从接受“五讲四美三热爱”的教育开始。
蒋庆的学问其实不存在任何异端色彩,他研究的是人性和人性怎么复归的千年命题。蒋同学对市场法律经济条件下可归之为食利一族的西政七八级人的简单要求,不能不说是在提醒我们还是要珍贵点什么精神,坚守点什么样的人性之美。
蒋庆的思想教我们看清了许许多多东西本来就存在着的底线,对我们这些壮心暮年的西政七八级人来讲,什么都不是很重要了,然而还只有学习是美好的。
蒋庆作为西政七八级的非典型学者,他代表着一种沧桑人生的特殊样式,他是一种价值的体现。
相关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