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莱特·戴维斯】虚无很重要
虚无很重要
作者:布莱特·戴维斯 著 吴万伟 译
来源:译者授权儒家网发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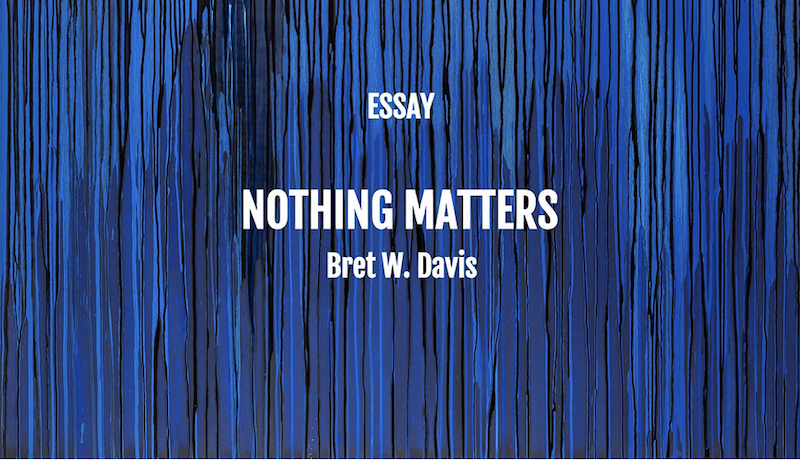
乔安娜·波考斯卡(Joanna Borkowska)的艺术品。
虚无主义的本质或许在于没有严肃对待虚无问题。---马丁·海德格尔
你有没有一觉醒来觉得起床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毕竟什么都不重要。或许你有这种感觉,但是,你的体验或许只是将其当作一种感觉,当作某种需要应对的主观心理状态,而非有关这个世界的客观事实。你或许想到假如你强迫自己起床,穿好衣服,喝一本咖啡,匆匆去散散步,你将摆脱这种糟糕的情绪,重新投入到周围世界有意义的奔波之中。
但是,你体验过不仅仅是一种感受的无意义性吗?你是否醒来沉浸在无意义的迷雾之中,就好像一张毯子把地球裹得严严实实。一种同质性的、琐屑无聊构成的氛围---弥漫在你的内心也包围在你的身边---它是多孔的,却是压倒一切的,既有压迫性的沉重,又有让人迷茫的轻飘飘之感,这种氛围给客观事物以及内心思想统统笼罩上一层无色无味的无意义感,带着某种看似无法转变的信念,即没有任何东西是真正重要的,这个宇宙毕竟既没有韵律也没有理由,既没有价值也没有目标。你是否相信,我们的人生故事就像莎士比亚的《麦克白》所说,“人生如痴人说梦,充满着喧哗与骚动,却没有任何意义”?
这样的虚无体验或许总是萦绕在人类的心头。但是,所有文化都在某种程度上克服了它。的确,文化作为培养有意义的规范和有目的的工程的活动---可以被理解为一种集体的努力,旨在克服潜在的无意义感,即认定一切都毫无意义,是一种语义上的“恐惧留白”(horror vacui)或者虚空恐惧症(kenophobia)。但是,在欧洲历史的某个点上---准确地说是在19世纪最后的几十年里----这种无意义感带着难以抑制的报复欲望浮上台面,而且获得了一种名称:虚无主义。
是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在1885-86的一则日记中宣称,或者至少准备好宣称:“虚无主义站在门口。”他认为,20世纪的门槛将面对虚无开放,也就是说,人们将体验到一种虚无主义,迎接“价值、意义和愿望的彻底拒绝和排斥。”人们越来越多地感受到,似乎任何事情都不再重要,都没有价值或者意义了,都不值得追求也不值得鄙视了。尼采在1887年的另一则日记中问到“虚无主义意味着什么?”他回答说,“最高贵的价值开始贬低自己的价值。目标已经缺失;“为什么”找不到答案了。”在尼采看来,基督教文化把自己玩砸了:我们对基督教的信仰教导我们尊重真理,真理则产生了科学;科学或者应该说科学主义,即科学本身能够为我们提供有关现实的所有真理的观念---毁掉了我们对基督教及其价值观的信仰。尼采说,我们应该为“上帝的死亡”负责。这意味着我们已经“将地球和太阳的连接切断。”他的主张是现代西方人---除了某些反动的保守派以外(当然在美国比在欧洲还多得多)---不再真正相信我们人生所依赖的道德和意义超验性的普遍源头。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做错了什么:我们的神学弑父者表明,不仅仅我们的罪恶再也没有办法得到宽恕,而且“罪恶”和“救赎”的概念本身都已经丧失了威力,“善”和“恶”如果不带有神权政治上的惩罚威胁和家长制的奖励诺言的话,将不再带有任何意义。我们为什么还要做或者不做任何事呢?
尼采知道,他来得太早了。大哲学家或许总是领先于他们的时代。尼采的书在他还在世之时就已经引起轰动,但并没有在哲学家中带来根本性的变化。不过,几十年之后,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一些西方哲学家---包括20世纪影响力最大的哲学家之一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以自己的方式对尼采的预言以及他的主题---做出回应。尼采的预言是虚无主义的到来,其主题是虚无主义无法通过逃离或者退却来解决,而只能通过置身于“在彻底经历虚无性的‘危险’中才能被克服”,这是德国诗人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Friedrich Hölderlin)的用语。
在他著名的---或者按照逻辑实证主义者如鲁道夫·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的说法“臭名昭著的”演讲中,海德格尔1929年在弗莱堡大学发表的就职演讲“什么是形而上学?”中对学界同仁阐明了他的看法。在说明了众多“科学”(或者“学界学科”,翻译成更一般性的说法“Wissenschaften”可能更好)人文学科(Geisteswissenschaften),还有自然科学(Naturwissenschaften)和社会科学(Sozialwissenschaften)之后,海德格尔问道,“当科学成为我们的激情之后,我们的存在从根本上说发生了什么?”换句话说,我们能够说,当所谓的没有利益纠葛的追求客观知识取代了哲学上的爱智慧之后,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当一种要清除所有激情的欲望成为支配我们思想和实证探索的唯一欲望时,将发生什么?各种各样的科学考察存在的这个或那个具体领域:化学构成、生物动物、心理心智、社会群体等等。科学关心每一种存在---除了这些存在之外,其他都不关心。毕竟,除了这些存在,还有其他什么东西呢?虚无。海德格尔的听众或许这样想,“到现在为止,一切都好,只是一个哲学家的某些寻常的、无伤大雅的喋喋不休罢了。”但是,他们的下颚可能要惊讶得掉下来了,至少眉毛要抬起来了,当海德格尔接着询问,“关于这个虚无,该怎么办呢?”人们能够想象的一个反应:“这不就是一个蹩脚的语法笑话吗?你根本就没有办法考察虚无,因为没有东西让你考察啊。”“毕竟没有一个东西在那里等着你去考察。”海德格尔或许回应说,“不,那不是我们渴望的东西,”回应可能是这样的。房间里的逻辑实证主义者可能大声质问,“你只是在玩文字游戏。这样愚蠢的问题,其基础除了复杂的文字游戏之外,什么都没有。”它们与严肃的哲学探索没有任何关系;就是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所说的“语言去度假”的案例而已。海德格尔先生不过是另外一只需要从捕蝇瓶中飞出去的哲学苍蝇而已,需要逃出自己制造出来的修辞陷阱。这就是为什么你们不应该给这种非科学的虚假哲学家终身教授岗位的理由,至少在他们学会产生可衡量的学术成果之前,正如所有真正的科学学者都在做的那样。(事实上,与卡尔纳普和后来拥抱科学主义的分析哲学后继者相比,维特根斯坦本人却非常同情海德格尔的问题,但是,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涉及到这个事实,虽然有巴门尼德(Parmenides)的不要陷入不可言喻的和不可理解的“非存在道路”和亚里士多德的名言“自然界里是没有真空的”等古代警告的漫长阴影,但是理论物理学家们越来越多地发现各种虚无观念恰恰位于自然科学最困难的难题的核心。请参阅不仅仅是菲杰弗·卡普拉(Fritjof Capra)的先驱性的、融合性的著作---也许存在一些问题---《物理学之道: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的平行线探索》,而且还有约翰·巴洛(John D. Barrow)的《虚无之书:真空、空虚和宇宙起源的最新观点》和赫宁·根茨(Henning Genz)的《虚无:虚空空间科学》。在15世纪的时候,多才多艺的里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就宣称:“在我们发现的最伟大事物之中,虚无的存在是最伟大的发现。”)
当然,海德格尔预料到人们可能惊讶得掉落下巴。其实,他的意图是扮演哲学牛虻的角色,戳中他的那些过于清醒的同行的双眼,因为他们乐此不疲地然而短视地向下盯着自己瓶子里可科学测量的存在。“虚无---在科学的眼中,除了觉得是愤怒和幻觉之外,还能是什么别的东西?”科学并不希望认识虚无中的任何东西。海德格尔非常乐意承认,对于虚无的符合逻辑的调查是形而上学的根本性问题,形而上学(他在该演讲中使用这个词想表达的意思)是人类存在的根本性特征。他也承认动脑筋思考本身是没有办法对付这个问题的:“因为思考从根本上说总是思考某些东西,必须采取一种行动,这与他在想到虚无时的情况截然相反。”
作为拥有视野潜能的存在,缺乏光亮难道不能引发我们体验一种无法看见却在有时候明明感受到的压倒一切的黑暗的存在吗?
科学的符合逻辑的实证性的思考方式总是基于特殊体验;任何体验似乎都是对某物的体验,对某个存在的体验,无论是意识对象还是思想或者想象中的观念。怎么可能有虚无的体验呢?柏拉图教导我们说,就像我们通过太阳光看到可感觉的物品一样,我们需要依靠理性之光看到可理解的物品。但是,正如意大利哲学家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在讨论亚里士多德有关“潜能性”特殊存在的话语(潜能性是一种奇怪的“某物”,还不是实际的存在,或许从来不会存在)时指出的那样,难道没有一个怪异的、但是无可辩驳的意识,在其中我们的确“看见黑暗”?作为拥有视野潜能的存在,缺乏光亮难道不能引发我们体验一种无法看见却在有时候明明感受到的压倒一切的黑暗的存在吗?
与此类似,海德格尔认定,我们的确拥有一种特定在场的体验,这种在场指的是缺乏一种有关居住着决定性存在的有意义的世界。首先,他指出,我们拥有普遍存在的情绪的某些体验,里面包含了丰富的感情,引导我们去适应这个“作为整体的存在”世界,而不仅仅是存在的集合(this ensemble of beings)中的这个或者那个存在。他提及快乐、爱情和深度无聊作为例子。比如,当你体验到快乐的时候,整个世界似乎都是兴高采烈的。当你感到深度无聊的时候,一团“令人窒息的迷雾”笼罩在这个世界上,用其“了不起的冷漠”覆盖了一切。
但是,即便是深度无聊,这种无所不在的冷漠并不能充分向我们暴露出虚无性的彻底深渊。在无聊中,仍然有一种有意义的后尝(aftertaste)和先尝(foretaste)---外面实际上存在一个有趣的世界,只不过此刻我不能接近它,就是这样一种感受。但是,在体验海德格尔所说的“最根本性的焦虑情绪”时,就连进入一个天生有意义的世界的这条生命线也被切断了。他对比了他用焦虑表达的意思“畏”(Angst)和恐惧(fear)的不同。当我们害怕的时候,总是对某物感到害怕。这个某物在我们看来有些吓人。我们周围的整个世界或许看起来更吓人,就像现实版的恐怖电影;但是,它仍然是一个有意义的世界,带着清晰的价值观(追杀我的凶手是个恶魔)和独特的目标(我需要赶紧逃出这个闹鬼的房子!)
相反,在根本性的焦虑情绪中,没有任何东西看起来是有意义的。其实,似乎什么都没有。事物如果要呈现出是这个样子而不是那个样子,或者这个紧挨着那个,那就必须存在某种意义结构。一个存在要存在,它就必须能够被确定、被定义、被划定边界(接近词源学意义上的同义词),以便和相反的、临近的或者某种相关的存在区别开来。存在从定义上说是相互关联在一起的,它们必然是在某个可理解的语义结构内相互联系在一起。但是,如果这个世界不再显得有意义的话,将发生什么呢?当这个世界作为语言结构的有意义整体已经被打破,成为相互没有关联的东西漂浮在没有结构的空间里的一团乱麻,又将发生什么呢?海德格尔说,我们将在极端的焦虑情绪中面对面遭遇虚无。“所有的事物,还有我们自己都陷入冷漠无情之中。我们抓不住任何东西。在存在者统统溜走的这个过程中,只有这个“抓不住的东西”来到我们身边,并留了下来。”
当这个世界作为语言结构的有意义整体已经被打破,成为相互没有关联的东西漂浮在没有结构的空间里的一团乱麻,又将发生什么呢?
萨特(Sartre)在1938年的小说《恶心》中,主要人物描述了他遭遇坚果树纠缠在一起的树根和公园中越来越难以抓住的东西,那些东西开始通过流淌的词汇和概念显示出其单纯的实然存在(is-ness),我们就是用这些词汇和概念维持抓住它们,与此同时又与它们保持一定的距离。在这个没有词语的、赤裸的存在的大片区域中,如此没有词语,庞大的赤裸的存在,在这个多孔的、单纯存在的集体中,什么东西都没有意义,什么东西都不再真正重要。萨特描述的这个体验不是与虚无(在缺乏存在的这个意义上)的遭遇,而是遭遇了存在的大量的、无法测量的、因而也是恶心的泛滥---大量拒绝被包含进去,拒绝被放进我们分配给它们的语言或概念盒子里去而变成可管理的东西。后来,萨特在1943年的《存在与虚无》中论证说,正是人类意识的主观性将否定性引入这个世界。否定的威力不仅意味着一种在事物之间做出有意义的区分的能力(这就是 f 那个,正如斯宾诺莎指出的那样,“一切规定都是否定”(determinatio est negatio)。它也意味着有能力想象世界不一样的情况,因而拥有理想能够让行动找到定位,旨在改变现状朝着理想迈进。可理解性和创造性都要求否定性。一个完全充满了存在的世界,一个没有任何鸿沟和虚无泛滥的世界,并不是真正的世界,即有秩序的整体这个意义上的真正的世界。它不过是多孔的、波动的小斑点,既没有可理解的意义也没有现实的自由,既没有创造性也没有责任。
伊曼努尔·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呼应萨特的无意义存在体验的描述---单纯的无意义实然(is-ness)---在1946年一篇题目为“存在:没有存在物的存在”的文章中,列维纳斯写到“当事物的形式在夜晚中消散,这个虚无不是那个纯粹的虚空。不再有这个或那个,不是有某个‘事物’”。但是,这个普遍的缺席反过来成为一种在场,就像失眠的时候降落在我们身上的那种单调的在场。虽然列维纳斯宣称“反对将夜晚的恐怖对应海德格尔式的焦虑,或者将存在恐惧和虚无恐惧对立起来。”我们将看到,海德格尔使用存在和虚无指东西的时候是将两者连接起来而不是形成对抗。海德格尔也没有考虑他用焦虑作为对某物---我们需要得到救赎的某个东西的恐惧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在海德格尔看来,我们需要虚无体验,以便参加到一种存在活动之中,它将给我们的个体和集体生活赋予意义。相反,对于列维纳斯来说,是另外一个人的面孔的体验和通过那张脸折射的上帝的超验性的无限性打破了存在的无意义的单调重复,用其他人的改变和我们对他们无法穷尽的伦理责任打破了本体论整体性令人窒息的同质性。(请参阅1961年的《整体性和无限性》Totality and Infinity)
虽然列维纳斯用伦理学代替本体论作为第一个哲学的先锋派激进性,但他对存在的无意义性的回应在关键意义上是显著的传统观点:追求宗教超验性的形而上学欲望和来自神圣命令的相伴产生的伦理责任(列维纳斯令人信服地描述的是,通过另外一个人的面孔的体验而最强有力地传达出来。)形而上学超验性为本来无意义的内在世界赋予了意义,通过另外一个人的面孔实现的神的启示开启了存在整体性的均质化过程。因此,列维纳斯的伦理现象学用后现代术语重复了前现代的主题:超验性的神圣痕迹为我们获得了世俗生活的价值观和目标。
但是,对于尼采来说,正是形而上学和宗教超验性首先诞生了虚无主义。通过将世界区分成为物质世界和超验性世界,地上和天国,通过将这个世界的价值观转移到另外一个世界,通过将人生目标推迟到来世,一旦我们发现自己不再能够维持对另一个世界的信仰,也就是说,一旦我们有一天醒来突然发现“上帝死了”,我们将不仅贬低了此世的生活而且让我们自己丧失了任何意义和价值的源头。我们应该为上帝之死承担责任,我们以真理和自由的名义杀死了上帝;但是,没有了上帝,我们显然不再有任何终极的源头和确保我们生活的道德和意义的基础。
但是,对于尼采来说,正是形而上学和宗教超验性首先诞生了虚无主义。
日本禅宗佛教和跨文化哲学家西谷启治(Nishitani Keiji)明白,尼采宣称的即将再度出现的虚无主义,在伦理学和宗教层次上的虚无主义就像病毒一样获得了抗药性。在一份自传性的随笔中,西谷启治写到,“虚无主义是虚无性在宗教维度上的再度出现,也就是说,在虚无性通常可以被克服的同样高或者同样深的那个维度上。”在过去,每当人们醒来陷入一种无意义性的情绪之中,或者被尘世生活没有终极价值和目标的意识折磨得疲惫不堪时,他们总是能够求助于对更高领域的信仰,求助于宗教教条和神的命令,从而再度确认这种生活---或者至少作为通向他处的一个步骤。但是,当我们不再相信神圣命令或者来世的赏罚,将会发生什么呢?我们是陷入绝望之中还是以某种方式找到发现或者创造价值观的新方式?
如果这就是我们能够获得的东西,我们能够确认我们认识的那种生活?我们愿意一遍一遍重新过这种生活,连同生活中的起起伏伏,连同所有的痛苦和欢乐,所有的欢喜和悲伤时刻?在尼采看来,这种“永恒性回归”的想法的“最大重量”是来辨认出此人是人生肯定者还是人生否定者的一种试金石。他想到,在虚无主义时代,人生否定者注定要成为渴望非存在的“消极的虚无主义者”。另一方面,人生肯定者能够成为“积极的虚无主义者”,即摧毁古老价值观的残余,以便他们能为创造新价值观开辟道路。这种积极虚无主义者为“超人”(overman),一种进化程度更高的人开辟了道路。从这种人身上流出来的“权力意志”能够让他创造自己的价值观而不是臣服于被“禁欲的牧师”刻在石头上的圣徒,这些人被认定为至高无上的主的助理。
年轻的西谷启治受到尼采的影响很深,到了中年时期,他把1949年出版的著作《虚无主义》(在作者的同意下,标题被翻译成《虚无主义的自我克服》)的核心章节都拿来阐述对他对尼采思想的发人深省的深刻解读。但是,到了他1962年出版代表作《宗教是什么》(在作者的同意下,标题被翻译成《宗教和虚无》)时,西谷启治对尼采的权力意志哲学的批判力度变得越来越强。他逐渐将权力意志视为佛教所说的因果报应---羯磨(梵语:karma),自我主义的自我意志或者确保我们绑定在一种生活方式上的“无限的驱动力”,这种生活方式让我们的无知和痛苦永久存在。尼采误解了佛教,将“进入虚无的意志”看作是消极虚无主义的顶点,那是一种终结所有欲望和消失在涅槃的空荡荡的虚无之中的自我毁灭欲望,同样,西谷启治则按照大乘佛教(Mahayana Buddhist)(尤其是禅宗)的适当方式把涅槃理解为自我主义追求的火焰的熄灭,这种追求让人从一种产生痛苦的生活方式中解脱出来,进入一种博爱、慈悲和充满同情和快乐的生活方式。
就像禅宗大师早就教导我们的那样,我们必须经历存在性的大死以便实现大活。
除了尼采的著作,传统禅宗大师比如18世纪的日本禅宗大师白隐慧鹤(Hakuin)和现代日本作家如夏目漱石(Natsume Sōseki),西谷启治一直以来都在探索最深刻的现代基督教作家如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yevsky)和最激进的中世纪神秘主义者和否定性的德国神学家、哲学家和神秘主义者埃克哈特大师(Meister Eckhart)的著作,此人注意到有时候谈及上帝性的“沉默的荒漠”---位于上帝圣父之外或者之下----作为“虚无”的深渊底部。西谷启治早先感受到在埃克哈特的彻底有神论和尼采的彻底无神论(或者按照内在的狄俄尼索斯术语(Dionysian terms)彻底重新考虑神圣性)之间的一种神秘的契合性。在其第一本书的第一章,基于他20世纪30年代末期居住在弗莱堡时写成并提交给海德格尔的一篇论文中,西谷启治用的“人生辩证法”的术语说到了这种契合性。在这种辩证法中,人类能够通过激进否定的方式来实现一种对激进人生的确认。就像禅宗大师早就教导我们的那样,我们必须经历存在性的大死以便实现大活。用现代困境的说法,在西谷启治看来,这意味着我们能够“通过完全经历虚无主义来克服虚无主义”,他使用这样的术语逐渐描述他的思想和人生道路。
在《宗教和虚无》中,西谷启治借用佛教(尤其是禅宗)术语来解释这个过程,使用从具体化(reified)的“存在领域和(代表性)意识”通过“虚无领域(the field of nihility)”“后退几步”一直到“虚空领域(the field of emptiness)”。虽然空虚领域(kū no ba空の场所)是通过虚无性领域(kyomu no ba虚無(kyomu)の场所)的激进化而达成的,他说,总体上不同于这个否定性的虚无:“是这个立场,绝对否定同时也是伟大的确认。”这里的空虚不是从存在一边看见的“相对性虚无”,作为来自身外的攻击的某种东西,而是从内部看见的“绝对性虚无”;正是在对面的到来作为像绝对近面的回归。虽然列维纳斯谈到朝向上帝的绝对他异性的形而上学“超验性”,西谷启治谈及的“超验性”则是激进地后退几步进入空虚领域作为自我的“起点”,这是一个领域所有的存在被实现成为它们真正成为的东西:“自身存在”(own-being)的空虚或者独立的实体,但充满了相互存在(inter-existence)或者“相互蕴涵(mutual implication)”。作为我们醒来意识到我们的最初相互联系的实验领域,空虚领域是“绝对的近面”(zettai shigan绝対)。那是爱情和慈悲自然从内部和我们中间产生的一个领域,无需诫命---也无需来自上边的承诺、奖励或者惩罚的威胁。
在其1937-1939年间在弗莱堡的短暂停留期间,西谷启治据说获得了长期的邀请,要在周末前往海德格尔的家为其讲授禅宗。海德格尔终身对东亚思想的浓厚兴趣得到了良好的记录。他常常表达出的不仅是对道家和禅宗佛教浓厚的兴趣,而且还有强烈的同情。在其解构整个西方哲学传统背后的形而上学基础的尝试中,海德格尔常常发现他要表达的后形而上学思想的其他开端与东亚思想的古代传统形成共鸣。(在多大程度上这些共鸣是巧合还是影响,这仍然是学界争论不休的话题。)
海德格尔有时候说,对他的思想领会得更深刻的是东亚人而不是其西方人同胞。在误解他的西方人中,海德格尔想到的不仅是指控他满嘴胡话的人如卡尔纳普(Carnap),而且还有充满热情地修改其思想的人如萨特。海德格尔在1945年战争结束后不久,曾经获赠一本《存在与虚无》。在此时写给萨特的信中,海德格尔表达了他的热情,称赞萨特踏上了他在1927年的《存在与时间》中开辟的道路。(面对当时的去纳粹化听证会,海德格尔显然也非常感兴趣能赢得著名法国知识分子的支持。)但是,在其1947年“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这是一篇内容浓密的文本,通过批评萨特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非常隐蔽地介绍了海德格尔思想上的重大转变,海德格尔决定性地和萨特的人道主义存在主义的自愿主义(voluntarism)刻意保持距离,在这种观点看来,人是“他渴望自己成为的那种人。”在萨特看来,人最初“出现在这个场合,”发现他存在于一个特别的处境中,拥有向它开放的特别范围的可能性,但是,在那个处境中,他基于萨特宣称的“意志”的“自发性选择”继续在根本上“定义自我”。
任意性地给世界添加意义的努力最终导致的是强化了这样一种印象,即这个世界本身是没有意义的。
海德格尔对萨特的主观自愿主义的唐突无礼的拒绝应该被放在他本人长达10年的纳粹哲学对抗的背景下看待。海德格尔逐渐认为,假设权力意志是存在者的存在(the being of beings)不过是颠倒的形而上学。海德格尔已经逐渐认为,任何形式的自愿主义都无法提供一种摆脱虚无主义的可靠方法---无论是有神论还是无神论,无论是个体的还是群体的,无论是尼采的,萨特的,或者海德格尔自己在《存在与时间》中更早的个人主义的决策主义(individualistic decisionism)或者他后来宣称的他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信念的“巨大愚蠢”,即相信希特勒体现出“德意志民族的单一意志”。相反,任何类别的自愿主义都表明“最深刻地卷入虚无主义的深渊,”因为任意性地给世界添加意义的努力最终导致的是强化了这样一种印象,这个世界本身是没有意义的。意义基于一种难以深究的任意性的自我中心主义的、种族中心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或者拟人化的神学中心意志。
在尼采宣称“这个世界是权力意志---除此之外,再无其他”之地,海德格尔认为,权力意志是从历史上看的存在者的存在的划定边界的理解。他事实上提出疑问,“这个除此之外再无其他”是什么?存在和虚无还能如何用别的方式来理解?海德格尔认为,萨特也简单地推翻了西方形而上学的术语;他在尝试随意挣脱它们束缚的意思时,甚至比尼采还更少些。比如,海德格尔认为,萨特的无神论人道主义是对有神论的匆忙拒绝,这种有神论简单地用微小的形式将神的特质转移到人身上。取代了神从原始的汪洋一片中创造一个有秩序的宇宙(正如《创世记》实际上说的话,虽然这个圣经宇宙学后来被基督教神学家们进行了很大程度的修改,他们提出了从虚无中创造(creatio ex nihilo)的教义,这种神学教义和古代哲学原则“无中不能生有”(ex nihilo nihil fit)异曲同工。对于零(nihil)的解释,就是作为存在的缺席。对于萨特来说,正是人类意识和意志的“为了自我”将意义强制性地放在存在的无意义的“自在”(the “in-itself”)上。同样,海德格尔认为,萨特误解了他在《存在与时间》中的命题,“此在的本质就在于其存在。”萨特简单地颠倒传统的形而上学观念本质先于存在,海德格尔则尝试同时思考本质与存在。在海德格尔看来,存在是一种“被携带进入虚无”的问题,这是他在“形而上学是什么”中说的话。在其“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对萨特的批评中,海德格尔进一步澄清了他的意思,存在是“在存在真理中的心醉神迷的固有性。”人类的存在,即此在(Da-sein (there-being))是开放的地方或者澄明(Lichtung),其中存在逐渐拥有了有意义的在场。在海德格尔后期看来,人类并没有任意地投射存在的意义,而是非常非任意性地参与到“语言在言说”(die Sprache spricht)的事件中,为人类的存在打开了从语言上说有意义的空间。在重新思考“存在”作为人类被召唤去密切关注和参与的“适当事件”中,海德格尔理解这个我们被抛入的“虚无”,在我们生活中最真实和最具创造性的时刻,作为新意义可能性的一个条件,而不仅仅是僵化的、古老意义的消解。
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海德格尔的确接受了导致其思想被误解的某些责任,因为他承认自己仍然在处于摆脱西方形而上学语言束缚的挣扎之中。一个说明问题的例子是,海德格尔用虚无的概念思考存在。虽然这在西方人看来不可能不觉得困惑不解,虽然在逻辑上他们很严谨,而且有简单地将存在与虚无对立起来的本体论,但是,因为东亚人将虚无仅仅理解为存在的否定或者丧失,海德格尔认为,他们处于更好的位置来理解他试图思考和准备说的话。
在若干场合,海德格尔说日本人能够比欧洲人同胞更好地理解他用“虚无”表达的意思。海德格尔在1963年写给一位日本学者的信中说,
“什么是形而上学?”这篇演讲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被翻译成日语,而且很快在你的国家被理解,这与它引进的这些术语的虚无主义误解在欧洲直到今天仍然占上风的情况形成明显对比。在演讲中和存在(das Seiende)对应,被称为虚无(das Nichts)的东西从来不是任何一种存在(niemals etwas Seiendes),它因此“是”虚无,但是仍然决定了这样的存在,因此被称为“此在”(das Sein)。
在1969年写给德国同事的信中,海德格尔写到,“在‘虚无’得到适当理解的远东,人们在这个词中发现了存在。”在他的基于他和一位来自日本的访问学者的对话而写成的“来自关于语言的对话(1953/54):一个日本人和一个探索者”中,海德格尔表达了对日本人理解其核心思想---存在作为虚无的能力的高度赞赏,他的日本对话者宣称,“对我们来说,虚空是最高贵的名称,指你用‘存在”这个词表达的意思。”其实,真实的情况或许是日本哲学家比如西谷启治有时候理解海德格尔想表达的意思,甚至比他本人理解得更好。比如在《宗教和虚无》中,西谷启治质疑,在说到“存在被抛入虚无时”,海德格尔事实上仍然在将虚无客体化,变成站在我们面前的某种东西。
按照西谷启治的说法,就海德格尔想到的虚无作为此在被抛入一种焦虑状态的深渊,“虚无作为某种“物”(从外面给此在带来威胁)的代表的痕迹仍然存在。”西谷启治在京都学派的后继者上田闲照(Ueda Shizuteru)追踪了海德格尔自己对我们与虚无的关系的理解的演变轨迹。海德格尔已经在“什么是形而上学?”中谈到了焦虑之中的“怪异的平静”,说“那些大胆者的焦虑”事实上“是创造性渴望的欢快和温和的秘密同盟者。”上田闲照暗示,海德格尔在那个早期演讲的结尾处提到的“释放自己(Sichloslassen)进入虚无”在海德格尔的后期思想中“得到激进化,变成了一种泰然处之(Gelassenheit)观念。”泰然处之(Gelassenheit)这个词是埃克哈特大师创造出来的,被基督教神秘主义者用来谈及放弃自我意志而产生的“平静释放”,被后期的海德格尔修改后用来描述我们最适当的存在(或许虚无)方式的成分特征。其中,我们从意志的现代形而上学中释放出来,去迎接一种存在的开放空间(Gegnet)的神秘体验,这种存在围绕在确定存在居住的我们有意义的世界的划定边界的视野周围。通过将我们人类中心主义的意志束缚中解放出来,进入科学理解的和技术控制下的有限存在领域,我们释放自己进入一种虚无体验,作为被掩盖起来的背景,存在的宽阔开放空间的过分内敛和收缩,一种难以计算的揭露事物可能性的宝库。在他的学术生涯中,为了强化他所说的“本体论差异”,也就是存在者的存在和存在物的差异,海德格尔有时候将存在说成是虚无。存在不是一个存在物,一个实体,因此,它是无物(no-thing)。在他的最紧凑、最晦涩难解因而神秘莫测的描述之一中,海德格尔写到,“存在:虚无:一回事”。但是,海德格尔用“一回事”并没有打算说存在和虚无是单纯的同义词,而是说它们难以解释清楚地属于一个整体,就像同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虽然他在不同的背景下提到这种亲密关系的方式不同,一般来说,可以说的是,在海德格尔看来,虚无是总是伴随着存在的隐晦(unconcealedness)的掩盖。虚无在本质上是存在的一种自我收敛或自我掩盖的维度。它是无蔽的遮蔽(the lethe of aletheia),适应事件“发生”(Ereignis)中卷入的修改“自行归隐”(Enteignis),围绕在(澄明(Lichtung))任何有边界的开放性黑森林的神秘(Geheimnis),那是可理解性的光芒能够照亮之地。它不是匮乏或空虚,而是划定边界的开放领域的完整性,其中这个或者那个划定边界的存在意识---这个或者那个意义视域---逐渐开始形成。
道家理解道即道路的方式是不确定的但是生殖力旺盛的虚无或者虚空,它能产生和容纳确定性的存在。
在海德格尔看来,虚无不是存在的虚无主义的匮乏,相反,正如他在《哲学的贡献》中所写,“虚无是存在(beyng [古代表示存在的单词,Sein的古老拼写] 的本质性颤抖,因此比任何其他实体更多。”为了强调存在的时间上的动态变化特征,海德格尔有时候使用它指“道”(der Weg)。他明确指出这与道家的核心概念道有关。道家理解道即道路的方式是不确定的但是生殖力旺盛的虚无或者虚空,它能产生和容纳确定性的存在。在道家的基本著作《道德经》中,我们被告知“存在源于虚无(有生于无)”“道乃中空的运载工具(冲),但是,用途从来不能填满其深渊性的深度。”海德格尔也提到《道德经》中的一个段落,提到了虚无在更加明显的划定边界的意义上的用途。罐子是陶土做成的,但是它的中空恰恰是让它有用的因素所在。
同样,房屋是由四面墙构建而成的,但是它的开放空间是让它变得有用的因素。像《道德经》一样,海德格尔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到虚无的这些划定边界和非划定边界的意义所在。西谷启治的老师和京都学派的创始人西田几多郎(Nishida Kitarō)提出了一个严谨论证和复杂表述的哲学,核心围绕着一个观念“绝对虚无的地方的自我确定性”(绝対無の場所の自己-限定)他区分了绝对虚无和“相对虚无”。前者是被理解为所有显示的所有现实的生成性矩阵,没有形状的,然而是所有自我划定边界的形式的自我划定边界的媒介,后者是被理解为单纯的存在缺失或者客观存在的主观性意识的缺失。西田几多郎广泛对比了西方和东方文化的形而上学前提,西方的存在凌驾于形式之上,东方的虚无凌驾于无形式性之上。当然,存在显著的差异和辩论以及规则中的例外,这些在西方和东方传统中都存在。使用了空性(nskrit: shunyata; Chinese: kong; Japanese: kū)有时候在佛教不同派别之间产生争论。这些佛教的虚空含义以不同的方式和道家的不同的“虚无”含义有关联(汉语中是无,日语中是mu)。这些术语和教导被传统禅宗大师和现代京都学派哲学家以不同方式交织在一起。本文没有功夫阐述这个复杂的思想史的范围(作为起点,我推荐刘继龙(J. L. Liu)和伯格(D. L. Berger)编辑的文集《亚洲哲学中的虚无》和拙文“禅宗中的虚空形式”)。我也没有功夫更深入对比西方神秘主义比如埃克哈特(比如拙文“为了虚无放弃上帝”)和海德格尔等哲学家(请参阅拙文“海德格尔与亚洲哲学”)。这里,请让我简单评论特别值得注意的一两个汇合点,或者至少是交叉点,引用了拙文“海德格尔与道家:不必要的存在的无用之道的对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将近结束的时候,海德格尔给妻子写信说,“在不必要的本质(我的意思是“存在”表达的意思),我最近发现了两位中国思想家的简短对话,我现在抄录给你。”他在这封信中抄录的对话选自《庄子》,道家的第二本基础经典。大约在同时,海德格尔在《乡间小路对话》结尾段落中也引用了这个对话。这个关键枢纽文本恰恰就是在他的思想发展的中期创作完成的。中文里表示海德格尔所说的“不必要”(das Unnötige)的词语“无用”通常被翻译成英文中的“useless”。海德格尔令人印象深刻地辨认出这个观念等同于他用“存在”(Sein)表示的意思。我们已经看见他说等同于“虚无”(das Nichts)。《庄子》也用“虚无”或者“虚”来说到“无用”。任博克(Brook Ziporyn)将海德格尔引用的《庄子》中的这个对话翻译如下:
惠子对庄子说,“你的话没有用。”庄子说,“懂得没有用处,方能跟他谈有用之处。大地既广又大,人所占用的只是脚能踏到的那一个平方而已。既然如此,那么只留下这一小块,把其余土地全部挖掉,一直挖到黄泉地狱,这样看来,大地对人来说,还有用吗?”惠子说。庄子说,“那按照这个道理来看的话,没有用处的用处自然就很明白了。”(请参阅:惠子谓庄子曰:“子言无用。”庄子曰:“知无用而始可与言用矣。天地非不广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则厕足而垫之致黄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无用。”庄子曰:“然则无用之为用也亦明矣。”——《庄子.外物》)
我们通常仅仅关注此刻直接在我们脚下的有限空间,也就是说只有那些在我们现有理解视野内被认为有用的或者必要的东西。我们按照事物在这种意义框架中的位置来理解和使用事物;依据他们在我们关心的事务处理中扮演的角色。但是,正如庄子所说,“依靠它所处的地位而被呼应或不呼应来做的事,或者依据它碰巧扮演的角色来评判某物,这难道不是荒谬可笑的吗?”“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人间世》)
按照《存在与时间》的早期海德格尔观点,我们将存在首先和首要地理解为世界中的“设备”,也就是说处于“意义整体”之中,这个整体是由“目的”通道的链条构建而成的,这些通道带领人们进入终极的“目标”(Umwillen),即一个由我们的意志(Wille)投射的人生工程。但是,在《乡间小道对话》中,海德格尔改变了立场,从意志转变为泰然处之(Gelassenheit)。在那里,与道家的无为观念不谋而和,他明确提到《庄子》中被引用的段落。海德格尔强调说,如果没有周围尚未发现的和显然“无用的”和“没有必要的”的地球扩张(海德格尔的开放空间或者庄子的“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於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庄子·逍遥游》)我们就不能越过现有视野,去开辟新理解和体验这个世界的新道路。
海德格尔有一次写到哲学的用途在于它没有直接用途。“它只有间接的影响,在那个哲学探索为我们的举止行为和决策准备新视角和标准。”在此意义上,我们与对象和目标的所有科学和日常交易,与在我们现有理解视野内暴露出来的事物和任务,都取决于哲学的更宽广世界观,这种世界观都必须习惯于无用之用。迷失在管理明显必要性的功名利禄的鼠奔之中,我们遮蔽了自身拥有的对“不必要性”的更深刻需要。
“在存在中奔忙”(Umtrieben an das Seiende),我们仍然忘记了我们与存在(Sein)的与世隔绝以及不确定的大量无物(no-thing)的基本关系。这些东西可以被隐喻地理解为囊括我们居住的“划定边界的林中空地”的浓密“树林”,或者作为令人晕头转向的庞大“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其中容纳了我们有意义的世界描述的“视野”。早期海德格尔很有名地将人类描述为在世存在(being-in-the-world)。但是,在依据禅宗佛教背景来解释海德格尔的时候,上田说,这其实总是在双重世界存在的问题,因为我们总是生活在一个去除边界的世界,它反过来位于尚未去除边界的“虚空”((kokū),正如有限的地球能够被描述为无限宇宙中的栖身之所。
***
我们典型地拥有隧道视野;我们只看见日常生活常规里有秩序的架构,这个架构是由我们个体和集体工程产生的,在此架构中我们在生活中为功名利禄鼠奔。位于我们通常习惯于居住的盒子边界之外的东西,就算出现甚至重新出现之时也只能呈现为虚无。我们可能体验到这种虚无---如果和当我们真的体验到它的话---作为对我们忙碌生活的令人担忧的、或者不方便的干扰,这种生活里充满了有意义的任务,它们似乎不断要求我们全身心地关注。我们的有意义的世界视野之外的开放空间,即使真的呈现出来,也只能呈现为无意义的乌有乡,作为喧嚣的、一团乱麻的一锅粥,要么是引发焦虑的虚无主义虚空,要么是引发恐惧和担忧的真空。
我们典型地拥有隧道视野;我们只看见日常生活常规里有秩序的架构,这个架构是由我们个体和集体工程产生的,在此架构中我们在生活中为功名利禄鼠奔。
海德格尔的名言是,“提问是思想的虔诚。”这成为漂亮时髦的哲学格言,经常被刻写在哲学爱好者和装腔作势者喜欢光顾的咖啡馆杯上的语录。但是,如果我们严肃对待它,并开始质疑一切,它可能显得任何东西都不重要了,就好像确定性的垫子被从我们脚下抽走,让我们暴露在虚空性的无意义深渊面前。我们或许甚至打翻了我们的无咖啡因卡布奇诺,但是,如果我们在那个体验中逗留或者逃离那个体验,我们或许开始感觉到自由解放。正如海德格尔所说,当“当我们释放自我进入虚无,我们将自己从人人都必须崇拜的那些偶像中解放出来,我们不再愿意卑躬屈膝了。”我们或许体验到这种虚无,不是作为引发恐慌的空无一物的虚无性,而是一种宽敞的开放性,让我们拥有自由和创造空间。我们或许发现虚无的不确定性不仅仅不是衰弱无力的匮乏而且是多孔的地下喷泉,不断冒出尚未定义的可能性。
正如海德格尔和庄子建议的那样,如果我们张开双臂拥抱那个开放的空间,为争取那个自由而解放自我---为了超越我们的占支配地位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的那个领域的开放性,我们将发现虚无能够成为自由的空间:摆脱僵化的语言和概念限制的自由,重新思考存在者的存在的自由,重新想象我们生活可能性的自由,重新规划我们共同居住的有意义的世界的变量。正如西谷启治建议的那样,如果我们一直后退穿过虚无性的领域,我们或许发现我们最初的家园是个虚空领域,这个发现能够将我们从自我的和的共同体的具体化和情感依恋中解放出来,让我们能自由地进行充满激情和创造性的合作。本文从反思令人深度担忧的情感开始,觉得任何东西真的都不重要。如果你没有转过脸去,如果你坚持把文章读完,虽然它已经更进一步堕入虚无主义的深渊这个话题,如果你耐心地思考东亚哲学家或许比海德格尔的西方同行更加准备好理解他运用怪异的违背逻辑的言内行为的前进方向,现在你可能明白,结果如此,虚无真的很重要。的确,“虚无”可以被理解为哲学家的终极关怀,这意味着在所有人中,只有我们在呼应最关键的和最认真负责的生存召唤。
作者简介:布莱特戴维斯(Bret W. Davis)马里兰州罗耀拉大学(Loyola University Maryland)教授,希金斯(T. J. Higgins, S.J. Chair)讲座教授。除了获得范登比尔特大学哲学博士之外,他还在德国学习和任教一年多,在日本学习和任教13年。用英文和日文发表论文几十篇,研究课题涉及到大陆哲学、亚洲哲学和跨文化哲学。译著有海德格尔的《乡间小路对话》和众多日文文本。著述和编辑的书籍包括《海德格尔和意志:走向泰然处之之路》(2007), 《日本哲学和大陆哲学:与京都学派对话》(2011), 《牛津日本哲学手册》(2020), 以及《禅宗之道:哲学绪论与禅宗佛教实践》(2022)。
译自:"Nothing Matters": An Essay by Bret W. Davis (Keywords: Zen; Kyoto School; Nihilism; Metaphysics) From The Philosopher, vol. 109, no. 1 ('Nothing').
"Nothing Matters": An Essay by Bret W. Davis (Keywords: Zen; Kyoto School; Nihilism; Metaphysics) (thephilosopher1923.org)
本文的翻译得到作者的授权和帮助,特此致谢。——译注
【上一篇】【西奥多·达林普尔】温柔之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