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飞】七个问题:超越古今之争,回归礼乐文明的真精神
 |
吴飞作者简介:吴飞,男,西元一九七三年生,河北肃宁人,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现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礼学研究中心主任。著有《婚与丧》《心灵秩序与世界历史》《神圣的家》《现代生活的古代资源》《人伦的“解体”:形质论传统中的家国焦虑》《生命的深度:〈三体〉的哲学解读》《礼以义起——传统礼学的义理探询》等。 |
七个问题:超越古今之争,回归礼乐文明的真精神
作者:吴飞
来源:“三联学术通讯”微信公众号
第一问:
2023年您在三联出版了新书《礼以义起:传统礼学的义理探询》,书中对近年经学、礼学研究中的重要议题多有阐释。我们知道,您最早的研究是偏西方的,比如社会学和基督教哲学,近年来您有一个“由西入中”的学术转向,开始更关注中国传统的学术,尤其是经学和礼学。可否请您聊聊,这个转向是怎么发生的吗?
吴飞
其实,长期以来我的研究都是在中西之间平行进行的。如何在西学建构的现代世界,思考中国的生活方式,是我一直在关心的问题。我的第一本书《麦芒上的圣言》处理的是西方宗教在中国的状况;第二项研究《浮生取义》则深入到当代中国人的生死和精神状态。要追溯现代世界的形成,必须深入研究西学传统,而自杀研究使我意识到,要理解当代中国,也必须追溯到古代中国,因此开始关注经学和礼学问题。最近几年虽然我写的中学文章越来越多,但阅读和思考始终都离不开西学传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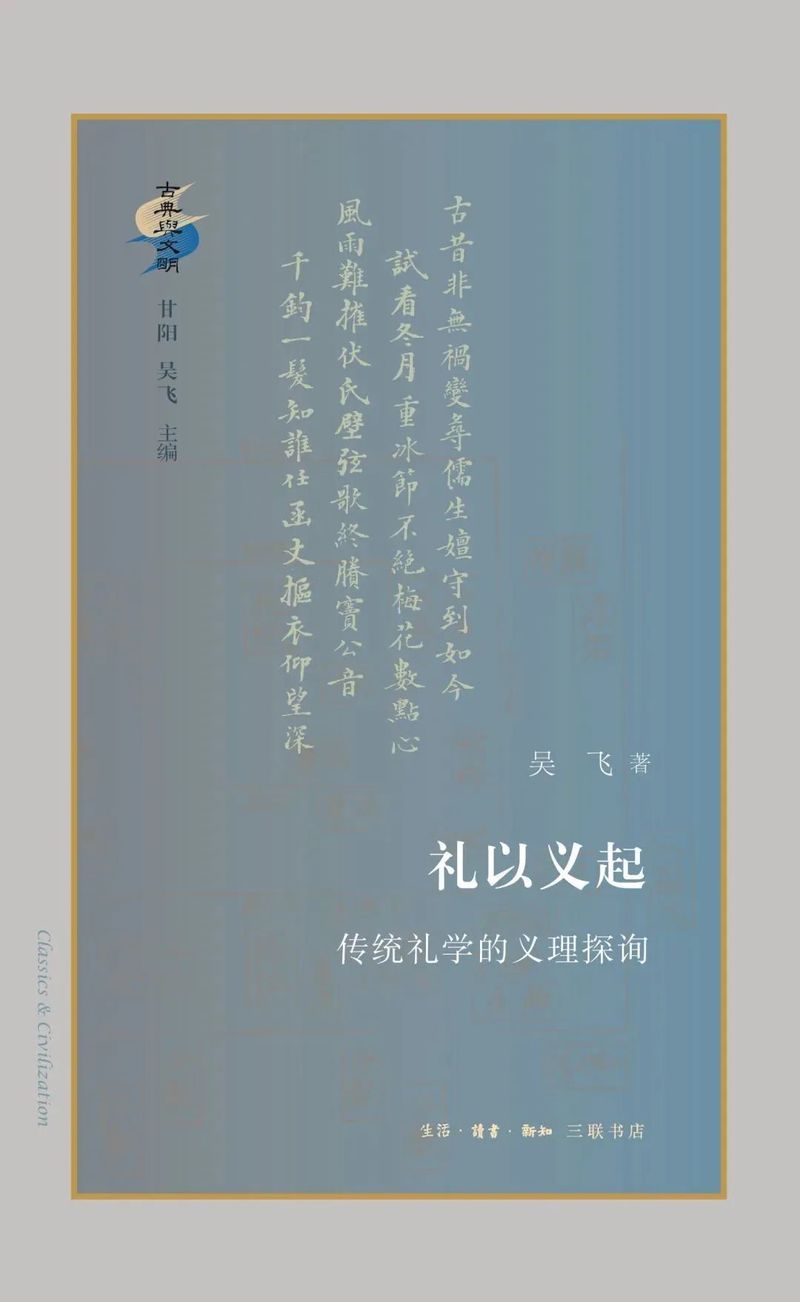
吴飞《礼以义起:传统礼学的义理探询》
第二问:
您几年前常常提到“文质论”,后来又把自己的研究收束到了对“性命论”哲学的阐释上,您为什么会提出“性命论”这个概念,您对“性命论”体系的阐释主要依托于哪些方面的资源?
吴飞
最初我在《人伦的“解体”》中提到了文质论,但后来感到文质论比较单薄,不足以概括中国思想传统的全部。所以提出了“性命论”,意思是,在文质问题背后,性命应该更根本,就像西方传统最根本的问题是存在。之所以提性命论,就在于,中国思想的核心问题不是存在,而是性命。不过,我并未因此放弃文质论。性命论的许多命题需要落实为文质论。可以说,文质论是性命论的方法论。性命论和文质论都是在西学传统的参照下,以中国经学传统为主要资源。文质论处理的是社会理论问题、历史哲学问题、文章修辞问题、个人修身问题,等等,但文质论也有其形而上学的层面。董仲舒、《白虎通》都说天质地文,而且我认为宋学理学在根本上就是文质论,因为“理”本义就是玉的纹理,是特别细密的文。而性命问题,虽然首先是宋明理学关注的问题,但先秦诸子、汉儒,乃至道教,都以性命为中心问题,所以性命问题也贯穿了中国思想的整个历史。性命,其实就是“文质”中的“质”。

吴飞《人伦的“解体”:形质论传统中的家国焦虑》
第三问:
改革开放以来,80年代兴起了“文化热”,90年代后又有“国学热”“儒学热”“经学热”等,经学的热度在近些年依然持续不降,更多人开始将对中国文明理想的探寻寄托在经学上。您如何看待当下的经学研究现状?对经学在未来的发展有什么展望?
吴飞
从国学热到经学热,这是越来越回到中国文明的根本。首先,我认为所有这些方面的学术推进,都取决于西学的积累和推进。经学之所以长期得不到重视,难以成为现代人的思想资源,是因为以前的西学研究无法为经学准备空间,现代的分科之学也无法容纳经学。但80年代以来,四十多年的学术积累,最大的成果在西学上,对西方古典学、中世纪神学、政治哲学、历史哲学等的深入研究,才激活了经学的研究视野。比起其他的国学门类,经学既是传统学术的中心和制高点,同时也如西方古典学一样是有门槛的,如果不认字、不认真读书,是不能随便乱说的。这就保障了,经学研究不会像其他一些国学部类那样,容易混进一些乱七八糟的胡说。但这需要很长时间的积累。像清代的许多经学家,如戴震、程瑶田这些人,他们关心的是很大的义理问题,但要弄懂这些义理问题,就先要认字读书,结果义理研究还未充分展开,反而是他们的小学研究被记住了。他们的研究积累,就使得我们今天再阐释经学,有了很高的学术起点,不会犯一些基本的错误。
其实最近几年不如前些年经学那么热了。一方面,专业研究,特别是许多年轻学者的研究,有了很大推进,但另一方面,专业经学之外的学者对经学的兴趣减弱了,就是因为经学容易变得很专业,非专业学者不容易读懂。但是,经学要对未来中国文明理想真正有贡献,必须对其义理做出更多创造性的解释。
第四问:
您的经学研究主要围绕“礼”的观念进行,礼学是个相当复杂琐碎的学问,很容易沉浸到大量古代礼学实践的细节之中,越做越窄,从而无法与更宏观的人文研究对话。那么,您是如何着手进入“礼”的研究的?您认为在当代,所谓的“礼乐文明的真精神”意味着什么?在现代人“礼观”越来越“稀薄”的情况下,礼学研究如何焕发时代生命?
吴飞
是的。礼学也是专门之学,容易陷入琐碎的细节,但不了解这些细节,也就无法理解礼学的真精神。这一关必须过,然后才能与更宏观的人文研究进行深度对话。我本人也是从细细读丧服入手展开礼学研究的,逐渐有了一些理解和想法。我认为,所谓礼乐文明的真精神,就是在三代,中华文明形成时,形成的基本精神,体现在六经当中。而对于当代人,则需要以这种真精神来理解现代性、应对现代性。
六经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是三代文明精神的记录与提升,而三代文明,在许多重要方面确立了中华文明的思维方式。新时代的经学,并非将六经中的每一部、每一句都当作颠扑不破的信条,而是通过解读六经义理,诠释出中华文明的基本精神。这一思路,与现代西方学者对待《圣经》的态度,亦颇类似。
面对三代文明,古人的史事体系与经义体系,是不可或缺的两翼;面对中华文明的丰厚遗产,现代人除了古史重建,也必然需要经义新诠。与古史重建相比,六经义理的现代诠释,还只是在摸索阶段。
经义新诠当然也不是简单的复古,而是对六经义理的现代诠释。三代作为中国国家文明的起源,不仅因为在时间上是源头,而且因为确立了基本的文明精神,就像希腊罗马确立了西方文明的基本精神一样。经义新诠则要告诉人们,三代所形成的这些制度、这些观念、这些著述,究竟传达了怎样的文明理想,诸如如何看待天地自然,如何思考人伦物理,如何理解家国天下,与其他文明的观念有何不同,并如何将它阐释得更高明。
我反对过于急切的制礼作乐,认为应该更谨慎一些,重要的是对礼乐文明的现代诠释,而非恢复古礼。
第五问:
您在礼学研究中,特别注重挖掘一些晚清经学家的观点,尤其是张锡恭、曹元弼、唐文治,这些学者在之前清代学术史的论述中并没有那么重要的位置,您是如何重新理解和挖掘张、曹、唐这些看似“非主流”学者的重要意义的?
吴飞
晚清民国是中国学术接触西方思想的开始,那个时代的各个派别都很重要。你提到的这几位老先生都出自南菁书院,在面对现代性时采取了非常不同的态度。唐文治先生与时俱进,主持交通大学和无锡国专,曾与北大的蔡元培先生齐名,是有巨大贡献的教育家。他一方面能够主持以理工科为主的交通大学,另一方面又能在现代教育体制中主持无锡国专,甚至在抗日时期还能坚持,培养了无数优秀人才。这当然是特别值得重视的。

唐文治(1865-1954年)
张先生和曹先生(曹先生有两位,曹元弼和他的堂兄曹元忠,曹元忠先生的学问是比曹元弼先生更高的,但去世早了些,著作没留下太多)和唐文治先生不同,他们是前清遗民,至死都留着辫子。因为唐文治在请求宣统皇帝逊位的奏疏上签名,三位老先生都和他绝交了(两位曹先生后来又和唐先生恢复交往,张先生却至死没有再见过唐先生)。这种精神和现代性可以说格格不入,是我们今天特别不容易理解,也应该去理解的。当时也有许多前清遗老聚集在上海花天酒地,三位先生近在咫尺,却不加入他们,而是采薇著书。他们不理解这个现代世界,但以“守先待后”为己任,至死都认为中国文化还有希望,所以在孤独中写了很多重要著作。鲁迅先生曾经买到过张先生作序的书,发现这些清遗民其实特别喜欢顾、黄、王等明遗民(顾黄王在晚清得到朝廷肯定,曹元忠起到了很大作用),而且还表彰在清代遭遇文字狱的学者,其实也对他们颇有敬意。
在具体学术上,我认为清代经学、史学、文献等方面的成就都非常重要,有很多地方发前人之未发,张、曹三位先生是清代学术的殿军,对清代几个方面的研究传统都有重要总结。现在重视他们的人越来越多,这对于我们发掘清代经学的成绩,是很有好处的。
第六问:
当您开始做中国传统宗教与哲学思想的研究后,您看待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的方式有什么变化吗?如果让您去诠释中国的文明理想,您会怎么说?
吴飞
我想在根本上没有大的变化,但具体方面当然是有推进的。大致说来,无论性命论还是文质论,都以自然为本,最高的自由就是最自然的生活方式,而不是人类文明对自然的超越或改造。我认为这在现代世界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第七问:
《礼以义起》收入在您和甘阳老师一起主编的丛书“古典与文明”中,这套丛书2017年开创,六年出版二十六种作品,相比其他“古典学”丛书,其最大特色就是中西学并包、翻译和原创齐头并进,强调“中国的文明复兴,需要对中国和西方的古典做出新的理解和解释”。请问您和甘老师怎么规划这套丛书的选题,尤其丛书“中学”部分作品的出版,有哪些考量?在丛书推出六年后,您对这套书的未来期待是什么样的?
吴飞
随着古典学在中国的展开,出现了很多套古典学丛书。这套书之所以称为“古典与文明”,就意在不止是限于专业的古典学研究。当然,像前面说的,无论中西古典学研究,都是有门槛的,不是随便怎么说都可以。基于对文字、文献、历史的学术基础,才能有更多思想的阐发。许多古典学研究,都要从特别具体乃至琐碎的问题入手,这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我们非常看重的,但我们希望,这套书里面所收的著作,要么直接要么间接地,会涉及到更宏观的文明问题,它的读者不能只限于古典学的同行,而是更宽广的人文学者,和对相关问题感兴趣的读者们。所以,我们也收到过一些非常好但过于专业的书稿,我们就没有收录到丛书中。以往收录的著作中,像关于希腊罗马的一些书,既有专业性,也有可读性,虽然可能只是在谈一个具体问题,但会牵涉到许多重大问题。比如《希腊人与非理性》《自由意志》,就得到了许多读者的肯定,可以说相当实质地推进了国内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再如巴霍芬的《母权论》,虽然有些老了,一些观点现在未必还接受,但是一本有巨大影响的古典学著作。而中国古典学方面的著作,比如乔秀岩、叶纯芳老师的几本书,主题是特别具体的问题,但有着非常宏观的问题意识,可以视为中学方面的典范。比如乔老师比较了孙诒让和黄以周的研究,两个人都是晚清经学大家,都有巨大贡献,但孙诒让的《周礼正义》就不能算经学著作,只能是考据学著作,而黄以周的《礼书通故》就是经学著作,因为是通过考据来表达经学思想的。乔老师这个标准就是我们丛书的标准。我们收的是黄先生这样的著作,而不是孙先生那样的书。现在有不少年轻人的书,既有扎实的考据,又有宏观的问题意识,我们特别欢迎这样的书,无论中学西学。

“古典与文明”丛书
责任编辑:近复
作者文集更多
- 【吴飞】作为实事求是之学的古典学 04-15
- 【吴飞】由祭礼尚质看巫史传统的超越性··· 02-16
- 【专访】吴飞:研究古典学,不是为了复古 11-27
- 【专访】吴飞:研究古典学,不是为了复古 11-06
- 【吴飞】经学何为?——六经皆史、六经皆··· 04-06
- 【吴飞】生命与命脉之间的法 03-08
- 【吴飞】七个问题:超越古今之争,回归··· 03-08
- 【吴飞】知几与稽疑 ——略论易学的命运··· 02-27
- 吴飞 著《礼以义起——传统礼学的义理探··· 07-26
- 【吴飞】文质论视野下的荀子人性论——兼··· 05-07
微信公众号
儒家网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

微信公众号
儒家网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