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惠生】天人合一叙事方式中的中国古代政治生态学
天人合一叙事方式中的中国古代政治生态学
作者:汤惠生
来源:《中华读书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五年岁次甲辰四月初一日壬申
耶稣2024年5月8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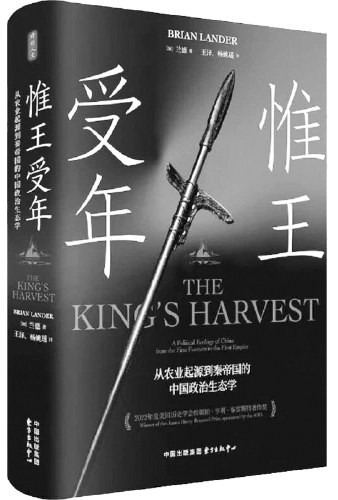
2023年8月由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出版的加拿大学者兰德(Brian Lander)的《惟王受年——从农业起源到秦帝国的中国政治生态学》(The King's Harvest:A Politi⁃cal Ecology of China from the First Farmers to the First Empire)一书(下面简称《惟王受年》),书中讨论了大约从距今一万年前农业起源到公元前2世纪末秦帝国灭亡的政治权力生态学。作者在书中讲述了农业系统在经过漫长的新石器时代发展后,人们学会了驯化与种植越来越多的动植物。新物种的培育和驯化增强了人类改变环境的能力,最终不仅能丰衣足食,还可以用稳定的盈余粮食来培育相应的政治机构。而政治机构的兴起和发达,又促进了用盈余的粮食养活的非农业人口的增加,最终导致了国家的产生和帝国的出现。该书是在西方现代理论、观念和方法中讨论中国早期政治生态学,但其叙事方式却很中国,所以我称其为天人合一叙事方式中的政治生态学。
英语政治生态学(political ecol⁃ogy)一词最早是弗兰克·托尼(Frank Thone)于1935年在其《自然漫谈:我们为草而战》(Nature Ram⁃bling:We Fight for Grass)一文中首次提出。20世纪70年代以后,政治生态学随着发展地理学(development geography)和文化生态学的兴起而逐渐发展起来。政治生态学以环境与生态为研究对象,并在生态和环境的背景中讨论政治及其经济问题。
殊途同归,古代中国天人合一思想中的天人关系为“天人感应”,认为天(自然)和人也是相互交通感应的。《中庸》说万物尽其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庄子·天下篇》说:“古之人大备,配神明,醇天地,养育万物,均调天下,泽及百姓。”到了汉代,董仲舒又在前人的基础上建立了“天人感应”的完整的理论体系,如《春秋繁露·观德》中所说的“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天地者,万物之本,先祖之所出也。广大无极,其德昭明,历年众多,永永无疆。”天有四时,王有四政,天人之际,合而为一,“以类相符”也。
人神之间犹如天地相隔,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对立的,而宗教的出现就是为了天上与地下以及神人之间的沟通。作者在书中谈到中国古代没有明确的宗教形式,不像欧洲国王,要通过神职人员才能与上天交流,“而中国的皇帝却可以自称为神”。“受年”是商代甲骨文中的用语,丰收之谓,有“贞岁商受年?王占曰:吉。东土受年?南土受年?吉”“鲁受年”等语式的记载。该书的译者之一王泽在《译后记》中说:“中译在‘王受年’前面加了‘惟’,‘惟’可以是无意义的发语词,也可以是‘唯独’‘仅有’的意思。”实际上这种“惟王”在周代金文中就已经是一个固定句式了:“惟王受命,无疆惟休,亦无疆惟恤”(《尚书·召诰》)。“受命”和“受年”应该是一样的,都是指来自天赐神授之谓。只有“王”等同于上天的神,也就是“天人合一”,这种“惟王”的句式才能具有其神性的能指,才能“无疆惟休,亦无疆惟恤”。所以该书的题目《惟王受年》所表达的,不仅是中国的古代句式,更是中国古代思维。
《惟王受年》的副标题为“从农业起源到秦帝国的中国政治生态学”,但从英语中我们可以看到的原文是“第一批农人”(the First Farmers)。英文的副标题要鲜活好懂得多,讲的是最早有一帮种地的农民如何最初通过种地不但使自己能吃饱,还能有余粮雇些专门人来管理自己的生活从而让自己的生活有保障,最后建立起一个帝国来保障一群人,同时也更直指本义:只有农民才可以最终建立起一个帝国,因为只有农人才能积累起必要的盈余与财富。全书接着从容叙述在从公元6000年前到秦帝国这样一个长时段,农人是如何通过各种经济活动来塑造政治的,然后又通过政治来发展经济的。谈经济的时候不免各种枯燥的数字与表格,谈政治时也难脱俗于老生常谈,然而当这两者结合在一起时,便起到了化合作用,作者兰德便汲取了天人合一的叙事灵魂,消解了生死之间的对立和人与自然之间分离,二元统一的东方笔触陡然变得鲜活而生动:
东营遗址中有原始牛、野水牛、獐和麝、獾、猫和野羊的遗骸。直到随后的龙山时期,驯化的羊和牛的到来之后,驯化动物才取代野生动物进入人们的食谱。随着农业用地的增加,各种动植物开始在这里栖息。杂草和昆虫在农田里繁殖,刺猬、野兔和仓鼠也是如此。小鼠和大鼠等啮齿动物从聚落中的所有食物分得了一杯羹。麻雀、鸽子和其他鸟类,专门吃农作物及其害虫。蝙蝠和燕子学会了在建筑物中栖息,这是捕杀村落周围活动的昆虫的绝佳位置。家猫还没有从西南亚抵达中国,但野猫经常到人类聚落来猎杀上面这些小动物。农村正在形成自己的生态系统。
动植物考古学家笔下死气沉沉的植硅石、孢粉和动物残骸在这里又重生复活起来。作为兰德的博士生导师、哥伦比亚大学的李峰教授在该书的推介语中更加准确和生动地速写出作者笔墨风貌:“在作者近乎诗歌式的语言中,遗址中发现的碳化种子变成了田里生长的谷物,孢粉遗存变成了山上的树木,残骨变成了野外奔跑的动物。”
《惟王受年》的内容安排虽然按照时间的顺序从史前到历史时期,但叙事模式并非历史,而是沿着政治结构的演进来展开讨论。到了历史时期,其叙事模式和研究方法更是采用了天人合一的衍化形式二重证据法。历史时期的政治生态学研究除了引用参考如《史记》《汉书》《诗经》《管子》《考工记》等一般汉语历史文献外,还涉及到许多古代动植物、物候文献如《夏小正》《月令》《商君书》等书,这也是其突出特点之一。作者兰德是加拿大人,汉语并非其母语,但《惟王受年》中大量的动植物研究分析都与中国古代文献中的物候描述相联系,也就是植物考古方面的二重证据法,这显然不是因为他古文好,而同样也是由于作者东方天人合一思维下的叙事方式:
10月,“草木黄落,乃伐薪为炭。蛰虫咸俯在穴,皆墐其户。”秋天打的枣子,是唯一能储存过冬的水果。冬天是砍伐野生芦苇的时候,这些芦苇能用来铺屋顶、编篮子。沤麻也在此时,要打去麻叶留下麻茎,在水里浸透了,使其组织软化以打出纤维。随着叶枯草黄,牲畜能吃的草料越来越少,农民们在此时宰杀家畜家禽,也许还得送一头猪给封君。肉用腌渍的方法调制,或者做成这个时候流行的肉酱。11月,“水始冰,地始冻”之时,就得拿出长袍、麻衣和皮裘,没有这些衣服是挨不过冬天的。随着天气转冷,人们开始在家中取暖,温暖引来了虫豸。“(蟋蟀)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穹室熏鼠,塞向墐户。”
一年四季人们生活的变化乃是对自然环境律动的响应,东方称之为“天人感应”,政治生态学也同样认为是“环境条件的任何变化都肯定会影响到政治和经济现状”(Bryant,Raymond L.and Sinead Bailey.1997.ThirdWorld Political Ecology.p.28.Routledge)。夏含夷的序中将“天人”之二元既通俗又直白地解释为:“我们知道了历史上的得与失,我们至少可以理解一些‘山之性’。明白了山之性,至少能理解一点人之性。”并将其定义为“一个关于关中的新故事”。
《惟王受年》中的很多段落似乎是在一种蚂蚁搬家或垒砖建房一样的叙事方式中进行,即从小处入手,从大处收尾;从低处开始,从高处终结。譬如在第2章经过漫长的地理、气候与生态、食物生产的起源、早期定居社会和复杂社会的兴起,以及政治制度如何在城郭形成、社会阶层如何分化、如何通过战争攫取财富、如何逐渐增强汲取自然资源和社会盈余的能力等一系列枯燥的数据分析和艰苦的描述后,最终为我们呈上一个似乎是不经意搭建的立体乡村景观的一瞥:
公元前500年,秦国已经占据了关中的西周王畿,东方的孔子在山东默默无闻地教书。在过去的1500年里,农业又有发展。比起龙山时期,牛、羊更为常见。鸡从南方传入,与猪狗并见于乡间地头。田间的菜蔬种类繁多,人们在房前屋后种上果树、坚果。据我们所知,牛耕约始于此时。
这种研究方式正是我们所追求的“替死人说话”,或“把死人说活”(张忠培先生语)的模式。显然也是一种天人合一的表达,王子今教授在推介语中对此有着诗意的评价:“作者在解说社会与环境之间关系的演变政体与环境之历史的互动时,颇多智慧的思考……自然环境保护意识体现出当时涉及‘天人’关系的明智理念。我们看到,与‘五谷蕃熟’同时,‘泱漭无疆’的绿色景观得以存在。‘动物斯生,植物斯止’所表现的自然风景,展现出‘方春蕃萌’的蓬勃生机。”
这是一部早期中国环境史的专著,但也可以视作动植物考古的著作,因为其史前部分的章节完全建立在考古资料之上。不仅如此,作者是在中西方学术思想和理论的影响下而发展出自己的学术认识和研究方法。正像兰德自己所说的,他刚开始从事环境史的课题研究时,就受到美国环境史研究和中国历史地理学家的启发,特别是史念海先生关于黄土高原土地开发与水土流失的文章的影响。美国学者伊懋可(Mark Elvin)的《大象的退却》(The Retreat of the Ele⁃phants)中关于战争是早期中国环境变化的主要因素,直接被兰德借用过来。纵观历史,战争不仅是国家最初形成的重要因素,同样也是政治组织壮大的关键所在。考古学上发现的城邑周围越来越高大的城墙,反映了这些社群动员让你们建筑、进攻或防御此类城墙的能力。战争同样也是人类对自然进行强力改变的象征。所谓革命,是指新旧社会形态的更替,是改朝换代的变动。如果说农业是史前的一次革命,那么游牧同样也是一场史前革命。既然是革命,其过程就一定不是和平的,换句话说,游牧文化接替农业文化的过程,是暴力的颠覆,就是战争。就拿青海的考古学文化来看,宗日文化与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与宗日文化因经济形态的一致性故而很容易发生交集与融合,而卡约文化的畜牧和游牧,与农业经济则根本不相容,二者之间不可能融合,因为土地就一块,要么种地,要么放牧。青海地区卡约文化对齐家文化的接替,亦即游牧文化对农业文化的替代,也意味着人类对自然地貌、环境、植被以及河流体系的巨大改变和破坏。《惟王受年》一书的写作同时受中外学者的影响,也就是说兼容了东西方环境史理论与学说,并加以体现,这不仅难得一见,同时也是难能可贵的。
说到牧业或游牧,这也是《惟王受年》一书讨论较少或浅尝辄止的方面。我们不能要求作者去讨论至少是他不想详细讨论的内容与课题,但是,既然是关于中国秦以前的政治生态,那么,游牧政治和游牧经济便是无法回避的一个话题。游牧民族对中国的青铜文化和战争文化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和作用,这些逐水草而迁的游牧人群又是如何参与并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史前中国的政治生态的?主导中国战争史主调的夷夏之争实际上就是几千年来农业部落与周边少数游牧民族的战争,农牧经济领土之间的争斗。不过这算不上是《惟王受年》一书的缺憾,仅仅是作为读者的一种意犹未竟的期待。
责任编辑:近复
【上一篇】【赵逵夫】地域文化中的历史记忆
【下一篇】【杨朝明】为经典学习插上翅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