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万里】经典的集解、集说和长编 ——由《礼记注疏长编》引起的思考
 |
虞万里作者简介:虞万里,男,西元一九五六年生,浙江绍兴人。现任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讲席教授,曾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兼任《经学文献研究集刊》主编。著有《榆枋斋学术论集》《榆枋斋学林》《上博馆藏楚竹书<缁衣>综合研究》《中国古代姓氏与避讳起源》《文本视野下的诗经学》等。 |
经典的集解、集说和长编
——由《礼记注疏长编》引起的思考
作者:虞万里(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讲席教授)
来源:《中华读书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五年岁次甲辰四月廿九日庚子
耶稣2024年6月5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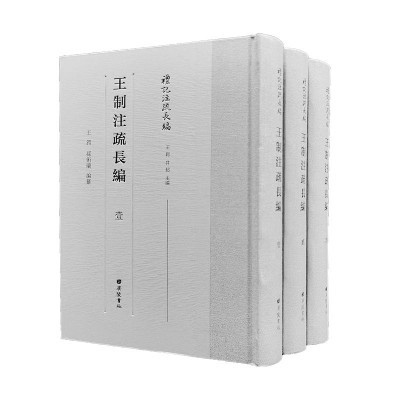
《曲礼注疏长编》《檀弓注疏长编》《王制注疏长编》,王锷等编纂,广陵书社出版
回溯集说、集解、长编、经解的历史及其体式演变,可以了解汇集诸家学说的经学体式,无论其名称同或异,都是经学历史发展所必然,是将文本和经义推向更深一层研究所必须,这就是我对《礼记注疏长编》认可和赞赏的原因。
——虞万里
通过跨学科的研究,通过经学文献的校勘与阐释,都有助于把握经学的主体性,但是当我们翻开《礼记注疏长编》,才可以直观地发现,经学的阐释传统才是经学主体性的真正所在,才是我们应该自觉继承和发扬的学术传统,才是我们超越分科治学,重新确立现代经学主体性的起点。
——徐兴无
王锷教授主编的《礼记注疏长编》已经出版了《曲礼》《檀弓》和《王制》三种,初步估计,《长编》全部出齐,约有60册左右。承他先后都第一时间寄赠,使我得以较早拜读学习。有感于当今传统文化研究的热度,经学尤其是礼学的专著和论文更是层出不穷,故《长编》的编纂和出版,引起我对当前礼学乃至经学研究和教学的一些思考。
一、《仪礼》《礼记》之难易
经学难,礼学尤难,礼学之难,莫过于《仪礼》,这似乎是一种共识。确实,《士丧礼》自孺悲见孔子,受教写出之后,其他篇章也逐渐形成。由于《仪礼》的仪节是一种行礼的过程,每个仪节的含义,不见于十七篇正文,研习者往往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所以七十子及后学已有懵然不解,必须师弟子传授和师友间互相切磋讨论方始得其谛义,这从《丧服传》的传与旧传以及《荀子·礼论》等文献中可以得到启悟。汉初高堂生传授时的训解是否为仪节的原意,已难印证,至多只能说大致正确。加之汉魏六朝隋唐以来,上自朝廷礼仪,下至民间婚丧,不断因革变易,所以歧说纷繁。好在《礼记》和其他典籍中还有一些解释《仪礼》的短篇,如《冠义》释《士冠》,《昏义》释《士昏》,《问丧》释《士丧》之类,可略窥西周制作和孔门师传之意。
至于《礼记》四十九篇,系七十子或七十子后学先后传授,由口授笔书递相记录,以不同文字辗转传抄,文本不一,来源各异。逮及汉初汇集于天禄石渠,尘封百年之后,简牍残泐断烂,交互相错,时亦有之。今就小戴编集四十九篇之文本,论其文字,则古文今文混杂,断烂错简纷糅。观其内容,诠解《仪礼》之仪节外,更涉三代制度因革,周初制礼作乐及春秋、战国各种制度文为,其中有实录,有传闻,亦有误解。以《王制》言之,郑玄谓其记先王班爵、授禄、祭祀、养老之法度,尚不足尽其内容。细分归类,有班爵、禄田、任官、巡狩、朝聘、教学、养老、国用、丧祭、职方十类。其中有一代之法,有四代沿革损益之制,若欲征文献以证,已有史文缺失之叹。以《檀弓》言之,有错简,如孔子少孤章;有脱文,如叔孙武叔之母死章。全篇采择七十子门人记闻,间夹杂逸礼经记,虽多言丧礼,而求义者多,陈数者少。以《曲礼》言之,包容更广。郑玄谓其篇记五礼之事,殆以有祭祀之说,有丧荒去国之说,有致贡朝会之说,有兵车旌鸿之说,有事长敬老执贽纳女之说。其内容虽可分析归类,但其内容与篇名“曲礼”有何联系?陆德明说《曲礼》是《仪礼》旧名,是委曲说礼之事。孔颖达认为是以其屈曲行事则曰“曲礼”,见于威仪则曰“仪礼”。历来各家,众说纷纭,至今也未有定说。其他各篇内容混杂,篇旨不一者所在多有。如《燕义》一篇,顾名思义,殆记君臣宴饮之礼,但篇首有“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一节,系《周礼·诸子》之文,与宴饮浑不相干,盖是小戴整理时误将其他简牍窜入。细察四十九篇,诸如此类者,不一而足。由此可见,要梳理《礼记》内容,溯其来源,别其条理,殊非易事。昔韩昌黎尝谓《仪礼》难读,不知《礼记》尤为难读,所以尤难者,以其背景深广,来源不一,简牍错杂,内容驳杂也。
二、今古文混杂的《礼记》
《汉志》于《礼经》十七篇之后,载“记百三十一篇”,师古以为是七十子后学所记。其中杂糅古文逸礼,知其文字亦多古文。小戴所编,是纯取百三十一篇,抑或兼编《明堂阴阳》《王史氏》和《曲台后仓》等记,历来都无定说,但无论如何,《礼记》四十九篇是一部今文、古文夹杂的有关礼制的传记资料汇编。其中今文用隶体书写,古文则用六国古文书写。汉代经师对于古文,大多无法读懂,或者说无法全部读懂。刘向《别录》说:“武帝末,民有得《泰誓》于壁内者,献之,与博士,使读说之,数月,皆起传以教人。”所谓“读说”,就是将不认识的古文字,通过对前后文义的理解,读成可以贯通文义的字,并将前后文义串讲成说。因为不同经师对同一经文体会不同、理解不同,所以各自的“读”和“说”也会不同,因而形成异说。如《汉志》列当时《孝经》有五家,经文相同,即都是隶书今文本,它与古文本《孝经》相较,有四百多个异文,平均四个字中就有一个异文。班固说“诸家说不安处,古文字读皆异”,可见凡有古文,经过不同经师的理解读说,必会产生异读、异文、异说,所以“汉读”是造成经典众说纷纭的源头之一。《礼记》既然是今古文杂糅的一部经典,那么它存有异文异说就无可避免。戴圣之后,郑玄之前,传《礼记》者有桥仁、杨荣、景鸾、曹褒、挚恂、马融、许慎、张恭祖等十余位经师,因为所传是一部古今文杂糅的经典,几经传抄又形成不同的文本,所以郑玄在注释时,无法像注《仪礼》一样,分清古文作某、今文作某,只能说某或为某,某或作某,经统计,这些异文有近二百个。他虽没有像注《周礼》一样引录某经师作某说,但各家因不同异文而有不同解说是必然的。郑玄之后至汉末,传《礼记》经师可考者有二十多家,魏晋以后,《礼记》地位上升,初唐孔颖达为《礼记》撰正义,传习讲解人数更在《仪礼》之上。宋代理学兴起,对儒家经典的诠释又有全新的、系统性的理解,卫湜汇集各家学说,居然有一百六十卷之多,异说之多,与传习、讲解人数和时代都有很大关系。清代偏重考据,又对《礼记》的汉注、汉读、汉说作了大量考订,《礼记》著作数量更胜于前。
三、集解、集说、长编与经解的意义
六艺经典异说在韩非所说“儒分为八”时就已萌芽,汉代经师秉承师说,读说文本,反映在简牍中,歧说矛盾已充分展现。要追本溯源,必须并陈众说,集解、集说体式的经解便应时而生。东汉初年贾逵的《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古文同异》三卷,是现今所知最早的比较著作。郑玄《周礼注》集杜子春、郑兴、郑众三家,还未用“集”字名。何晏《论语集解》录孔安国、马融、包咸等八家之说,始题作“集解”。六朝以还,注家越多,“集注”“集解”类著作也就越多,如李颙《集解尚书》十一卷,姜道盛《集释尚书》十一卷,崔灵恩《集注毛诗》二十四卷,崔灵恩《集注周官礼》二十卷,以及至今尚存的李鼎祚《周易集解》。即如《系辞》仅上下两篇,竟然也有《周易集注系辞》二卷。集注、集解著作的盛行,昭示着某部经典注解繁夥、解说歧出已到了不得不总结清理的时候,因而是经典诠释发展史上必然产生的形态,是评判众说、扬弃讹误、追求正解的必要手段。
长编一词,仿自李焘。稍后卫湜《礼记集说》一书,在并陈众说的层面上,已有“长编”的性质。明胡广领衔纂辑《礼记大全》,集四十余家之说,蒙“大全”之名而有“集说”“长编”之实。《钦定礼记义疏》八十二卷,采择更广,条例更密,既有长编之实,又兼裁断之判,是一经之总结,也是一时代标志性的经典。嘉庆初年,阮元命陈寿祺等纂辑《经郛》百余卷,后又循陈寿祺《经郛》汇辑古注条例,发愿纂辑“大清经解”,思将所有清代学者对一经一句一字之考证解释,分别汇集于一句之下,其相关者两见之。如戴震解“光被四表”为“横被四表”,系之于《尧典》;刘台拱解《论语》“哀而不伤”即《诗》“惟以不永伤”之“伤”,则《八佾》《周南》互见,如此毕陈众说,俾一览无余。只因老成凋零,人手缺乏,最后不得已而汇辑成现今丛书性质的《清经解》三百六十册。《清经解》虽造福学林,但欲检某经某句各家之说,必须翻阅多部、十几部甚至更多的著作,极为不便。沈豫率先着手改为“经解辑说”“经解汇纂”形式,思欲副阮元当时的意图,因个人势单力薄,无法完成。其后学者和书坊为便于利用《清经解》,想方设法编辑分类经解目录,希望便于利用。光绪年间,抉经心室主人赵贤经二十年孜孜不倦的努力,完成《皇朝五经汇解》,然亦仅部分实现了阮元的愿望。石印《五经汇解》,一展卷而清人诸说毕陈,曾为笔者所倚重,唯字小如蝇,颇伤目力,流传不广,故亦少为今人所知。
有鉴于经解著作繁夥而搜罗不易,翻检不便,近一二十年来,按经、篇、句汇纂、汇解形式,而不以“长编”名的著作亦时有所见,如《归善斋〈尚书〉章句集解》《诗经集校集注集评》等,凡此都是企望一编在手、众说毕陈的心理驱使下的产物。
四、《礼记注疏长编》编纂方式与意图
回溯集说、集解、长编、经解的历史及其体式演变,可以了解汇集诸家学说的经学体式,无论其名称同或异,都是经学历史发展所必然,是将文本和经义推向更深一层研究所必须,这就是我对《礼记注疏长编》认可和赞赏的原因。
《长编》汇集了卫湜《礼记集说》以下至郭嵩焘《礼记质疑》共十三家,虽说只是十三种著作,因为《礼记集说》汇集了郑注以下的一百四十四家之说,甘汝来等《钦定礼记义疏》于卫书外兼采元明诸儒之说,杭世骏《续礼记集说》更搜采卫湜所漏略者,益以元代十一家,明代三十七家,清代四十六家,故《长编》所集,当在二百五十家以上。尽管杭书所略及杭书之后,尚有数十百家之多,但此一编在手,已足备研究之资。
卫湜《集说》、甘汝来《义疏》、杭世骏《续集说》诸书互有重叠,为方便读者,不让篇幅过分冗长,《长编》在编纂过程中略有调整安排。需要说明的是,《长编》是汇集众说,提供资料,而不是要成一家之言。这对于求省便而欲得真知的学者而言,可能不厌所望,不免略有微词。其实,集说、集解、长编,自古以来,就有两种不同方式。郑玄囊括大典,以著为目的,所以兼采诸家之后,往往给出自己意见;《义疏》为显示“钦定”,亦多加“余论”和“辨证”:但并非所有集说之后都有评判。何晏、李鼎祚、卫湜之书,唯列诸家之说,极少按断。杭书《续集说》明言“不施论断,仍卫例也”。近出的《尚书章句集解》和《诗经集校集注集评》亦不加按断评判。这是因为,有的经义,罗列诸家之说,已经明白,无须赘辞;有的经文,诸家歧说不一,各有理据,无法作左右之袒。更有一些难解的经文,前人亦未有明确之说,简短的按语也无法解释清楚。所有这些,作为王锷教授团队在汇读《礼记》,纂辑《长编》过程中,比任何人都清楚。所以他们采取专门研究的路径,即在汇读过程中,碰到疑难仪节和经文,由有兴趣的人承担作专题研究,如《曲礼下》“君子行礼,不求变俗”、《檀弓》“葬日虞,弗忍一日离也”、《曾子问》“丧慈母如母”等等,都有专门的讨论文章,此将汇编成书另行。这种方式,是既不将不成熟的想法轻易加在《长编》之后,误导读者,徒增篇幅,更重要的是可以锻炼参与的学生综合分析材料,形成独立研究的能力。
我在阅读《长编》,理解《长编》体式过程中,时与王锷教授进行交流,得悉其组织学生,引导学生汇读《礼记》、纂辑《长编》、研究问题的形式与意图,似乎比单纯抄撮、汇编《尚书》《诗经》资料的意义更大,深感这是一条研究经学和教授学生,使学生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的切实有效途径,值得效法与推广。
责任编辑:近复
作者文集更多
- 【虞万里】训诂起源与传播形态 04-13
- 虞万里 著《文本视野下的诗经学》出版··· 04-13
- 【虞万里】《石经研究文献集成》序 07-26
- 【虞万里】王锷《礼记注》定本序 07-10
- 【虞万里 徐兴无】由《礼记注疏长编》··· 07-03
- 【虞万里】经典的集解、集说和长编 ——··· 06-26
- 经典研读社第二期,虞万里主讲《诗经》··· 05-25
- 【虞万里】《蜀石经集存》序 01-21
- 虞万里 著《中国古代姓氏与避讳起源》出版 08-26
- 【虞万里】中国经学的经典文本与思想内涵 05-23
微信公众号
儒家网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

微信公众号
儒家网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