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怀宏】让温和成为主流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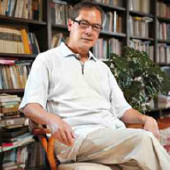 |
何怀宏作者简介:何怀宏,男,西历一九五四年生,江西樟树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著有:《契约伦理与社会正义──罗尔斯正义论中的历史与理性》,《良心论──传统良知的社会转化》,《世袭社会及其解体──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代》,《底线伦理》,《选举社会及其终结──秦汉至晚清历史的一种社会学阐释》,《道德·上帝与人》,《新纲常:探讨中国社会的道德根基》等。 |
让温和成为主流态度
作者:何怀宏
来源:原载于 《环球人物》
时间:癸巳年八月初八
西历2013年09月12日
何怀宏,1954年12月生于江西樟树一个农村家庭。18岁时去内蒙古参军,1984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4年后获得博士学位。曾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现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伦理学教研室主任,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伦理学、人生哲学、社会史等领域的研究。
何怀宏,就像他的文章那样温和、儒雅,发丝柔软,笑容恬淡,在这炎炎夏日里让人一下子静下心来,很难想象这位学者曾经当过11年兵。在接受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采访时,他温和低声,却总能拨开云雾,呈现清明。
作为北京大学伦理学教授,10多年来,何怀宏一直研究“底线道德”、“伦理重建”等命题,“我一直试图探讨一种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的底线伦理学。底线伦理指的就是每一个社会成员自觉遵守的最低限度的道德规范。如雨果所说,做一个圣人,那是特殊情形;做一个正直的人,那是为人的常轨。”
在何怀宏的眼里,“伦理学可以很深邃、很抽象,也可以很务实、很草根。”他的研究则把这种特性发挥到极致—他译过让总理和平民都喜欢的《沉思录》,写过每句话都要费心思去理解的学术专著,也时常在报刊上发表直白明晰的社会时评。2013年7月,何怀宏的新作《新纲常》出版,目的就如同副题所说,是为了“探讨中国社会的道德根基”。
为他人也为自己寻找到某种拯救之路
何怀宏从小就喜欢思考一些奇怪的问题,“我曾经非常恐惧,这个世界怎么来的,它会不会毁灭,人会不会不存在……所以,有段时间我晚上必须开着灯才能入睡,家里人都觉得很奇怪。”
何怀宏的阅读经历打着那个时代的烙印:在收购部门口收过旧书,为借一本书走十几里路……“我与书打交道的才能似乎远胜于与人打交道,我有一种嗅觉,能从人们想不到的地方找到书。”
高中毕业后,何怀宏到内蒙古当兵,一片冰天雪地,他夜里常常要走半个小时到哨位,站一个小时岗再回去。即便如此,何怀宏也不愿变成一个“不思不想”的人,他想方设法地借书,还借着去上海空军政治学校的机会学了一年多英语。军中11年,他的知识在阅读中丰富,而性格也在磨练中变得坚定果敢。
“文革”结束后高考恢复,因为所在部队没有考学机会,何怀宏只能干着急。而立之年,他才得到机会,考进了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读硕士,并选择了伦理学。“当时,几个年轻人的死让我震动很大:一个是当时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高才生冯大兴,他晚上潜入书店盗窃被人发现,在挣脱中击伤一位老人致死而被判死刑;另外一个是东北医科大学的学生苏克俭,他因对生命感到绝望而自杀,第一次被救了,但数月之后他再次自杀弃世。为他们感到悲哀的同时,我也试图抓住一点什么,希望能够为他人也为自己寻找到某种拯救之路。”
何怀宏用4年多时间,走了别人可能10年才能走完的路:分别用两年时间完成了硕士、博士学习。“我读博士时,除了一个在职的,何包钢、吴潜涛、远志明和我都住校。当时生活清贫,我们用大家名字的谐音作了一副对联,上联是"荷包无钱",下联是"何怀远志",横批是"三军无后"。我们4个人里,我是空军出身,还有两个人分别是陆军和海军,恰巧我们三人都是女儿,看来是没有男孩接军人的班了。”
何怀宏一直认为自己是思想和心灵上的“迟到者”。“如果"文革"一结束就能进大学,以当时的年轻和敏感会有怎样的收获呢?我不知道,有些机会失去了就是失去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重来。”
活着,就意味着思考
也许就是因为这种遗憾,让何怀宏更加勤奋。上学期间,他自学过拉丁语、法语、德语,并对梁启超所说的“中国欲求现代化的自强,当以译书为第一事”深以为然。上世纪80年代,何怀宏翻译了《道德箴言录》、《沉思录》等9部书,其中以《沉思录》最为出名。这本薄册子是古罗马哲学家、皇帝马可?奥勒留与自己的对话,大部分是他在战争的鞍马劳顿中完成的,内容是对乱世的看法,充满了摆脱欲望,渴望冷静、达观生活的想法。
2007年,温家宝总理在新加坡访问时,不但引用了《沉思录》中的一句话,还说:“这本书天天放在我的床头,我可能读了有100遍,天天都在读。”在温总理的“推介”下,《沉思录》流行起来,光是由中央编译出版社为何怀宏出的译本,销量就已达到30多万册。
何怀宏翻译《沉思录》是在1987年11月,当时他92岁的祖母刚去世,对他的打击很大。“她不识字,没出过远门,认识的人大概也不过百。她抚养而不占有,热爱而不支配,疼爱而不要求回报。翻译《沉思录》渐渐抚平了我心中的悲伤,也使我更深地意识到,德行比知识更可贵。”
如果说在翻译这本书之前,何怀宏是一个有点激愤的知识青年,受这本书影响,他变得温和而坚定,“一方面不那么激烈,怕烧伤自己或者烧伤别人;另一方面又不是无为放弃,仍然坚定地做好自己的事情。”后来无论是遭逢社会风波还是个人不幸,他都会翻翻这本书,“我总能从中读到一些让我沉静下来、继续努力的句子。”
从上世纪80年代末,何怀宏开始思考中国的伦理重建问题,以一种清冷的心境开始阅读中国古籍。但他又绝不是个困守书斋的书虫,陆续出版了《良心论》、《世袭社会及其解体》、《公平的正义》、《生生大德》、《中国的忧伤》等著作,思考传统社会伦理秩序和价值体系,探讨东莞工厂自杀工人、聂树斌杀人案等热点话题,研究当今社会道德及社会重建之路。
无论是读书、翻译,还是出书,在何怀宏看来,都是思考人生、社会的一种方式。“在我的词典里:思,丝也,思乃我生命的游丝或触须,在风中试探,试试看能抓住什么。思,乃对生命的执着和对死亡的抗拒。活着,就意味着思考。也可以说,思考的人才是有尊严的人,人在思考时最能表现出他的特性。”
有共同的底线,才能有所有人自由发展的社会平台
虽然探讨社会道德看来是老生常谈,但何怀宏提出的“新纲常”却有些石破天惊的味道,因为“纲常”这个词早就被作为一个负面词汇基本被社会忘怀了。他以儒家思想框架为依托,将旧三纲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改造为“民为政纲、义为人纲、生为物纲”,五常德中“仁、义、礼、智、信”不变,五常伦则由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5种人伦关系变为天人、族群、群己、人我、亲友5种关系。
环球人物杂志:中国文化向来尊崇礼教,为什么在近30年来,道德崩塌的情况会如此严重?
何怀宏:这与我们现在处在“三种传统”的影响之下有关:即2000多年来以“周文汉制”为关键词的“千年传统”;100年来以“启蒙革命”为关键词的“百年传统”;最后是近30多年来以“全球市场”为关键词的“十年传统”。
第一,从千年来看,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和陌生人打交道比较少,所以这方面的规范比较少。但到现代社会,大规模的与陌生人的交往成了主流。现代社会的伦理要求平等地对所有人,而传统社会这方面的经验不足。
第二,和近百年的传统有关,包括革命、斗争和造反的传统,它把人们分为势不两立的敌我两大阵营,而不是把人都当作平等的社会人。直到现在,这种意识依然没有消失,语言暴力、肢体暴力仍然随处可见。用斗争解决问题,而不是用妥协、谈判、对话、宽容来解决,这依然是我们当下沉重的负担。
最后就是这三四十年的社会转型影响。当前,社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个人也以求利为追求,但求利多少算够?即使手段、方式都合法,它的终点在哪里?大家都追求利益最大化,又互不相让,不正当的手段迅速蔓延。这些都是造成诸如食品安全等问题的原因。
环球人物杂志:您主张的“新纲常”怎么让它重新回到生活中呢?
何怀宏:提出“新纲常”的确是基于近百年来的社会大变,而道德根基旧的已破、新的未立,所以,这是个重建工作。为此,我想首先是要提出一些依据传统、直面现实的道德建构和设想,另外,也可以诉诸我们的信念、感情、本能。我相信“人皆有恻隐之心”,但它们也容易被遮蔽,需要以各种方式去唤醒人们心中本有的道德良知,让人们意识到:个人生存的前提是共存,而个人自由的要义是自律。这就需要建立一个稳固的,可以让所有人平等、自由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平台;而同时,这个平台上,人们的生活追求又是多元的。
环球人物杂志:在您看来,“新纲常”能够起到重建社会底线伦理的作用吗?在这方面,它会比政府的法规和制度更有作为?
何怀宏:道德只能起道德的作用,不能代替法规、制度,但它可以影响制度制定者,潜移默化地影响社会。一个多元社会如何才不会分裂呢?这需要社会成员达成某种共识,比如不互相伤害、有分歧不应压服而应说服、社会成员之间要互相诚信等。“新纲常”就凝结着社会的一些共识,有了基本的共识、共同的底线,我们才能进一步合作谋求一个更加公正的社会和美好的生活。
环球人物杂志:您对现实和未来最担忧的是什么?
何怀宏:我对现实最担忧的是政治。“新三纲”的第一纲是“民为政纲”,而“新正名”的第一条就是“官官”,意思是说官员应该像个官员的样子。中国本就有“官本位”的传统,今天由于经济和技术手段的加速发展,官员所掌握的权力和资源更大大超过了传统社会,人们一方面羡官求官,同时又骂官仇官,这说明了官员的德行和人们的心理落差之大。所以,约束和限制权力是当务之急,这需要政治制度的配合,靠法治和民主。而从长远来说,生态问题和生态危机可能会越来越明显。
环球人物杂志:现今社会,“戾气”随处可见,摔婴、杀人、一言不合便大打出手;另外还有很多人,包括部分愤青或公知,在谈论时事或与人辩论时,总是观点激进,言辞尖锐甚至国骂不断,对这些人、这些事我们该怎么看?
何怀宏:我相信许多激烈者的态度与他所处的环境有关。在一个有点昏昏欲睡的社会里,我们希望听到一些激越的声音,希望思想空间因此而扩大。但还可以考虑另一种平衡,比如说,更多地借助中间力量、中间态度,让温和成为一种主导力量。另外,还要加上“坚定”,我一直说温和而坚定。社会肯定会有两端人物,一端是激烈者、暴力者;还有一端就是完全放弃者、逆来顺受者,最好是中间的占多数,温和、理性但坚定地捍卫自己的权益,也关心别人的权益。当这样的一种力量占到主流,我想,这个“新纲常”也就建立起来了。
责任编辑:姚远
【上一篇】【何怀宏】寻求极端之间的中道与厚道
【下一篇】【何怀宏】《新纲常》简介、目录及引言
作者文集更多
- 【何怀宏】君子的人格 12-29
- 【何怀宏 赵占居】将无同?岂无异?——··· 06-07
- 【何怀宏】我们想要怎样的人类文明? 08-11
- 【何怀宏】政治、人文与乡土 ——当代儒··· 07-06
- 【何怀宏】人应该依靠什么样的伦理道德··· 08-08
- 【何怀宏】对新文化运动人的观念的一个··· 10-28
- 【何怀宏】儒学可以在政治上有作为,这··· 07-27
- 【何怀宏】抗议性政治不应成为主流 07-13
- 【新书】何怀宏:谈成功的书多,谈生··· 03-30
- 何怀宏著《新纲常》出版 11-19
微信公众号
儒家网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

微信公众号
儒家网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