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怀宏】对新文化运动人的观念的一个反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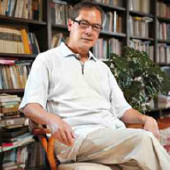 |
何怀宏作者简介:何怀宏,男,西历一九五四年生,江西樟树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著有:《契约伦理与社会正义──罗尔斯正义论中的历史与理性》,《良心论──传统良知的社会转化》,《世袭社会及其解体──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代》,《底线伦理》,《选举社会及其终结──秦汉至晚清历史的一种社会学阐释》,《道德·上帝与人》,《新纲常:探讨中国社会的道德根基》等。 |
对新文化运动人的观念的一个反省
作者:何怀宏
来源:中华读书报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九月十六日丁丑
耶稣2015年10月28日
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之后发生的新文化运动,试图唤起“吾人最后之觉悟”,即进行思想、文学乃至语言文字之革命,其着眼点是在器物、制度变革似乎不奏效之后解决人的问题,尤其是人心的问题。
如果说20世纪初的《新民说》还主要是试图建立能够适应新的制度的、社会政治层面的公民德性体系,那么,新文化运动中的“人的观念”已经涉及从信仰、追求、生活方式到社会行为规范的一整套价值体系。
于此,新文化运动就触及到中国文化的根本,触及到主导了中华文化两千年的儒家思想文化,因为它也是以如何做人、如何成人为核心的。
1.衡量文化的儒家的“成人”是以要成为高尚的道德君子为目标的,是要“希圣希贤”,以此前的圣贤为榜样,如孔子说:“吾从周”,“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夫!”颜渊说:“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而后世又起而仿效仿效者,学习学习者,追寻“孔颜乐处”。
儒家的这种“成人”追求是普遍号召的,即“有教无类”,任何人都可以进入这种“成人”的追求;但这又是完全自愿的,儒家从来不曾试图在社会民众的层面强制人们都成为君子,儒家对人性的差别也有深刻的认识,于是实际上还是只有少数人愿意和能够进入这种追求。
这种开始主要是同道、学园或学派的追求,到了西汉汉武的“更化”期间,有了一种社会政治的制度连带,即通过政治上的“独尊儒术”和察举制度,解决了秦朝没有解决的、可以长期稳定的统治思想和统治阶级再生产的两大问题,遂使一种人文政制成为此后两千多年的传统制度的范型。学者同时也成为朝廷的官员和乡村的权威。“士人”既是“士君子”,也是“士大夫”。
儒家试图驯化自己,也在一定程度上教化民众和驯化君主。而从两千多年历史看,它在驯化自身上最成功,其次是教化民众,最后才是驯化君主。它造就了世界文明历史中一个文化水准最高,道德方面也相当自律的官员统治阶层;造就了一个书卷气最浓、重文轻武的民族;也熏陶了一些明君,但却还是有许多不够格的皇帝。君主道德水准的提高与君主权力的提升并无一种正比关系,相反的关系倒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
2.中国近代以来,首先破除的是这种“成人”的政治连带,废除了科举制和君主制,然后是新文化运动试图全盘打破一切传统的束缚,摆脱一切羁绊,非孝反孔,追求一种个性绝对自由解放的新人。
社会不仅渐失“齿尊”,年青人甚至有意斩断和中老年人的联系,乃至从一开始,刊物和社团就是以“青年”“新青年”“少年中国”为号召的。
于是,相当于昔日“士人”阶层的知识青年始初有一系列走出家庭、尝试一种全新共同生活的工读互助团和新村的试验,但是,这些新生活的试验不久都归之于失败。当个人自愿结合的团体尝试变为“新人”失败之后,从中吸取的教训不是反省这理想,而是得出必须全盘改造社会的结论。挟苏俄思想赤潮的涌入,社会的重心转而走向一种在政党竞争、军事斗争中的“新人”磨炼。
在这一过程,始终有一种完美主义的伴随:先是追求完全自由的个人,然后是追求一个尽善尽美的社会。
为了实现这一完美的社会理想,却需要另外一种“新人”,一种接受严格训练和组织纪律的“新人”。那么,在这两种新人之间——试图完全摆脱一切束缚的自由“新人”和接受严格纪律约束的组织“新人”之间如何转换?这种转换可能是借助于一种无限放大和不断推远的完美未来:在未来的完美世界中,将实现所有人的完全的自由和幸福;而为了实现这一人类最伟大的理想,则必须接受目前最严格的纪律约束。走向一个黄金的世界必须通过一个铁血的时代。
于是,为了完美的自由,必须进入一种最严格的规训。而在社会层面倡导追求解除一切羁绊的绝对个性自由,适足以为一种对个人的绝对控制准备“特殊材料”。
任何一个乌托邦理想家设想的社会都会是完美和可实现的——只要在这个社会里生活的都是理想家设想的“新人”而非现实的人类。于是,是否能够造就出这样的一种“新人”,对这样一个理想社会的实现就至为关键,甚至生死攸关:如果人们的确能够被普遍地造就为理想家心目中的“新人”,这一最后的社会状态就将是天堂;但如果不能,实现这一社会的过程就可能是地狱——而不是其中一些知识者所以为的“炼狱”。
古代世界也有培养和造就“新人”的尝试,比如斯巴达通过某种军事共产制来造就一个勇敢简朴无私利的武士统治阶层;埃及的马穆鲁克体制通过购买和劫掠非穆斯林世界的奴隶男童,进入与社会封闭的学校培养为各种军事和政治的统治人才,但他们的子孙不能再成为统治者,因为这些子孙不再是奴隶,因而必须一代代重新购买和培养。而终身不婚的天主教会的僧侣和修士甚至也可说是一种培养“新人”的尝试。
但这些古代的“新人”尝试和现代世界的尝试明显不同的是:它们都是明确地限于这个社会的全部人口中的少数人的,这少数人与社会民众是保持相当的距离甚至是相对封闭隔绝的。比如说柏拉图描述的共产制是仅限于少数统治者的,他们拥有统治的权力和很高的社会地位与威望、荣誉,但他们不用于属于个人的私有财产,甚至不拥有自己单独的家庭与儿女,以此来保证权力不被滥用和遗传。虽然这也可能仍然是一个不能持久的乌托邦,但古代的“新人”尝试的确没有试图去改造所有人,去改造整个社会,它们也没有一个地上完美天堂的梦想。包括渴望一种超越存在的完美的基督教,也没有打算实现一个人间此世的天堂。而在新文化运动之后出现的“新人”尝试则是大规模的,全社会强行的,为的是实现一个完美主义的社会理想,然而,这一完美未来的地平线却令人沮丧地不断后退。
于是,这就会提出一个人性的普遍可能性和可欲性的问题:人们或许能在很大程度上洗心革面,改造自己,我们的确可以看到有这样的道德圣贤或宗教圣徒。但是,人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改变社会上几乎所有人、或者就是大多数人的人性?而且,一种强行的试图全盘改造他人和整个社会的尝试,是否本身就违反道德乃至人性?
无论如何,新文化运动带来了社会对于人的观念和理想的一个剧变。在民国之后、新文化运动之前,社会崇尚的还多是孔子等传统圣贤人物;在这之后,崇尚的人物就再也不是以孔子为中心的传统人物了。新文化运动标志着传统人的观念的一个巨大转折。
和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不太一样,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一是有意和传统的断裂乃至决裂;二是和政治的紧密连接。最后,它的结果主要不是文化的成果,而是政治的后果。
西方文化复兴运动产生了一系列文化的巨人,而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则开启了一个激烈动荡的时代,这时代也产生了自己的政治巨人,并不断树立自己的英雄模范人物。新文化运动中不乏道德高尚的君子和文化的翘楚,但是,经过百年来一系列的转折跌宕,它最后造就的最引人注目的人物可能还是寥寥几个政治“超人”和不少“末人”。
3.今天我们也许有必要重温传统的“成人”之学,但也必须根据现代社会的情况有所转化。
传统儒家的“成人”之学能够转化的一个关键是:它同时也是一种“为己之学”。它也明确地自视为一种“为己之学”,这意味着即便在古代最强势的时期,儒家也并不打算在全社会强行其“希圣希贤”的道德,它的君子理想向几乎所有人开放,但实际只有少数人能够甚至愿意进入,因为它需要一种更高的文化能力和更高道德标准的自我约束。
它也不仅是少数的,而且是自愿的,它不是尚武的,而是尚文的;它开始也不是抱有政治统治的目标的,而只是一个求学问道的团体。但它通过选举制度造成的一种沟通上下、注重文化,政治机会平等的文官治理体制最后却延续了两千多年,在世界文明史上也是绝无仅有。它的这一独特意义看来还没有得到世界足够充分的认识。
儒家的“成人”路径或可说是一种“学以成人,约以成人”,即最终能够趋于道德自由之境的人们,主要是通过一种自我的学习和功夫,通过一种和神圣、社会与同道的立约,通过规约自己而最后达到自由的自律。
新文化运动中的人们急欲摆脱传统,其中激烈者呼吁要“打倒孔家店”,而今天重温孔子有关“学以成人”的名言,却深感其中有即便是现代人亦不可违者也:
十五有志于学——这是“成人”关键的第一步,但还远不是“成人”。“志学”同时意味着自身的有限性和自身的可能性,于是开始有一种修身求知的自觉。学是起点,是开端。不学无以成人。虽然这“学”并不限于文字和文献之学,但在中国的儒家那里,的确也离不开文字与文献之学。
三十而立——这是初步的成人,也是社会眼中的成人。它不仅是性格的独立、也是经济的独立;不仅是自我事业的初步确立,也常常是家庭的确立。即所谓“成家立业”,但最重要的还是一种精神品格的独立,虽然今后还可能会有探索方向上的错误,但那也是自我选择的结果,而不是人云亦云。
四十而不惑——虽然可能意志还不足,境界还不够,但此后或不再犯根本的认识论错误,不会再走大的弯路,尤其是不易受浪漫的空想的蛊惑,理性已经相当冷静和充分,情感也相对稳定。
五十而知天命——这已经是大成的时候。“命”既是“使命”,也是“运命”,即是开放,也是限制。命也,非来自我也,天降于我也;命也,无可更改也,但最大的限制即被自觉地认作“使命”,也可能恰恰构成最大的力量,而且还构成一种真正有力量者的安心。
六十而耳顺——“耳顺”是对他人,对社会而言。自己对来自他人和社会的一切已经“宠辱不惊”,而且,对他人还有了一种透彻认识人性之后的宽容;对社会也有了一种通透的理解,知道还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
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时才是达到一个真正的个人自由之境,完善之境。道德意志不是脱离规矩为二,而是与规矩合一。规则完全不再是外在的异己之物,而就是自身精神最深的需要。
这一过程以自我始,以自我终。但最初的自我是一个刚刚开始发愿和立志的自我,最后的自我则已经是一个与天、地、人契合的自我。
且不说还有“困而不学者”,志学者并不是都能达到这最后一步,甚至达到“知天命”这一步都很难,可以说只有很少人能达到这最后一步,甚至中间的几步,但这最后的一步就像歌德所说“永恒的女神”,引导有志者永远向上。
而如果说,即便如孔子这样的圣贤,也是自许为“学而知之”而非“生而知之”,我们有谁又敢说自己是天纵之才而不需要通过学习就能悟道和成人?我们即使承认如柏拉图所言“学习就是回忆”也具有一定的真理性,即学以悟道成人也需依赖一定的天赋与悟性,然而,后天的、艰苦的“学习”也仍然是不可缺少的媒介和必须的途径。
而如果说,即便如孔子这样的圣贤,也是到七十岁的时候才能做到“从心所欲不逾矩”,即在经过几乎一生的规约之后才得到比较完全的自由,我们有谁又敢说我们一开始就可以不要任何约束就能悟道成人?我们有谁又敢说自己可以通过摆脱一切羁绊的绝对自由而成为新型的完人?
这提醒我们或许从一开始就要预防一种对个人绝对自由和完美政治社会的追求。
孔子又说:“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颜渊亦言:“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
我们或可究其“约”义且又广其“约”义,谈到一种伟大的预约与规约。
首先,“学以成人”可以是一种神圣之约,是自我与超越存在之约。这超越的存在可以是天,可以是神,可以是圣。因为这神圣之约,所以我要成为配得上这神圣的一个人。
其次,这约定也是一种社会之约,是自我与家庭、与亲人、与职业群体和其他团体、与政治共同体、与整个社会之约。我必须做一个担负起我的各种社会责任的人。
再次,这约定也是一种同道之约,是自我与同一志向的朋友之约。这是自愿的结成一体。对于一个伟大的目标,我们每一个人的力量都可能是不够的,需要互助和互励。而到一定时候,一个人如有了相当的力量,又是要散发开去的,而这散发也是回收,这力量又会加倍地回到自己的心身。
最后,又还有一种践约,这践约实际也主要就是规约,我们需要不断地规训自己,而这律己其实又是一种自律。不否定有人有顿悟的可能,但很少人有这样的可能。悟性之高如李叔同者,入佛门也是进入律宗。
一种志愿必须从自己的内心生发出来,“十五有志于学”便是立约的开始。预约不妨其高,不妨其不与众同,但不断落实,不断具体;规约则不妨从低开始,从底线开始,从与众人同的社会规则开始,但能够将“庸常之行”与“高尚之志”连接起来。
虽然古代“成人”的意义就已经不是完全一律,有儒家的“成人”,也有道家的、或其他路径的“成人”,但儒家的路径的确是占据主导,而今天的“成人”则更趋多元,不再有一种固定的、统一的意义。类似于古希腊的“Virtues”,人们追求的人生目标将向各个方向展开,它们不仅仅限于道德或宗教的,还有艺术的,各种才干和能力的,甚至精致的休闲之道,体育竞技之道等等,而所有这些追求又应该受到一些基本的规约的限制,以不妨碍他人的同等合理的追求。
今天的任何一种“成人”或都已经失去社会政治的直接效用,这就使一种神圣和同道的相约显得更重要了。
以上诸约在传统社会的儒家那里是一体的,天道与社会、一己与同道、本体与功夫常常都是打通的。而道德渴望与其他方面的文化追求、乃至与政治权力、经济财富和社会名望都是连接的。但现代社会的人们则可能、或也只能择一而行,而对何谓“成人”目标的理解也有了各种合理的差异,但精神却仍可以是一种:即努力在做人中寻求“成人”的意义。
责任编辑:葛灿
作者文集更多
- 【何怀宏】君子的人格 12-29
- 【何怀宏 赵占居】将无同?岂无异?——··· 06-07
- 【何怀宏】我们想要怎样的人类文明? 08-11
- 【何怀宏】政治、人文与乡土 ——当代儒··· 07-06
- 【何怀宏】人应该依靠什么样的伦理道德··· 08-08
- 【何怀宏】对新文化运动人的观念的一个··· 10-28
- 【何怀宏】儒学可以在政治上有作为,这··· 07-27
- 【何怀宏】抗议性政治不应成为主流 07-13
- 【新书】何怀宏:谈成功的书多,谈生··· 03-30
- 何怀宏著《新纲常》出版 11-19
微信公众号
儒家网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

微信公众号
儒家网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