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奥麟】 "中和"专题讨论(一)——《中和旧说》之可贵处
"中和"专题讨论(一)
——《中和旧说》之可贵处
作者:孙奥麟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原载于“儒家人文学”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四月廿六日甲寅
耶稣2016年6月1日
“儒家人文学”编者按:
儒家的心性之学中,中和问题大略是金字塔塔尖一样的存在,是心性之学的收摄处。《中庸》谈到中和问题的文本只有寥寥几句,而一旦讨论起来,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理、气、心、性、情、意、感、应、知、行问题却全都参与其间了。
编者对朱子的中和新说,总是不能领会。承蒙川大的“中哲三先生”不弃,命我在切磋班上主讲中和旧说,此事也就成为了中和问题讨论的缘起。谈中和问题,三个钟头的切磋班自然是不够,其后,四五位同学与编者的私下研讨也一直没断过,其间更蒙远在京师的天成君来信参与,将讨论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令编者受益匪浅。
编者冥顽,于中和新说,至今也未能体贴得上,反而持己论愈坚。讲论过程中,编者更发现,严守中和新说的同学们意见也往往并不全同,反是差异颇大,各有高见。
古时朱张会讲,三昼夜不能合。于中和的问题,愚见是谈不拢不妨,谈不拢便不谈却害事。这次推出的中和讨论专题,已经收集了六七篇文章,其一为编者引发讨论的论文《论中和旧说的可贵处》,其后为切磋班的现场发言记录两三篇、其后为与天成君讨论中和问题的四封书信。我们也期待各位师友能以投稿形式参与到讨论之中,让这次专题讨论能以定于一是告终。(孙奥麟)

(一)
数年来,笔者对中和新说总不甚体己,对旧说反较亲切。自丁、曾二位老师命讲旧说后,我将新旧说皆细读了三四日,方才知道从前读得实在粗,对中和问题的重要性也一直忽略,此足以暴露平日涵养工夫之粗疏。年来丁老师数次问我的所学能否得一收摄处,我也曾漫然以“以道体为收摄”应之。此番或是有所为而命我讲,此种婉衷,我于准备讲稿时方有体会。于是不敢藏拙,借此机会尽呈陋见,望就正于各位老师和同学。
苏季明问:“中之道与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同否?”曰:“非也。喜怒哀乐未发是言在中之义,只一个“中”字,但用不同。”
伊川将“中”字解释为“在中”与“道之体段”两义,朱子将“在中”与“道之体段”两训分别开为新旧说,然而不论哪一说,于伊川全盘言语似终有不少抵牾。以目下学力所见,朱子对中和问题的理解,大体旧说与伊川同处少,新说与伊川同处多。伊川与朱子新说的同处,则在于都不肯认“喜怒哀乐之未发”为性,之所以如此安排,目的则在于从中拈出主敬存养的工夫。
朱子对于中和旧说的概括,在《答张钦夫第三书》中较为详细。
人自有生即有知识,事物交来,应接不暇,念念迁革,以至于死,其间初无顷刻停息,举世皆然也。然圣贤之言,则有所谓未发之中、寂然不动者,夫岂以日用流行者为已发,而指夫暂而休息、不与事物之际为未发时耶?
尝试以此求之,则泯然无觉之中,邪暗郁塞,似非虚明应物之体;而几微之际,一有觉焉,则又便为已发,而非寂然之谓。盖愈求而愈不可见,于是退而验之于日用之间,则凡感之而通、触之而觉,盖有浑然全体,应物而不穷者。是乃天命流行、生生不已之机,虽一日之间,万起万灭,而其寂然之本体,则未尝不寂然也。所谓未发,如是而已。夫岂别有一物,限于一时、拘于一处,而可以谓之中哉?然则天理本真,随处发见,不少停息者,其体用固如是,而岂物欲之私所能壅遏而梏亡之哉!故虽汩于物欲流荡之中,而其良心萌蘖,亦未尝不因事而发见。学者于是致察而操存之,则庶乎可以贯大本达道之全体而复其初矣。
朱子对于中和新说的概括,在《与湖南诸公论中和第一书》第四十九书较为详细。
按《文集》、《遗书》诸说,似皆以思虑未萌、事物未至之时,为喜怒哀乐之未发。当此之时,即是此心“寂然不动”之体,而天命之性,当体具焉;以其无过不失,不偏不倚,故谓之中。及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则喜怒哀乐之性发焉,而心之用可见;以其无不中节,无所乖戾,故谓之和。此则人心之正,而情性之德然也。然未发之前不可寻觅,已觉之后不容安排,但平日庄敬涵养之功至,而无人欲之私以乱之,则其未发也,镜明水止,而其发也,无不中节矣。此是日用本领工夫。至于随事省察,即物推明,亦必以是为本。而于已发之际观之,则其具于未发之前者,固可默识。
新旧说都引入了“寂、感”一对概念,然而,窃谓此两字于研究中和问题意义不大,反而颇有一种将思路滑至歧途的危险。《系辞传》言:
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
此言原本是讲占验之理,无思无为的是形而上的变化之道,寂然与感通的是形而下的人为,说人须寂然不为邪妄所动,才能至诚感格。周子曾以“寂然不动”说人之诚、“感而遂通”说人之神,此正是取其本意;程子又曾以“寂然不动”说中、以感而遂通说“和”;以“寂然不动”说心之体,“感而遂通”说心之用,此或属譬喻指示之语,然而总有将性或心说成有时而动的流弊。周程而后,此言的主语“易”字遂每每为理学家视而不见,“无思也、无为也”常用来说形下的心体,“寂然不动”与“感而遂通”,本来是因寂而感,寂感同时之意,却演变出了寂静感动、寂翕感张的意思。清儒刘沅也曾对此种化用有不解,说“明明言易,竟说到圣人心体上去。”愚见今日论中和问题,也似可以舍去寂感一句的各种解读,一来无此必要,二来措字失之毫厘,所指谬以千里,势必会带出许多不必要的窒碍。
《中庸》经文言“喜怒哀乐之未发”,观《遗书》、《语类》,程朱每言“喜怒哀乐未发”。将“喜怒哀乐之未发”缩写为“喜怒哀乐未发”,是将“之”看作虚字,然而,《中庸》开篇用字本极简省,这一个“之”字是否属于可有可无呢?细细玩味,有无一“之”字,二者的所指似乎不同。“喜怒哀乐之未发”,似乎是“能成就喜怒哀乐、本身却不在喜怒哀乐层面的东西”,一如“春夏秋冬之未发”指能成就春夏秋冬,本身却不在春夏秋冬这一层的元亨利贞之理,“喜怒哀乐之未发”也似指生生不已之性。相较而言,“喜怒哀乐未发”则语义单纯,特指“心未有喜怒哀乐”的状态。
譬如烛火亮则灯笼亮,性是不已的,心也必定是不已的。单就性言,性自没有未发时,其发用也没有强弱缓急之别。心之于性,好似浮云蔽日,心的发用则有个明昧精粗的动态,它虽然呈现出时时不一的动态,却也没有止息不发之时。唯独心性并提的时候,则可言性为未发,心为已发,此处大概也是子思立言的本意。
新说认为,人有一种喜怒哀乐未起而知觉朗然之时,所谓“思虑未萌、事物未至”之时。此种静穆清明固然人人都有体验,却未必好说此时没有喜怒哀乐,怕是喜怒哀乐皆较淡泊而已。七情虽然迭为心境的色调,然而不论破涕为笑还是乐极生悲,其间皆似不能容发。
心中斯须不和不乐,而鄙诈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须不庄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
《祭义》、《乐记》二篇皆有此一句,程子语录中也曾引此条。由此一言观之,心之本然似乎也不是无情,而是有个恬然之乐在。人静坐或体会夜气时,最易于见到此种恬然安乐处。窃疑乐之于人情,犹如土之于五行、白之于五色、甘之于五味,先须有个底子,然后木火金水、青红皂黄、辛酸苦辣才有个寄托之地。心之本情是乐,然后种种情感才有了舞台,得以你方唱罢我登场,或悲欣交集,或百感辐辏,交生出万千心境。孔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颜子在陋巷,则“不改其乐”,皆是此种气象。孟子又以“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为君子之乐,君子无一息愧天怍人,那么此乐便也无一息不存。倘若人心的本色是个欣欣然之乐,那么才有人便有心,才有心便有情,才有情便有乐,如伊川言“才思便是已发,才发便谓之和,不可谓之中”,终究难有个“喜怒哀乐未发”之时。
情不可断,那么意是否有断绝之时?在我则未有可信的体验,如果以理来推,则意也似无断绝之时。我曾有一二年的静坐经历,其间种种心气上的体验固然不无,意却似从未尝断,只是不断改头换面地出来蒙混而已。
心下所发出的意是一个接着一个,然而,是否有禅家所谓前念才逝,后念未生的间隙在?这一点,我也难于确知。以目下的所见,意固然不似川流之水一样流行不止却浑无界分,也不似檐下雨滴般前赴后继却彼此隔绝,意好似都带个小钩子,前一个意与后一个意彼此虽有界分,可一个意过了,它总要钩挂着下一个出来。由此观之,心下念念相继的意好似条无尽的锁链一般,它的各个环节彼此独立又不失为一体,诸多环节诚有大小粗细之别,却仍是牢不可破的。(此处说法只说到一头,后续会有修正。)
当睡眠之时,谋划思虑的意固然罕见,较为低级的意和生物性的意却总还是有的,它也是一心在记忆、躯壳与外物上感应出来的,感应到重大处,便形于梦境,感应到极重大处,则要从睡梦中惊觉。人才活,意便不可斩断,譬如电脑固然是用来运行程序的,然而开了机便不管它,它也定是在一直工作的。此理也是阳爻的穷上反下之理,阳气有消长而无有消尽,意有显隐而无泯灭。至于心理分析家所谓潜意识,往往不区别显性意识与潜藏意识的轻重、精粗、大小,甚至还要本末倒置,自然是不合道理的。
如果意也不能断,则“思虑未萌”之时也是没有的;至于“事物未至”之时,想来也没有,非止视听言动的小事相续不断,进德修业的大事也未尝须臾止息,何况孟子明言“必有事焉而勿止(‘正’作止之误,此处从孔疏)”。
《中庸》又言:“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愚意以为万般物类,有资格作“天下之大本”的,终究只有道体。而中和新说所谓“事物未至,思虑未萌,而一性浑然,道义全具”的“中”,说它是一个人的大本,或许还有得商量,以其作天下的大本,直观上总觉得有些不实、甚有些至以小援大的意味。
《中庸》又言“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此一句,对辨析前文“喜怒哀乐之未发”的所指究为何物甚是重要。朱子新说以“天地位、万物育”为人去致中和的效验,曾言:
“若致得一身中和,便充塞一身;致得一家中和,便充塞一家;若致得天下中和,便充塞天下。有此理便有此事,有此事便有此理。如‘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如何一日克己于家,便得天下以仁归之?为有此理故也”。
以“位”字说天地,自是说天位乎上,地位乎下一事,《易》言“天地设位,圣人成能”,是说天位乎上,地位乎下,圣人有以成能乎其间。《易》之言“天地设位”在先,子思不至于不读《易》,此处言“天地位”,当不会仅指天地间风调雨顺而已。
又“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与“致中和天地位万物育”也实有所不同。克己复礼是内圣造,天下归仁是王道成,克己复礼与天下归仁是体用关系,舜三年成都、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孔子为万世素王,凡此都是天下归仁的事实。然而,人致中和,固然能参赞化育,或勉强可说是“万物育”,至于“天地位”,则绝非人能为,且不说天地宇宙,只尧舜之于洪水,孔子之于衰世,皆有不可改易者。倘若解说成“张三致中和,则张三的天地位;邻家李四不致中和,则李四的天地不位。”如此却似甚勉强,也与实在道理不符。
《中庸》后文有一句话,可以用来参考此问题:
“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此处重重铺陈递进,若依中和新说的思路,最末子思本该言圣人“位天地、育万物”之实,然却只说到与天地并立为三便止。由此猜测,“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一句,在子思本意,或许也非人致中和的效验?至于天地本身是如何“位”的,《中庸》文本也有过详细的描述: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无穷也,日月星辰系焉、万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广厚,载华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万物载焉。”
天地之设位,子思明言是造化积聚使然,并无圣人致中和的极功介入其中。其实,关于圣人致中和的极功是何等情形,子思也有过具体描述:
“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
体味“律天时、袭水土,如天地、如四时、如日月”,子思似只说圣人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德如天地而已,并无一种“天地位焉”的本领。
窃以为,子思于“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处,只是先指出了个人的当然之理,后面则不止于人,子思更将此理推及于物,人固受性于天,天地万物也是各得其性,人能致中和,万物也能致中和,人时时可以去致中和,天地万物则有时而能致中和,这里是就其同处言。
“致中和”的“致”字,朱子取“极尽”之意,与后文天地万物之事有许多不协,前文已辨之。故而似乎宜取“达”、“造”之意,为其训更从容,且更可以扩人类与自然二界。人当然是可以主动去极尽中和之道,但天地万物却要坐待中和,譬如气化自有未能凝结天地之时,及凝成天地,也定有“天地不交而万物不兴”之时。窃以为以“致知”的“致”字是训“达”意较顺,此训从“物格而后知至”上也可见。
同样,《中庸》言“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既然说是“天下之大本达道”,便不只是人之大本达道,这是说人与万物的同一处。至于人物的差异处,在于物虽没有邪妄,却往往无能破除所气秉的拘束,一如金不会自去纯、羽不会自去白。此拘束,需要人力参赞天地之间方能济之;人作为一物,也自有气禀之拘,更多了一份人欲之蔽,看似反不如物,却因有虚灵之心而有“修身以道”的自觉,此间的功夫,子思于后文讲诚处自有大段解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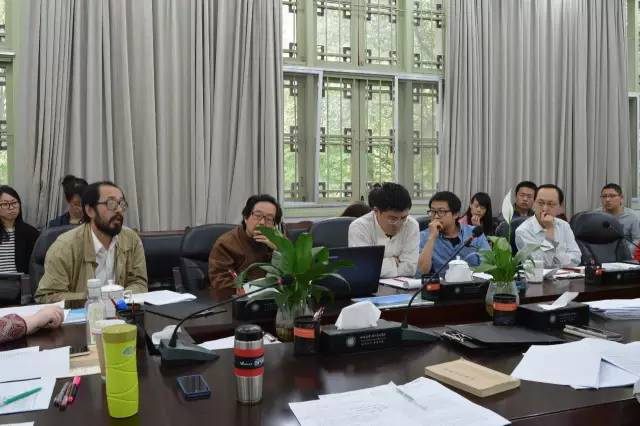
(二)
倘若不认中和新说,最易为学者所诟病的,是致知之外少了一份涵养工夫,与伊川“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的教人路数抵牾。
孔学一以贯之,涵养与进学同须贯彻终始,此二事并无可疑。然而两者并观,则涵养与进学也须一贯,不能没有个本末,否则便是二以贯之。在这里,我倒不乏一些陋见,不知道是否合理。
《大学》是一以贯之的学问,是学者入德之门,圣人的极功也在其中。然而《大学》唯以格物致知为源头,如丁老师《大学条解》所言,“格物一气到底,则天下平矣”。将一部《大学》压缩到最精,则是孔子一句“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其中也不见中和新说所谓思虑未萌时的涵养工夫。反之,若以中和新说观之,《大学》只是教人一条腿上的工夫,格物致知而外,同极重要的涵养功夫则须人自去从《中庸》中体贴出来。为难的是,《中庸》文本又并无一语明确言及中和新说所发明的、未发时的存养工夫,治国九经之类反而说得详细。且新说所指明的中和之学,高明博学如朱子者也须四十岁而后方能悟及,我辈此生何可企盼?圣贤之书,多是拟一中人而对之言,圣贤的涵养工夫,果如是之难解乎?
其次,中和新说固然认为“敬”字须贯穿动态,却也认为有一个无事时存养的、甚至思虑未起时的敬。孔门说敬,只说“执事敬”、“行笃敬”,孟子说敬,则是“必有事焉而勿止,心勿忘、勿助长”。持敬似乎都是在动态中持的,动态各种各样,唯独没有一个静态的持敬。才要有个收敛提撕的意思,纵然只是轻轻照拂一下,便又是作意了。可以说,未去持、未去主时没有敬,才去持、才去主时,便是已发。
如果可以不负责任地猜测,持敬的工夫于《大学》并非不存在,而是在诚意正心二目上,其本源处、实下手处则在诚意。愚见意诚就是敬,诚之就是持敬,意意皆诚就是敬而无失。正心一节上,有所忿懥、恐惧、好乐、忧患,也须以诚意功夫为把柄对治。
为方便参考,不妨先将诚意一节的传文附上:
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
值得注意的是,《中庸》于存养工夫极言“诚之”之道,《大学》也于此处说出“诚中形外”;《中庸》于存养处说出慎独工夫,《大学》也于诚意处说出慎独工夫,凡此或不是巧合偶然,或许两书所载只是一样功夫?
为阐明我的思路,这里我援引并改写一下《知有统分论》的开头几句:
乾坤并列,然统言之乾包贯坤;阴阳交错,然统言之阳包贯阴;动静互根,然统言之动包贯静;天地定位,然统言之天包贯地;仁义对举,然统言之仁包贯义;知行并兴,然统言之知包贯行;凡此本源大目,皆一身两在而无间,指首该尾而无余,统言分说,贵无罅隙。此义吾儒固有之也,独进学与涵养不其然乎?
从乾坤大义上推,似乎不妨说进学包贯涵养,致知包贯持敬,然而,涵养不可以包贯进学,持敬不可以包贯致知。若以《论语》“学而时习之”一言括之,则致知一路是“学”,涵养一路是“习”,持敬或诚意便是“时习”。学可以包贯习,也可以与习并列看,但习不可以包贯学,也不可离学而独存。若无进学,所持的是个空空的敬,甚至可以是荒谬的敬。持空空之敬的是和尚,持荒谬之敬的是香客,凡此都非圣门之所许。
敬与持敬是有区别的,一者是心之状态,一者是存养工夫。前贤往往不甚区分,要人自见地头,在今日论中和问题,则宜于区别。另外,我与朱子对“诚”字的解释也稍有不同,大体朱子以“诚”为“实”的意思,愚见“诚”固然包含了“实”的意思,但如果以“实”言“诚”,则不足尽诚之全体,更只滑到了一个“信”字地界。“诚者,实理也”、“真实无妄之谓诚”这些解释自然没错,然而每每易被人误解为“泊在真实无妄处就是诚”、“诚是理之实”,凡此总是静态的,没见到性的动态;只见到性的“不易”一面,未及性的“不已”一面。朱子尝明言道理是“所以然而不可易,所当然而不容已”,所以我窃不自揆,将“诚”字定义为“实理流行”四字,以为此可兼“不易”、“不已”两面。如此,则“诚者天之道也”、“诚则无事矣”之类也能得到一个更圆满的解释。
由此再推,所谓“意诚”,说念念都是实,不如说念念流行都不违实理流行。而诚其意或者主敬,就是每令道心为之主,心下好似有一个检票员一般,将每一个要进站的乘客进行排查,有票的则进去化为实践;没票的则无不剔出,不使其化作戏言妄动之类。
若先无一个实理流行的意,便不会有要惺惺、要持敬的念头。意的来源可以说有两个,即道心之发和人心之发,然而,就根本而言,所有的意只是一个性体上发出来的,譬如一个源头的水分作清浊两股,这两股后来又合并成半清不浊的一股,这就是人心下所能体会到的意。
朱子又有《敬斋箴》,是朱子一生敬学具体而微的呈现。
正其衣冠,尊其瞻视。潜心以居,对越上帝。
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择地而蹈,折旋蚁封。
出门如宾,承事如祭。战战兢兢,罔敢或易。
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属属,罔敢或轻。
不东以西,不南以北。当事而存,靡他其适。
弗贰以二,弗参以三。惟精惟一,万变是监。
从事於斯,是曰持敬。动静无违,表裏交正。
须臾有间,私欲万端。不火而热,不冰而寒。
毫厘有差,天壤易处。三纲既沦,九法亦斁。
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敢告灵台。
《敬斋箴》字数不多,却将主敬工夫的方方面面都照顾到了,其义理,大约是将一个“敬”字四面撑开。有数句说到了“主一无适”一面,如“当事而存,靡他其适”、“惟精惟一,万变是监”之类;有数句说到了“戒慎恐惧”一面,如“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属属,罔敢或轻”之类;有数句说到了“齐整恭肃”一面,如“正其衣冠,尊其瞻视”、“足容必重,手容必恭”之类;有数句说出了“专主天理”的意思,如“潜心以居,对越上帝”、“动静无违,表裏交正”之类。
然而即《敬斋箴》看,“敬”字功夫实在难于以“主一无适”四字概括,伊川对患于思虑纷扰的苏季明说敬,也只说“莫若主一”,只说“主一”是个紧要处。朱子说出了主敬的四面功夫,却似并未点出四者的收摄处、发端处何在。故而阳明批评主敬若是“主一无适”,则“好色便一心在好色上,好货便一心在好货上”也是敬,然而其人又说“主敬是专主一个天理”,又把下手投足的细密工夫全都丢了,四面只留下了那个不能孤立存在的一面。
愚见唯有“诚意”功夫可以照顾到“主一无适”、“专主天理”、以及“戒慎恐惧”、“齐整恭肃”四面。譬如一把雨伞,诚意是雨伞的杆子,须推着它,才能将主敬的四面同时支撑张大。诚意就是主敬的根本处、实下手处,有这个把柄在手,则四面自然都能照顾到,一旦丢了这个把柄,则主敬的四个面向也无从寻觅了。《中庸》言:“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故君子诚之为贵。”这里面的“诚之”,想来就是主敬的工夫,可以肯定的是,这个“之”的最小单位,只能是意。
之所以具体的涵养要从诚意上入手,因为意是人内外交通的枢纽,是知行互相转换的中转站,是人心初能体验觉察到的精细运动。人的履践都是意带动的,好好色、恶恶臭、戏言、戏动都是意的兑现,此处做到极致,想来便是“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
颜子“无形显之过”,想来正是诚意功夫好,或也不是没有不合礼义的意,只是这一两个妄意才出来就被剔出掐灭;至于三月而稍违仁时,则或因为有一两个混入的妄意未能及时察觉,发而为行动,然而颜子之心此时又自会生起个勿自欺的意,使自家不远而复,重又恢复意意相续的天理流行。至于阳明说致良知,未尝不是见得一隙光明,却又把人人都作颜子看,非但极不周遍,又因其人以良知为重而以格致为轻,反而使人人丧了做颜子的本钱。求复本心而颠倒本末,在《易》谓之“迷复之凶,反君道也”。
或有人谓“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诚意是致知之后事。逻辑上的顺序固然是格致诚正,然在人也是“莫不有其已知之理”,故而人不必先去格物然后可以做诚意工夫,人是必有事焉,于诚意,勿不耘其苗,亦勿助长可也。使胸中已明的全部义理皆无折损地经由意之诚而付诸实践,这便是诚意之全体大用,也是主敬之全体大用。由此观之,诚意工夫可以时时来做,不该、也本不当有间断。做到了圣贤,想来也只如飞机经过滑行而起飞,诚意变成了诚,主敬变成了敬,勉强而来的原来是我所固有的。
千说万说,愚见人是没有诚而不敬之时,也没有敬而不诚之时。实际上,程朱虽未说诚意就是主敬,对诚意与主敬的同一处也有所见,下面引若干条语录,可供参考。
敬是闲邪之道。闲邪存其诚,虽是两事,然亦只是一事。闲邪则诚自存矣。(此伊川言,以下为朱子言)
问:“‘诚意、正心’二段,只是存养否?”曰:“然。”
或问:“中与诚意如何?”曰:“中是道理之模样,诚是道理之实处,中即诚矣。”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少个敬不得。(此处若以主敬为诚意则极贴切,以主敬为诚意之外的工夫,则有二以贯之之嫌。)
问:"敬何以用工?"曰:"只是内无妄思,外无妄动。"(无妄,诚也;无妄思,诚其意也。)
圣贤言语,大约似乎不同,然未始不贯。只如夫子言非礼勿视听言动,"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言忠信,行笃敬",这是一副当说话。到孟子又却说"求放心","存心养性"。大学则又有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至程先生又专一发明一个"敬"字。若只恁看,似乎参错不齐,千头万绪,其实只一理,只是就一处下工夫,则馀者皆兼摄在里。
综上所论,大概《周易》于乾卦说个实理流行之诚,自坤卦始言“敬以直内”,其所以敬者,则不在坤卦而在乾卦,此处也足见“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之义;《大学》有“敬”字却不深究,于存养则开诚意一目详说;《中庸》有“敬”字而皆作“尊敬”解,于存养处则反复详言一“诚”字;《通书》则是极言诚而不言敬,于存养处,则说“端本,诚心而已矣”。愚见程子首言敬,或是就着圣贤训诫反推出的一种工夫,为其学养深厚,故而与《大学》所讲的诚意工夫吻合,并无失处,然而主敬舍诚意则无把柄,诚意贯主敬则有余裕。朱子立新说为持敬开路,愚见却仍以旧说为是。
讲稿草就,散漫无统,且实未写完,其中的见解也多未自信,还望各位师友有以教我。
责任编辑:姚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