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文明】市场和国家都应充分尊重家庭——驳陈志武教授
 |
唐文明作者简介:唐文明,男,西元一九七〇年生,山西人,北京大学哲学博士。现任职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著有《与命与仁:原始儒家伦理精神与现代性问题》《近忧:文化政治与中国的未来》《隐秘的颠覆:牟宗三、康德与原始儒家》《敷教在宽:康有为孔教思想申论》《彝伦攸斁——中西古今张力中的儒家思想》《极高明与道中庸:补正沃格林对中国文明的秩序哲学分析》《隐逸之间:陶渊明精神世界中的自然、历史与社会》等,主编《公共儒学》。 |
原标题:市场和国家都应充分尊重家庭
作者:唐文明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表,原载共识网
时间:西历2016年7月4日
共识网编者按:近日,知名经济学家、耶鲁大学金融学院教授陈志武接受了FT中文网的专访(点击此处阅读),他认为:“儒家文化过于强调家族对个人的保障和救济,因此抑制了金融市场和福利政府的发展。半个世纪以来的技术进步,将让市场在几千年来第一次战胜儒家。”儒家与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真的势不两立吗吗?持守儒家立场的学者对此有何看法?本文系清华大学哲学系唐文明教授对陈文的回应,经作者授权共识网首发。转载请注明来源。

问:最近耶鲁大学金融学院陈志武教授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记者采访时认为市场最终会战胜儒家,您怎么看这种观点?
答:我在网上看到了这个采访的内容。应该说其中讨论的主要问题是真实的且非常重要,但陈志武教授的一些观点却是经不起推敲的。

问:陈志武的观点似乎是,儒家与市场是对立的:有儒家则无市场,有市场则无儒家。这是我看了对他的采访后留下的整体印象,可能也代表很多人对那篇采访的观感。我一方面觉得这种看法有点流于简单,另一方面又觉得他言之成理,您认为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答:儒家伦理对于现代市场经济或作为狭义的经济制度的资本主义,是存在着不可化解的张力还是能够成为一种精神动力,这是学术界早已注意过、讨论过的一个老话题。我们知道,在东亚经济崛起之前,大多数现代学者都认为儒家伦理是阻碍市场经济的,自然也不可能为资本主义提供什么精神动力。日本以及后来的“亚洲四小龙”的经济成就使得很多学者有了新的看法,概而言之,他们提出了“儒家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个韦伯式的问题,并试图得出肯定的回答。虽然历史学、哲学和社会科学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对这个问题的理性探究,但是所取得的成果却不很可观。
历史学方面的研究可以余英时的《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为代表,如果你仔细阅读他的书,你会发现其实他的结论是很可疑的。特别是对于儒家伦理与明清以来的商人精神,是否存在一种他的解释框架内所刻画的动力关系,你会看到其实他自己也感觉到无法坐实,所以在书中非常谨慎地使用了一些或然性的修辞。
哲学方面的理论探究也同样乏善可陈,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对儒家伦理的理解和刻画在现代人文主义思潮的遮蔽下出现了很大问题,特别表现在,未能正确理解儒家自身的超越精神,未能充分理解孝的统摄性意义,从而在一开始刻画这个问题的内在结构与要素时就已经偏离了正确的方向。
西方学术界对这一论题的刻画和回应主要表现在他们对亚洲价值观的概括和评判上。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印裔学者阿马蒂亚.森为例,在1996年他曾说:“近来赋予儒家伦理、武士文化和其他动机的作用,使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说看起来像是退役运动员的喃喃自语。”与这种充满嘲讽口吻的刻画相应的核心看法则是这样的明确表态:“我本人对鼓吹亚洲价值观奇迹的理论甚为怀疑。”首先需要指出,这种反驳针对的主要是英语学术界通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而得出的关于亚洲价值观的概括,其要点在于将亚洲价值观刻画为一种权威主义的文化,通过对秩序、纪律、效忠等理念的强调来谈论亚洲价值观对资本主义的成功可能做出的贡献。对亚洲价值观的这种反驳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回到了东亚经济崛起前的流行观点上,即认为,儒家伦理不是且不可能是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精神动力,而是且必然是其精神阻力。我留意到的一个现象是,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更多的学者回到了这种旧有的观点,而将亚洲价值观看作是某些一厢情愿者的喃喃自语。通过这个简单的梳理,你可以看到,陈志武的观点基本上在我刻画的这个思想脉络里。
问:您提到这项研究乏善可陈的原因在于研究者没能正确地理解儒家伦理,包括将儒家伦理简单地理解为一种权威主义,您是否是在暗示,如果这一点得到纠正的话,关于儒家伦理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可以得到肯定的回答?
答:很难简单地回答是或不是,首先是因为,中文学术界关于韦伯式问题的探究与英语学术界关于亚洲价值观的讨论虽然都将问题归到儒家伦理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上,但实际上各自的侧重点非常不同,甚至可以刻画为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一个是比较标准的韦伯式问题,即,儒家伦理能否为一种理想型意义上的资本家或商人提供充分的精神动力?另一个更多关系到政治层面,即,一个儒家思想主导的政治社会能否保障和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
对于前一个问题,我觉得基本上可以得到肯定的回答,尽管停留于那样的提问方式远远不够。以往所有的讨论都没有充分重视孝的统摄性意义和孝的美德在这个主题上的重要性。孝的含义不仅在于善待父母,所谓能敬、能养,更在于荣耀父母,所谓“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这是儒家独特的荣誉观念,植根于孝的美德。这种独特的荣誉观念会构成一种精神张力,促使人追求现世的成功。当发财致富越来越成为一种颇有诱惑力的人生选择,孝的美德就能为经商提供一种动力性和规范性的精神力量:为了荣耀父母而致力于做一个成功的商人。
至于像陈志武那样认为儒家和基督教一样重义轻利,而又没有像基督教那样在商业伦理问题上经过了重大调整,在理论认知和历史认知上都有很大偏差。在利的问题上儒家一直采取非常务实的态度。儒家义利之辨的实质是以义正利,并非单纯轻视利,特别是和基督教、佛教等注重天国、来世的宗教相比,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所以某种意义上儒家根本不需要类似于基督教或佛教那样的转折或调整。余英时讲“中国近世宗教伦理”的入世转向时是从禅宗讲起的,在讲儒家时就转而讨论上行路线到下行路线的转折了。即使以“正其义不谋其利”为传统儒家的主流思想,余英时也已经指出了明代以来出现的儒家内部在商业伦理问题上进一步的理论调整,比如王阳明的“新四民说”、“贾道冥合天道”的思想以及明清之际出现的“儒家治生论”等。陈志武如果对儒家的思想稍微多一点点了解,或者读过这本我认为并不太成功的书,也不会作出那么轻率的断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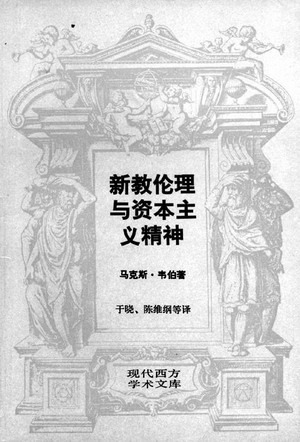
问:那资本主义为何没有在传统中国发展起来呢?韦伯将之归因于儒家伦理,难道没有一点道理吗?
答:这个问题非常复杂,因为儒家伦理涉及很多方面,而且我们刚才已经谈到,存在不同层次的问题。在此我只想说明一点,资本主义没有在传统中国发展起来,有很多原因,将之完全或主要归因于儒家伦理可能不太恰当。实际上,韦伯命题——新教伦理为西方资本主义提供了精神动力——如果被放大地理解,也是不合适的。比如,就我最近读过的两本思想史著作来说,阿尔伯特.赫希曼在《欲望与利益——资本主义之前的政治争论》中展开的思想史考察和提出的看法在我看来远比韦伯重要;阿里扬德罗.A.夏福恩在《信仰与自由——晚期经院哲学家的经济思想》中则指出,中世纪晚期一些天主教经院哲学家、特别是一些西班牙经院哲学家,是后来“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先驱。
问:如果儒家伦理意味着一种权威主义的文化,那么,儒家伦理与资本主义发展所要求的市场制度及其自由精神就难以协调。假如这就是陈志武的观点,您不是要质疑他的推理,而是要质疑他的前提,对吗?
答:首先,自由与权威并非像一般人所认为的那样非此即彼。我当然也不同意把儒家伦理刻画为一种权威主义的文化,特别是就大多数人赋予“权威主义”这个词的实际含义而言。这或许就是陈志武的观点,和那些批评亚洲价值观的学者没有实质差别,但这并不是他在那个采访中的主要关切。那个采访有趣的地方在于他对社会结构的古今之变与儒家伦理的关联性的刻画与断言。一方面,他承认儒家伦理在古代中国的重要性,特别关联于由儒家伦理所维系的家庭和家族制度,而且认为儒家在宋代、清代都成功地回应了与市场化有关的社会变迁所带来的挑战。
另一方面,他认为,现代以来、特别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技术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变迁,“打破了中国两千多年所依赖的家族体系”,从而导致了这样的状况:“市场化和社会福利已经成为现代中国人主要依赖的安身立命、规避生活风险的两种方式,家族和原来的亲情网络的作用则越来越低了。”正是基于这种历史刻画,他才提出“这一次市场会战胜儒家”这种危言,而论证的要点则被他刻画为,“儒家文化过于强调家族对个人的保障和救济,因此抑制了金融市场和福利政府的发展。”
这当然是个非常有意义的话题。问题在于,家族在中国历史上有不同形态的变化,但无论如何变化,家庭——我这里指的是由夫妻、父母与子女、兄弟姐妹三种人伦所构成的小家庭——从孔子的思想诞生以后就一直是中国社会的基石,而且中国人的伦理生活一直深受这种家庭观念的影响。即使是现代,比如说当下,中国人仍具有很深厚的家庭观念,在很多方面与西方人形成明显的对比。一言以蔽之,中国人安身立命的主要场所是家庭,过去如此,现在如此,我相信将来也还是如此。这里的关键并不仅仅在于物质层面上的保障和救济,而是涉及中国人对于“何谓美好生活”的真切回答。声称市场或国家能够代替家庭成为人的安身立命之所是一种拂人性、逆人情的论调,我相信很多中国人会同意我的这个看法。
陈志武观点的荒谬性可从他举的例子中分析出来。比如他提到我们吃饭,一般会请长辈先动筷子,在他看来这是一个资源配置的问题。如果按照他的市场逻辑,以后吃饭应当是谁有钱谁先动筷子,等我儿子比我有钱了,我得等他先动筷子我才能吃。将这个市场逻辑贯彻到底,贯彻到我们生活的全部领域,一切都遵循市场逻辑,这是我们期望的生活吗?我想绝大多数中国人会说不是。那实际上意味着生活世界的全面殖民化,被市场殖民,或者像马克思说的,被金钱奴役,被资本异化,决不是我们所欲求的生活。“长辈先动筷子”的常识恰恰意味着我们对于生活的共同理解。这对一个政治共同体来说是弥足珍贵的东西,恰当的政治主张应当基于这种共同美善观念而提出。
重视家庭的价值并不意味着排斥市场和国家。相反,家庭能从市场中获取成就自身、繁荣自身的财富,也能为市场提供守规则、有教养的商人。同样,家庭能从国家那里得到正当的保护,也能为国家提供具有仁爱与正义美德的公民。说家庭承担较多的保障与救济意味着阻碍了金融市场和福利国家的发展,这真是一种本末倒置的论调。至少,家庭、市场和国家都有其独特的领域,都有其独特的目的和规则,彼此之间不应当僭越。更进一步说,市场与国家能够给人提供的保障和救济应当基于对家庭的充分尊重,决不应当成为对家庭制度和家庭价值的破坏性力量。你知道有一种国家主义思潮,在中国思想界常常被归在左派名下,而与之相对的自由派基本上是市场至上主义者,我想也就是陈志武所青睐的市场派,至于左翼自由主义,大概是以市场加福利国家为他们的核心主张。如果这些就代表了目前中国公共话语领域中主流的政治观点,那么,我认为被归为左右两派的这些主张其实都没有很好地体察民性、民情。总而言之,市场的发展与国家的建构都不应当以破坏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代价,而应当成为维护和实现我们的美好生活的恰当手段。
陈志武的观点也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提示,即,市场和国家,就其本性而言,都是倾向于过度扩张的,我们应当思考的恰恰是如何限制市场和国家的过度扩张。其实,左右之争已经将这个主题呈现出来了。左派常常强调应当建立强大的国家以限制过度市场化带来的问题,特别是因贫富差距拉大带来的不平等;右派则往往呼吁限制政府与国家,为市场留下足够的地位。关于这个主题,我认为在儒家传统中还有更多的思想和文化资源有待挖掘,儒家伦理还能发挥更大的作用。这就涉及儒家在社会伦理、政治伦理等方面的主张了。
前面我曾提到政治层面的韦伯式问题,即,一个儒家思想主导的政治社会能否保障和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忽略这个问题在提法上的不足,我想首先需要注意的是,儒家思想主导的政治社会认可市场的价值、尊重市场的规则。从历史经验看,记载在汉代《盐铁论》中的贤良文学代表当时的儒家,他们特别强调国家不应当通过自己经营工商业而与民争利、与商贾争利。这个看法的前提恰恰是经孟子特别表达过的义利之辨。就是说,义利之辨恰恰是儒家尊重市场的理论基础。这其中的关键在于,儒家认为,国家应当超越市场,不仅要维护百姓、民众的普遍利益,而且要以捍卫、促进他们的美好生活为根本鹄的。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古代中国——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以儒家思想主导的政治社会——一方面通过有关分配与再分配问题的种种制度安排以保障全民的利益,另一方面则非常重视人伦教化的作用。就经典中的立意而言,井田制和学校制是儒家平等主义主张的两大基本制度,但实际的制度创新和政策发明远远不止于此,以至于康有为的弟子陈焕章在近代思想史上第一次使用了“儒教社会主义”来概括儒家的政治、经济主张。

问:那么,依据儒家经典,会有一种什么样的保障和救济理念呢?毕竟,市场或福利国家所带来的保障也是我们可欲的,而且或许还能减轻家庭的负担。
答:在这一点上陈志武说的基本上没错,对于保障和救济的承担者,儒家认为合理的次序应当是:家庭、国家和社会。首先是家庭,这是非常自然的。在家庭无法承担的情况下,国家应当承担。经典中说要让“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其中的鳏、寡、孤、独都指向家庭生活不幸的人,也暗示国家的责任应该在家庭之后。罗素曾经注意到,现代国家在功能上试图取代过去父亲的角色,这种倾向在福利国家的概念中显示得更为明显。而无论是广义的现代国家,还是在西方已经实践多年的福利国家,其缺失和弊病也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至于说市场和国家提供的保障和救济能够减轻家庭的负担,这恰恰是家庭所期望的,但不必也不应走到破坏家庭、破坏人伦的地步。事实上市场和国家所能提供的保障和救济也能够与儒家人伦理念主导下的家庭共存,只要其保障和救济是从家庭的整体利益出发而不是从单个人的利益出发加以考量。说到这里,我想你应该很清楚了,陈志武刻画的市场派与儒家的争论其实质仍然是过去我们讨论过的那个老话题:是伦理中的个人和基于伦理的国家,还是原子化的个人和基于契约的国家?前者当然是儒家所主张的,但其典范的理论建构和实践开展尚未完成。
问:所以您不认为这一次市场会战胜儒家?
答:如果经过反思的儒家伦理意味着大多数中国人对于美好生活的核心理解,那么,我反倒是相信,无视这种核心理解的种种市场主义或国家主义主张必将在实践中被挫败。在过去的不同时代儒家都面临过各种各样的挑战,也都做出了成功的回应,以至于一直延续到今天。经典之所以为经典,文明之所以为文明,其力量由此可见。当然,现代以来儒家面临的挑战比以往的都要大,如果只从一百多年的短时段看,可能会觉得在现代性的大趋势中儒家难有复兴之途。如果放长时段看,可能就不至于那么悲观了。只要我们怀着赤诚的信念,让经典真正进入我们的生活,带着新的问题主动接受经典的指引,在经典的指引下去思考,去践行,我相信,文明的活力一定会再次恢复,我们的文明一定能够再次获得新生。“不学狂驰子,直在百年中!”这是陶渊明《拟古》诗中的一句。这句诗在陶渊明那里颇值得玩味,背后有一个基于宏大理想的历史观,但又决不意味着走向浅薄的乐观主义,我想,这句诗也适用于我们这里所讨论的话题。
相关链接
【陈志武】这一次市场会战胜儒家
http://www.rujiazg.com/article/id/8496/
【上一篇】【章翼】弘毅知行会历史小记
【下一篇】【马培路】为往圣继绝学
作者文集更多
- 唐文明 著《隐逸之间:陶渊明精神世界··· 02-17
- 李天伶著《誓起民权移旧俗——梁启超早期··· 09-03
- 【唐文明】论孔子律法——以《孝经》五刑··· 04-07
- 【唐文明】定位与反思——再论张祥龙的现··· 12-29
- 唐文明 著《极高明与道中庸:补正沃格··· 09-15
- 【唐文明】三才之道与中国文明的平衡艺术 01-06
- 歌曲孔子版《孤勇者》(唐文明填词并注··· 09-09
- 唐文明 著《与命与仁:原始儒家伦理精··· 07-21
- 【唐文明】敬悼张祥龙老师 06-09
- 【唐文明】沃格林与张灏先生的中国思想··· 05-27
微信公众号
儒家网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

微信公众号
儒家网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