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东】走出由“普世”观念带来的困境
 |
刘东作者简介:刘东,男,祖籍山东峄县,西元1955年生于江苏徐州,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学专业博士。先后工作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北京大学中文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现任浙江大学中西书院院长、敦和讲席教授。创办和主持《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人文与社会译丛》两大图书系列,以及《中国学术》季刊。著有《再造传统:带着警觉加入全球》《自由与传统》《天边有一块乌云:儒学与存在主义》《国学的当代性》《德教释疑:围绕<德育鉴>的解释与发挥》等。 |
走出由“普世”观念带来的困境
作者:刘东(清华大学国学院副院长、教授)
来源:《读书》2016年8期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七月初一日丁巳
耶稣2016年8月3日
编者按:庄子《逍遥游》开篇几个故事引发的小大之辩,原意是讲小者和大者的区别,小者拘泥于自身狭小的眼界,无法懂得大者高远的境界。后来,郭象将小大之辩解释为大小各有其性分,各自性分得到满足,彼此都没有什么可羡慕的。在这个全球化的复杂时代,如何思考不同文明、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亦可以小大之辩为起点。刘东通过“大空间—小空间”的框架,辩证地剖析了文化的存身之本以及文化间的相处之道,向我们挑明这样一个原则:从来都没有任何一个具体的文明,在人类发展的任何一个有限阶段,就有权认定自己是绝对或天然地具有“普世”性。
“大空间”与“小空间”走出由“普世”观念带来的困境
晚近以来,我先是几乎脱口而出地,但此后又是念念不忘地,提出了所谓“大空间”和“小空间”的理解框架。而开诚布公地、开宗明义地讲,这个框架的提出,首先就是为了避免以往在普世主义—特殊主义、绝对主义—相对主义之间所遇到的各种纠缠与陷阱。早在二十多年前,我就曾在《文化观的钟摆》一文中,描绘过在这两者之间的左右为难。
正是鉴于这样的困扰,我这一次毋宁从传播学的意义上,再提出一种“价值中立”的框架,希望它能从思想的出发点上,就排除掉对于作为绝对观念的“普世”价值的执迷。也就是说,为了防范任何个体都只能占有的、相当短暂的历史时间对于他们各自认识所产生的影响或误导,这个框架想要预先就阻止人们去坐井观天般地,只是从自己那个时代的受限眼光出发,便对某种观念进行全称的肯定。
在这个意义上,它就是要用一把新的“奥卡姆剃刀”,来切除人们那种不由自主的做法,即把自身所占有的相当有限的时空,视作了通用于古往今来的普遍历史时空。这意味着,哪怕对于那些已被当代人普遍接受的价值——包括所谓的科学与民主、自由与平等——这个框架仍要预先就从方法论上指出,就算它们看似已经很接近具有“普世”的性质了,而且也确实在调节和校准着当代人的生活,但它们仍然未必就是“普世”的。

我所以要发出这样的思考,相当一部分原因在于,在这类“大空间”得以形成的过程中,正如米歇尔·福柯所精辟地读出的,从来都并非单纯是由话语在起作用,也同样有权力在起作用,而后者或隐或现的强势存在,就难免要妨碍我们去直面赤裸裸的事实和真理。——此外,由于这种总是居于主导位置的、从小就令人们耳濡目染的,且暗中会受到权力支撑的话语,它作为人们基本的教育背景,作为马克思所讲的那种意识形态,一般都潜伏在思想的地平线之下,也就构成了人们往往并不能反省到的、文化上的“前理解”。
比如,曾经在很长的历史阶段中,其实蒙古人和阿拉伯人,都处在这种国际大空间的核心地位。再比如,也曾经在很长的历史阶段中,亚伯拉罕宗教的各种变态形式,也都处在这种国际大空间的核心。然而,一旦时过境迁,或者一旦等到那种话语背后的权力衰落之后,其实也没多少人会继续认为,像那种确曾被普遍奉行过的价值,还会具有怎样的“普世”的意义;相反,他们往往还会用“恐怖统治”或“黑暗世纪”这样的语词,来描述那个曾经“普世”过的政治空间或价值系统。
当然,这样的国际空间作为一种历史的遗产,仍是由当代的西方世界来取而代之了,而且,它对于当代人的文化心理,也仍然具有类似的覆盖作用,而且也肯定不会是毫无道理的,所以很容易使之产生一种“普世”的错觉。不过,也正因为这样,我们就必须尖锐地挑明这样的原则:从来都没有任何一个具体的文明,在人类发展的任何一个有限阶段,就有权认定自己能从“经验上升为先验,心理上升为本体,历史上升为理性”(借用我对李泽厚老师哲思方向的概括),从而是绝对或天然地具有“普世”性。
从“文化圈”及其传播的角度来看,任何较大的文化空间的形成,从来是源于较小文明的相互接触,乃至边界叠加。“小大之辩”从来都是相对而言的。一方面,如果在其外部不存在更大的空间,一个文化空间就未必会意识到自己的“狭小”或有限;而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各个较小空间的相互叠加,也就不会在它们所共享的那个部分,基于富于生产性的文化间性,而形成较为阔大的文化空间。

比如,作为中国主体的华夏文明,是由所谓“炎黄子孙”来共同承当的,可在远古的时候,其实黄帝一族和炎帝一族,却本是你死我活的竞争对手。然则,正因为文化的接触与融合,这个华夏文明也便在文化冲突的过程中,经由原本两个较小空间的叠加而形成了。再比如,回到雅斯贝尔斯所讲的轴心时代,实则在那个至关重要的公元前五世纪,那几个差不多在同时产生的世界性文明,也都表现为经过了反复叠合的、由其内部的单元所共同支撑的、范围较为阔大的文化空间。
同样的道理:到了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文明对话之所以对我们如此重要,也如此致命,也正是因为当年的这几大轴心文明,又开始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彼此的接触、叠加与组合。换句话说,大家休要只为文明间的冲撞而惊诧忧心,实则这个“世界史”只有走到了今天,才真正算是在开启“全球史”的进程。
但又正因为,如今再次开始接触与叠合的文明,都曾属于过去时代的轴心文明,都曾拥有既各不相同又举世公认的伟大圣哲,所以,虽说在这个全球化的起始阶段,西方世界仍自拥有强大的权力,在支撑它的看似“普世”的话语,然而,又毕竟不能只靠它的权力本身,就来覆盖这个空前广大的全球空间。果真如此的话,那就不再是基于彼此投合的相互叠加了,而只是势必要引起激烈反抗的纯然占领,或者是一种文明在全球范围的机械复制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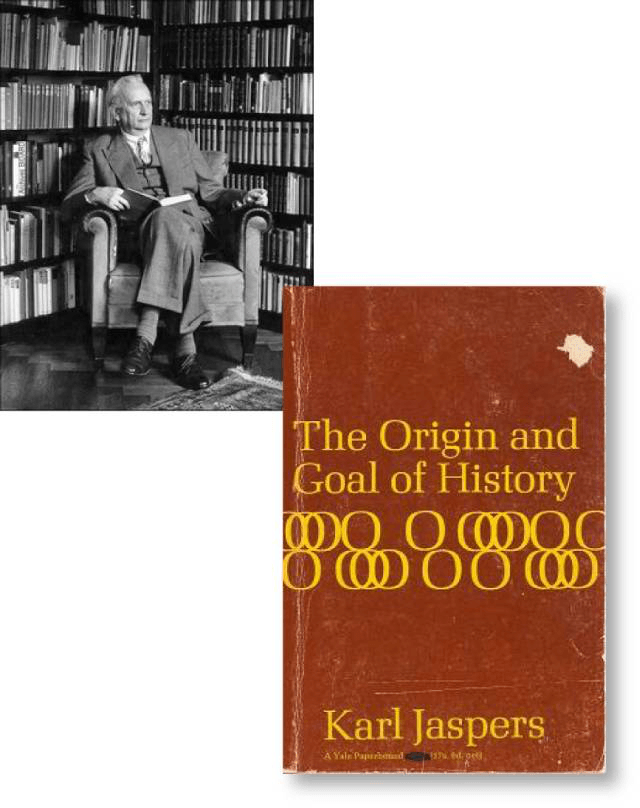
卡尔·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
必须充分意识到,只有当各个小空间中的文化主体,经由主动的诠释而认可了来自外部的价值,那些小空间才会焕发出足够的积极性,去跟外部的文明进行部分的叠合与重组,从而,那种被双方乃至多方认可的价值,才会在文化心理上真正地隶属于国际大空间。也就是说,这里所讲的空间叠合,绝对不可能是纯然机械的,或者纯粹强迫的,而只能是在积极诠释的基础上,贴合着另一小空间中的潜在倾向,而被创造性地激活起来,或者被自然而然地发明出来的。
由此综合而言,一方面,如果从大空间的角度来看,它必须仰仗来自小空间的文化动能,才能得到源源不断的发展推力;另一方面,如果从小空间的角度来看,它们也需要在对话或协商中,去跟其他文化场域进行磨合与角力,从而使它们共同支撑起的大空间,能够展现为充满生机与弹性的,并且能够随着环境的变迁,变得扩大或缩小、移位或变形、演化或调整。——实际上,所有诸如此类的变化轨迹,已经构成了以往的全部世界史,而且也势必再支撑起今后的全球性历史。
正是出于这个缘故,正如紧紧伴随着全球化趋势的,还有个相反的在地化的趋势一样,如今全球史过程的另一奥秘则又是,人类并不只是在一窝蜂地拥向大空间;恰恰相反,即使那种国际大空间业已形成了,那些共同叠合起它的各个文化小空间,也仍然需要予以保留、呵护乃至加强。

“见鬼,‘亚马逊’的域名已经被抢注了!”
这很主要的是因为,凡是传播到了更大空间中的文化内容,其具体内涵就一定会随之而被稀释,而且在这种成反比的线性关系中,那个大空间越是开阔与广大,其间的文化信息就必然会越是稀薄,乃至于稀薄到了仅仅倚靠那样的内涵,并不能支撑一个特定共同体的赓续与发展。这也就意味着,如果有一天,地球人不仅自己建立起了自己的国际大空间,还必须跟外星人去建立彼此的星际大空间,我们也仍然可以想象,那中间的文化信号一定会是高度抽象的。比如,我们既不可能要求外星人也来欢度我们的、具有特殊文化传统的节日——如果他们也有这类文化心理需求的话——也不可能发自内心地投入到他们的节庆欢乐中去。

这样一来,我们就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过去和未来的生活世界中,永远都不可能只有向之归化的大空间,却并无对之认同的小空间,正如任何一个特定的个人,都永远不可能没有自己亲切的乡音,而只去讲一种由书本所规定的、冷冰冰的普通话。无论如何,在任何一种特定的小空间中,都有其无法进入,也不需要进入大空间的东西,特别是它的特定的人类学之根,它的特定的历史路径依赖,它的特定的文化风俗习惯,它的特定的文字与口传传统。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才在前不久的文章中写道:“即使是生在这个日益全球化的时代,那种误以为自己可以不凭任何文化本根,便能游走和投机于各个文化场域之间的‘国际人’,尽管可以自诩为‘最超然’或‘最先进’的,并且还往往会据此而轻视本国的国学,可在实际上,都不过是最没有力道和最缺乏理据的。——这样的人,除了要频频地返回本国来拾人牙慧之外,也就只能再到国外去进行有意无意的逢迎,以经过刻意掐头去尾的本土案例,去逢迎地验证那些由别人所创造的、似乎‘必有一款会适合你’的‘先进’理论。而由此一来,即使原本是在别家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智慧资源,一旦到了这些国际学术掮客口中,也就只能被变成唇齿之间的无根游谈了。”(《国学如何走向开放与自由》)
在这方面,又正像我在前边的那篇文章中所说的:“比如,就以本人生平最爱的贝多芬为例,我们一方面当然应当意识到,即使以往只被抽象理解的《第九交响乐》,仍有暗中的文化之根和宗教之根,而不能对它用人声所推向的乐曲高潮,只认定是利用了某种‘高级的乐器’。但我们另一方面也应注意到,尽管这两者几乎就是前后脚完成的,而且‘贝九’还肯定是挪用了《庄严弥撒》中的人声要素,但由于其宗教意味的浓淡不同,毕竟只有前者才是属于‘大空间’的,而后者则只能是属于‘小空间’的。——换句话说,在非西方的或非基督教的世界中,人们也许可以接受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却未必就可以领教他的《庄严弥撒》,因为至少在前者那里,特定宗教的意涵并不是以一种劝世口吻而道出的,而是以一种稀释的和人间的形式而表现的;甚至,人们即使在接受‘贝九’的时候,也未必就是全盘接受了它的‘文化之根’,而只是接受了它能跟自己的文化意识相互重叠的那个部分。”(《国学如何走向开放与自由》)
也正是出于这样的思路,我还曾在另外一篇文章中解释道:“在交互文化的全球化进程中,必须要分清哪些东西属于‘文化之根’和哪些东西属于‘文化之果’,从而知道哪些东西只能属于‘小空间’,而哪些东西则可以属于‘大空间’。也就是说,由于任何特定的具体文明,都在它的特定起源之处,有其独特而隐秘的、人类学意义上的根源,所以,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真正能够提供给跨文化交流的,便只是从那些根底处长出来的、作为‘文化之果’的东西。反之,对于那些隐秘而独特的‘文化之根’,凡是居于特定文明之外的人们,充其量也只能去同情地了解,力争能够既‘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而绝不能亦步亦趋地再去学习。”(《总体攻读与对话意识》)

应当看到,在这种“文化之根”与“文化之果”的辩证关联中,其实任何一种特定的文化小空间,它越是向国际大空间输送得更多,那么,在它内部的文化动能也势必就越强,或者说,它内在禀有的文化独特性也就越大。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其实文化的普遍性和文化的殊别性,文化的外向性和文化的内生性,从来都是相互依赖着的,而并不是相互排斥的。
必须马上转而提醒,这又绝对不会意味着,任何一种小空间便可以有故步自封、抗拒世界的理由。恰恰相反,正如我以往在北大课堂上反复申论的,在这个全球化的复杂时代,我们一方面当然应该存有“文化本根”,但另一方面却绝不应该持有“文化本位”。——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任何的一个文化小空间,尤其是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如果完全不去跟大空间接触乃至试图叠加,那么它就相当孤僻或怪异、单薄而萎靡,就只能这般一味地顾影自怜下去,就失去了生存下去的活力和理由。
在这个意义上,我所提出的这种“大空间”与“小空间”的理解框架,恰正是要在来自双向的危险中,去小心翼翼地采取“执两用中”之道,既去避免文化失语,又去避免民族主义,既去避免文化失序,又去避免闭关锁国,既去主张文化自立,又去避免文化自大——或者更尖锐地说,是既要去避免在全盘西化中,由于丧失自我而走向失败,也要去避免在不知变通中,由于闭目塞听而走向殊途同归的失败。
正是鉴于诸如此类的缠绕与纠结,也鉴于当时国内学界又荡回了“文化相对主义”的一极,我才在二十多年前的《文化观的钟摆》中指出:“如果我们退一步尚可以权且采取‘文化相对主义’之方法框架的话,那么进一步却又完全不能满足于它。既然‘万国之上犹有人类在’,我们就不能一味去把古人留下的文化母语当成不可逾越的观念障碍,竟致使这个星球上的人群永远被剖化成若干不同的物种;特别是,恰因为置身于人类一方面已经智慧到了可以顷刻间毁掉他们共乘的飞船,另一方面却仍自愚笨得不知怎样和睦共处的时代,我们就更不能把辉煌的历史传统糟蹋成沉重的思想包袱,竟致使各式各样的有色眼镜总是妨碍大家去直面对于全人类都堪称最为紧迫的问题。纵使横隔在地表上的各种文化篱笆从我们刚刚落生那天起就使每个人的精神视野都留下了先天的盲点,我们也必须自觉与这种‘文化的宿命’进行不懈的抗争!”
我还多次辨析过这样的文化景观:如果让人扼腕的是,文明间的接触与重组从“短时段”的参照系来看,往往会引起冲突、摩擦与震荡,甚至会引起特定文明的衰落或衰亡,那么让人惊喜的是,只要哪个文明还命不当亡,只要它能够咬牙熬过最初的苦痛,只要它还能在这种苦痛中汲取经验,同时也汲取来自外部世界的有益滋养,那么,它就会在历史“长时段”的参照系中,守候到自己的再次崛起与再度辉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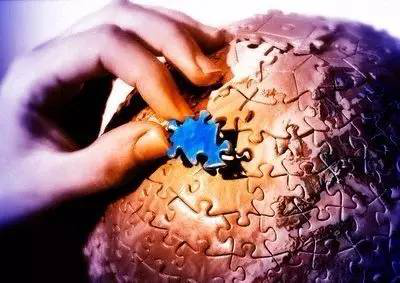
从“大空间”和“小空间”的理解框架来看,之所以会只是由于观察“时段”的不同,就足以从同一个历史过程中,观看出如此迥然有别的、忧喜不同的历史景观,也正是因为在冲突最剧烈的文明边际,反而最有可能产生出丰厚的文化叠合,甚至会因为由此叠加起来的文化高度,而崛起为未来文化空间的中心地带。
这中间的道理,也正如我以前曾经写到的:“历史阵痛最剧烈的时代,往往也正是历史惰性最小的时代。纵观孔子、苏格拉底、释迦牟尼和耶稣之后的全部世界史,也许再没有哪个时代的哪个民族,会像近现代中国人这样苦难深重地游离于各种既成的文化秩序之外;但也正因为这样,也就再没有谁会比他们更容易从心情上接近敞开着最大创造机会的新的‘轴心时代’。”(《回到轴心时代》)
进一步说,巴望着重新回到那个创造性的轴心时代,当然又是为了以再创造来超越以往的轴心时代,以便为人类再次打造足以安身立命的基业。
如果真想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像我前不久所指出的,要从冯友兰当年的“从照着讲到接着讲”,再发展到“从接着讲到对着讲”。——“一方面理所当然的是,对于任何严肃的思想者来说,无论他最初出生于哪个具体的时空,他由此所属的那个特定思想场域,尽管会向他提供出阿基里斯般的力量,却不应构成他不可克服和摆脱的宿命;恰恰相反,他倒是正要借助于从‘照着讲’到‘接着讲’再到‘对着讲’的学术言说,借助于不断拾级而上的、足以‘一览众山小’的文化间性,而不断地攀越着文明的高度,和走向思想的合题。”(《国学如何走向开放与自由》)无论如何,唯有在这种既据理力争又虚怀若谷的“对着讲”中,发展到了立足于全球场域的人类文明,才可以敞开更加辉煌的突破可能。
只不过,我最后还是要再来提醒一遍,即使当真能够在“对着讲”的基础上,从某种意义上超越了以往的轴心时代,我们也仍然只能是在相对的或有限的意义上,或曰在传播学的“价值中立”的意义上,形成更加广大的文化空间。而既然如此,我们就仍要慎用所谓“普世”的概念,因为我们仍要充分地意识到自身生命的有限,从而谨慎地对待自家思想的局限。正如我们置身于当今的时代,已经接近于心悦诚服地接受了“自由与平等”“科学与民主”这类的观念,但笔者受到本文所提的框架的制约,仍然只会把这样的思想内容,谨慎地说成是进入了国际“大空间”的,而不是贸然把它们说成“普世性”的。
唯其如此,才可能像我前不久写到的:“我们在一方面,可以用‘大空间’来取代那个‘一元’,从而既在传播学的相对意义上,认可某些相关要素的‘普遍性’,却又避免了必然引起争议的‘普世性’,以及由它所代表的文化霸权;因为在这样的意义上,它们无非是更靠近那个‘一元’,却并不担保其本身就是那个‘一元’。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用‘小空间’来取代那个‘多元’,从而又在人类学的经验层面上,守住另一些相关要素的‘殊别性’;由此在这样的意义上,这种‘多元’就既可以确保世界的丰富性,又不至于撕裂总体人类的基本共识。”(《起伯林而问之:在自由与多元的轴线上》)

以赛亚·伯林
事实上,如果我们不能冷静甚至冷酷地认清这一点,并且始终如一地严守住这一点,那么,我们也就根本不可能基于丰厚的文化间性,而完成对于昔日那个轴心时代的超越。另外,也只有既具备了这种充满批判精神的意识,却又并不因此便感到失望与失重、惶惑与眩晕,我们才算是把人类文明的价值基础,从而也是把自己本身的全部生命过程,奠定到了清醒的理性主义支点之上。
责任编辑:姚远
作者文集更多
- 【刘东】儒家德教有何重要性? 03-23
- 【专访】刘东:“天下大同”何以必然来自··· 01-12
- 【刘东】落实儒学的历史条件 ——从《天··· 01-26
- 【刘东】国学热是文明自赎,精英儒家能··· 12-04
- 【刘东】国学如何走向开放与自由 06-09
- 【刘东】走出由“普世”观念带来的困境 08-03
- 【刘东】传统就像空气,只有在它遭到毁··· 07-04
- 【刘东】世俗儒家与精英儒家 06-06
- 【刘东】真正的儒者会拥抱世界 11-25
- 【刘东】国学如何走向开放与自由 07-20
微信公众号
儒家网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

微信公众号
儒家网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