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苍龙】“本末先后”与“因人而异”——当代读经教育的两个原则和内在张力
“本末先后”与“因人而异”——当代读经教育的两个原则和内在张力
作者:王苍龙 (英国爱丁堡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
来源:“探索与争鸣”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八月廿七壬子
耶稣2016年9月27日
当前有关读经教育的讨论正在往纵深的方向发展。9月3日,此次争论的中心人物王财贵先生接受专访(简称“专访”),可算作对批评者们的一次总体回应。不过,王教授的回应似乎并没有得到学界的认可。贺希荣老师在同日发表的文章(简称“贺文”)中认为,“王财贵的回答没有直面任何问题,甚至没有作出任何姿态,一仍其旧之陈义甚高虚与委蛇而已。”
笔者的看法是,一方面,王教授的确摆明了一个姿态,并以他自己的方式直接回应了一些重要问题;但另一方面,他的这些回应也的确是老调重弹,与以前的论述相比,不论是内在逻辑还是立场姿态,并无二致。之所以说他摆明了一个姿态是因为,他的表态是立基于当前读经教育的“现实生态”的。例如,在有关他本人与读经堂主的关系这一关键问题上,他申明“读经圈内所有教师家长皆为朋友,彼既非我学生,亦非我职员,我只能劝,不能记他的过,革他的职”。这符合读经教育的现实,因为不管读经圈内部有多少争论,都是在民间社会的背景上进行的,王财贵先生不论其理念是否被私塾堂主接受、在多大程度上被接受,也的确没有法律上的强制权力。换言之,王教授和其他私塾堂主,只是道义和理念上的“师徒关系”(一些亲近的追随者们以“老师”称之),并不是法律行政性的上下级关系。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民间读经教育团体内部不能进行自我调整。正如贺文所建议的,王教授可以通过“改变产品标准,比如说不主要看包本……”来对私塾产生约束力。但是,这种“约束力”也只是道义性的、软性的、非强制性,不具有行政性、刚性和强制性。
可是,令批评者们无法理解的是,为什么王财贵教授依然还是“旧调重弹”呢?为什么他不直面“老实大量纯读经”模式带来的问题呢?目前的讨论多从读经教育团体的宗教性、王财贵本人的宗教立场出发进行激烈批评。在本文中,笔者试图从读经教育理论的内部逻辑入手,寻找可能的解答。通过仔细研读该专访,笔者发现,王财贵的读经教育话语实际上隐含了两个不同原则,分别指向读经教育的两个不同方向。这两个原则虽然在他的读经教育理论建构中似乎可以自洽,却在现实的实践操作中引起了诸多问题,呈现出一种内在的张力。这两个原则,一个是“本末先后”,指向培养“文化大才”的方向;另一个是“因人而异”,指向“全民读经”的方向。无法有效地协调此二者的关系可能是王财贵教授不能直面当下问题的一个理论性的原因。

王财贵
1“本末先后”:一种文化激切的心态
第一个原则是“本末先后”。在专访中,王教授说:“我常以为‘物有本末,事有终始’,我所说的,其实只是个立本知止的方向,其他是个人自由的。”在他的读经教育理论中,一个贯穿始终的内在逻辑是,把教育教学的内容区分为本与末、体与用、先与后的二元关系。抽象地来说,读经教育中的本末观念主要有三点:(1)“本”比“末”更重要;(2)不仅如此,“本”涵盖着“末”,二者并不在同一层级上;(3)既然如此,教育应该先“本”后“末”,“本”先而“末”易——这被认为是合理的教学次第。由这一论述逻辑,合乎人性的教育便被理解为一个区分本末且按照本末先后开发人性的过程。具体地来说,在读经教育中,常见的教学安排是:以读诵经典为根本,这需要优先去做;其他科目如识字、写作、阅读、吟诵、训诂、典故、才艺皆为末节,可待大量读经后再做不迟。
“本末观念”在读经教育理论中最明显的一个体现是记忆与理解的关系。在王教授看来,记忆被视为儿童读经教育的“本”、“先”、“体”,理解则被视为“末”、“后”、“用”。他说:“人类儿童期学习能力主要表现在记忆,而不在理解,所以吾人注重13岁之前的基础教育,先以记忆为主,让他背诵经典。”之所以做这样的本末先后安排,是因为他认定记忆与理解的时机不同,儿童时期记忆力强而理解力未发达,应该“以记忆与智慧的教育为先,以理解与知识置后”,这样才“正合人性成长的轨迹”。不仅如此,他还宣称记忆力教育对理解力教育具有“笼罩性”,即:先做记忆的教育有助于“让一个人具备更好的理解能力与学习知识的兴趣”。
以“十三岁”为界,先记忆后理解,这是“本末先后”原则在读经教育理论中的具体表现。尽管在论述时,王财贵结合了儿童发展心理学的有关论据,但在他看来,记忆为本先、理解为末后应属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东西,并不需要科学论据加以佐证——当然,王财贵教授所使用的“科学论据”也被柯小刚教授批评是“伪科学”。
之所以强调记忆经典为本,而把解经置于相对不那么优先的地位,这可能与读经教育理论背后隐含的一种文化激切的心态有关。从2001年北师大的那场演讲开始,王教授就在不断地强调“先读起来再说”,字里行间能体会到复兴文化传统的紧迫感。在另外一次专访(2012年)中,他在谈到吟诵与读经的关系时说:
“我不是反对音韵和吟唱,但我们现在是连一点文理的基础都没有了,要救亡图存啊。这个时候不需要那么在意太平盛世的东西。所以,先读起来比较紧要,读熟了再吟诵,不迟。或者一面读,一面以吟诵作为调剂是可以的。本末要分清楚。”
这种“救亡图存”的文化激切心态在读经实务上有两个鲜明的体现。一个是“阿猫阿狗”论。在专访中,王教授专门提到这一点,明确地说道:‘阿猫阿狗也可以当教师’,不是一种积极的正面主张,而是一种消极的遮拨之语。”在他看来,之所以宣扬“阿猫阿狗”也可教读经,是因为“在今日经教断丧百年的时代”,圣贤难寻,而孩子读经却是要“尽早开始”的,“不能等找到圣贤了才开始”。这种激切的文化心态显而易见。
另一个体现是三十万字包本背诵的规定量。在读经圈内有一种“方法”,叫做“双十读经法”,亦即每天读十个小时,连续读十年;另有一种“三十万字包本录像”的提法,即把三十万字中外文经典全本背诵并加以录像。以此二法,希望在儿童时期奠定一个人一生为学的“根本”和“基础”。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在文化激切的心态下,按照“本末先后”原则对读经的数量和时间进行定量化和标准化的规定。这一量化取向被诸多读经私塾特别是最近几年出现的“纯读经”私塾采用,在教学实践中造成了不少问题——也正因为此,它成为这个阶段“读经”争议的主要目标,是被批评的主要对象。

2 “因人而异”:读经教育的多元性
另一个被王财贵先生所强调的原则是“因人而异”。在这次专访以及其他场合中,他反复提及所谓的“老实大量”应是“尽量老实,尽量大量”,意思是,每个人应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在自己可能的范围内尽量做到“老实大量”。“因人而异”原则不同于上述“本末先后”原则的关键处是,它并不对读经的数量和时间进行定量化和标准化要求,而是采取一个较为开放、灵活、多元的态度对待读经教育及其与其他教育的关系。在这一原则下,读经教育的确真正具有呈现“百花齐放”局面的可能性,有助于切实推动“全民读经”。正如王教授在专访里所言:
“譬如有的从论语教起,有的从蒙学教起;有的先教识字,再背书,有的先背书,后教识字;有的有阅读,有的纯读经;有的重诵读,有的重德行;有的学才艺,有的纯读经;有的有外文,有的纯中文;有的以上书院为主,有的不上书院;有的杂以宗教,有的纯文化;有的在家读,有的在学校读,有的在社区业余读,有的在学堂读;有的一天读十分钟,有的一天读十小时。不一而足。这哪里是一刀切啊?”
的确,在这种“读经+”的模式下,看不到“一刀切”的影子,因为一切教学模式、教学方法、教学内容、教学过程都是因人而异、因地制宜的。因此,个体在如何读经的问题上,“必需独立做思考”,“各自做好自己即可”。进而言之,本着“因人而异”的原则,即使是在具体的“读经”过程中,不同的个体也应被区别对待,学堂也应“因材施教”。正如王教授在专访里所说:
“即使在所谓‘严格纯读经’的学堂里,有的学生一两个月背一本书,有的三四个月,有的半年,也有一两年才背一本的,视各人能力而不同。同一年龄的孩子所读的书,有的开始读论语,有的读完论语读孟子了,有的四书读完读五经了,有的中文读完在读外文了。教学的方法,有的用带读,有的用齐读,有的用自读,有的用自学。这都是因材施教的范例,不同于一般教育,凡九岁的学生都学三年级的语文和数学。”
因人而异的原则甚至还体现在对“理解”过程的解读上。在王财贵看来,理解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是需要经过长期的酝酿而生发出来的自然的感悟。“老实大量读经理论”的实践者空山先生在一篇题为《读经到底要不要理解》的文章中认为,理解是无时无刻不在的:
“即使在所谓‘严格纯读经’的学堂里,有的学生一两个月背一本书,有的三四个月,有的半年,也有一两年才背一本的,视各人能力而不同。同一年龄的孩子所读的书,有的开始读论语,有的读完论语读孟子了,有的四书读完读五经了,有的中文读完在读外文了。教学的方法,有的用带读,有的用齐读,有的用自读,有的用自学。这都是因材施教的范例,不同于一般教育,凡九岁的学生都学三年级的语文和数学。”
“一个孩子即使不读经,甚至不读书,只要他生活在一个有人与人交往的环境里,只要有人和他正常地交流,他的理解力也照样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老师的一句话,父母餐桌上的聊天,和小伙伴的游戏娱乐,都在增长他的理解力。”
由此,他宣称孩子再读经的过程中会有自己的理解,这种理解是一种不需要人为干预就能产生的,尽管“并不需要特别地精细”。

3两个原则的内在张力
两个原则指向了两个不同的方向:“因人而异”的原则指向了“全民读经”的方向,而“本末先后”的原则指向了培养“时代性文化大才”的方向。如何处理这两个原则的关系呢?对此,王财贵本人提供了一种理论性的说法。他认为,教育应该“先立乎其大”,从最高原则、最高标准出发(即“本末先后”原则);但是在实践过程中可以“打折扣”,可以不必固执于那个最高标准,而是根据各人的实际情况而采取相宜的办法(即“因人而异”原则)。
不过,在实际的读经教学实践中,处理这两个原则的关系却并不那么容易。特别是文礼书院成立以后,本着培养“时代性文化人才”的宏伟目标,王教授的读经教育理论日益偏向于定量化、标准化、老实化、大量化、纯读经化,特别是提出的三十万字包本录像的具体量化指标,对于各私塾具有显著的导向性。于是,一些学堂纷纷成立“文礼书院班”,以包本录像三十万字为教学内容,以进入文礼书院为教学目标。在这个通往三十万字的包本录像过程中,学生的学习内容单一化,不得不经常忍受老师的批评和体罚,而那些被搁置的科目也真的就被搁置了。
与此同时,“因人而异”的原则却相对地被轻视和低估了,只是经常作为一个应付批评和争议的辩护理由被使用,而这种做法很容易让人产生如贺文类似的感觉:没有直面任何问题,“做了甩手掌柜与事外汉”。
根据笔者的观察,虽然在“纯读经”模式提出之前读经圈也有所谓“七节五轮”包本背诵的方法,但是,专门以进入文礼书院、完成三十万字包本录像为目标的“老实大量纯读经”模式却是最近两三年才出现的,并不是读经教育推广之初就有。王财贵教授在专访之初评价此次读经争议时说:“我从五十年前刚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指媒体报道所反应的问题和情况)时,就了解了。何况二十余年来,争议不断,但都是那些问题的重复,几乎不必看,就了解了。”字里行间能体会到王教授对自己的读经教育理论的自信。但在笔者看来,读经教育十几年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新争议。面对这一新局面,旧有的应对方式可能欠缺足够的说服力和解释力,无助于新问题的解决。
在说完上面这段话后,王教授在专访中贴出了2006年的一篇《对“反对读经者”之总回应》的文章,文中把反对者分为有地位和无地位、真诚的和不真诚的,且主要是官员和学者两个群体。在此笔者想要提醒的是:如今这一轮(相对于2004年的读经争议,笔者称此次为第二轮)的争议,已经不再限于这两个群体;读经教育实践者这一群体是这一波争议的发动者和主要力量——媒体和学者只是这一波争议持续了一段时间后跟进报道和引发批评而已。也就是说,曾经深入实践“老实大量读经教育”的私塾堂主和追随这一教育理念的家长和学生,现在居然开始公开批评这一教学模式——这并不是二十余年前就有的情况。这是一个新情况,出现的是新问题,面对的是新局面。对此,读经教育实践者们需要重新定位自我,真诚地进行自我反思和自我批评,拿出一个直面新问题的姿态,这才真的有助于问题的解决,有助于读经教育的进一步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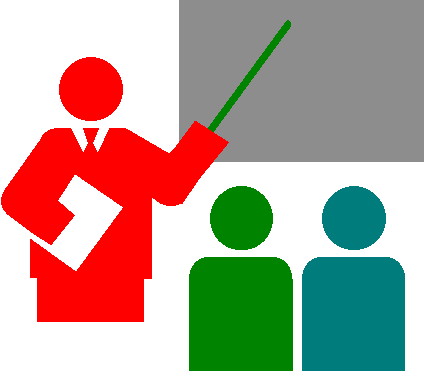
4结语
综上所述,笔者分析了读经教育理论的两个原则——“本末先后”和“因人而异”。这两个原则实际上指出了读经教育的两个不同发展方向:前者指向了一个培养“文化大才”的方向,后者指向了一个“全民读经”的方向。读经教育如今出现的问题,是培养“文化大才”的这个方向所出现的问题,这个方向的关键词有:三十万字、包本录像、双十读经法、纯读经等。换言之,基于“因人而异”原则的“全民读经”这个方向并没有出问题,顺着这个方向,诸如“论语一百”、业余读经班以及其他“读经+”的教育模式纷纷出现,真正体现出读经教育的活力。
进一步言之,当前的读经圈、媒体和学者的批评主要针对的是培养“文化大才”这一教育方向出现的问题,矛头并没有指向“全民读经”方向。然而,王财贵教授在面对这些指责时,自觉或不自觉地用“全民读经”的教育方向予以应对,的确有回避问题的嫌疑——回避由纯读经包本三十万字以培养“文化大才”这一模式所产生的诸多问题的嫌疑。

基于“因人而异”原则的“全民读经”的教育方向的确是一种“多元的教育”。从这个意义上讲,王教授所谓“读经是多元的教育”这一论述是合理的——把“读经”与其他教学内容相结合,相辅相成,当然很好。但是,基于“本末先后”原则、以培养“文化大才”为教育方向的纯读经模式,却只能是多元教育中的一元,只是一种教育类型而已。最近几年来,王教授以“全盘化西”为教育标准,其指向便是“文化大才”的方向。并且,这一方向在被不断地强化,造成了诸多问题,引起广泛争议。这些问题的出现并非偶然,它与王财贵教授的读经教育理论的内在张力具有内在的关联。
责任编辑:柳君


